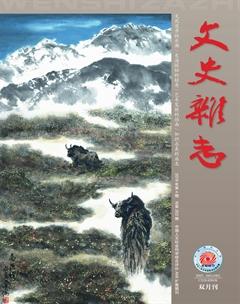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
嗣响

李白塑像(在安徽马鞍山采石矶)
中国古人践行报国理想通常走从军——上战场与入仕——进官场这两条途径。就初、盛唐的知识分子而言,则往往通过科举或荐举而出将入相。李白自恃才高八斗,自然不屑走科举入仕的路子(他自由散漫惯了,也没有兴趣去接受科举考试的桎梏与煎熬),而是采取干谒(求见达官贵人以获荐举)的方式试图直达高位,即以直通车的方式博得君王青睐,做个当代的傅说、姜子牙、管仲、诸葛亮或谢安,以拯世济民,治国安邦。为此,他不惜曳裾权门,四处干谒。在初、盛唐文人中他的干谒诗文写得最多,也最出彩,但也因此被后世的某些学者所看低,视为庸俗、丢人格。他被人批评得最厉害的就是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因醉酒冲撞李长史乘驾而写的道歉兼干谒的文章——《上安州李长史书》。
不过我们细读该文,虽不乏有恭维与自责之辞,令外人颇觉鄙下,但却暗藏玄机。这就是似抑实扬,外卑内亢,分明是一篇机智又骄傲的自我褒赞。你看他劈头一句就来得响亮:“白,嵚崎历落可笑人也。”(我李白,是个卓尔不群的拔尖人才,磊落坦荡,谁见谁爱。)接着才说他酒醉以后恍惚之间,未及回避君侯(李长史)座驾,“惟大雅含弘,方能恕也”(只有大德大量者才能宽恕)。反之,则不能原谅我李白。这便狠狠将了李长史一军。以后的行文便在这一张一弛、欲擒故纵中徐徐推进,最终捧出三首“辞旨狂野”的献诗请君侯一览,目的豁然昭明。识者至此不禁莞尔。所以说李白这篇《上安州李长史书》是一篇伪装得很好的自我推荐书。一些学者不谙个中奥妙,便匆匆以“卑下”论之,未免有遗珠之憾。
这情形,与李白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5年)于襄阳(在今湖北)晋谒荆州长史韩朝宗时所作《与韩荆州书》大致相同。是书起首一段“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云云,即被抑李者视为阿谀奉迎之词,但随后排闼而出的一段,则自当令这些抑李之士语塞。你看李白是如何夸赞自己的: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这一段将胸怀大志的李白的一腔节概、满腹风神如连珠滚石般泻而出,令人目清气爽而鼓之舞之。
需要指出的是,李白此次干谒韩荆州,虽仍难逃拍马屁之嫌,但却是长揖不拜,对后者以平辈礼相见。他后来所写《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诗有“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句,可为这种“失礼”行为作注脚。而这种失礼,却符合他“平交王侯”的一贯原则。由此,我们又不得不怀疑他在安州以酒醉挡李长史之道,有可能是借酒装疯,故意为之;然后才有机会借道歉而推销自己。所以说,李白的委屈自己是有尺度、有底线的,这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这正如赵蕤《长短经》卷一《文上》之《知人》所说:“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真正高洁的人一定有不可玷污的神色,真正有操守的人一定有值得信任的神色。质朴的神色,浩气凛然,坚定稳重。)李白有时表面的庸俗其实也难掩他内在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光芒。
李白在天宝初“供奉翰林”前的“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如果简略地给排个路线图,可以看出他“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之梦的连贯性、坚韧性与发展性——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前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李白知晓后专程赴成都,在苏颋必经之路上碰见他,恭敬地递上名片(即李白自称“于路中投刺”),并献上自己的几篇诗文(包括《大猎赋》初稿)。苏颋后来看了,颇为器重,对群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专车之骨”[1],即巨人之骨。苏颋用以美誉李白,说他是一个天才,又特别勤奋,虽然还略显稚嫩,却已见大家风范,假若继续努力学习,开拓视野,完全可以与西汉才子司马相如相媲美。李白听到大都督府传出的这一评语,十分高兴;十年后,将它写进《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让裴长史明白,自己20岁时,就受到当时天下大才子兼益州最高行政长官苏颋的赏识。不过,苏颋实际向皇上推没推荐李白,未见史料记载;或者推荐了,而未打动皇上的心,也未可知。
也就在李白向苏颋“路中投刺”这年(开元八年)底,他还向当时名扬天下的大文人、大书法家李邕[2]献诗,请求荐举自己。李邕当时从括州(治括苍县,在今浙江丽水市东南括苍山麓)员外司马升调渝州(治巴县,在今重庆巴南区)刺史。李白从成都匆匆赶往渝州拜谒李邕,并以《上李邕》诗一首表白心迹。诗云: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風歇时下来,犹能却沧浪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庄子·逍遥游》载齐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笔下的大鹏志向大,力量大,气魄更大,正是青年李白所摹效与寄托的对象,所以他常以之自况,表明自己的抱负与处世态度。他的这首干谒诗,因为是写给同样以才气自负而张狂的李邕看的,他引以为同好、同气或同类,所以毫不客气,直抒胸臆,将心中所想倾泻而出,无所遮拦,显出初生牛犊的勃勃生气和锐气。“宣父犹能畏后生”两句,用孔子(即宣父)在《论语·子罕》里的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表示自己少年已怀壮志,是国家未来栋梁,要李邕莫看轻了,须荐举提携才是。以李邕的秉性和眼力,他是应该欣赏李白的。只是李邕的异端、怪诞(《新唐书》本传载其“矜肆,自谓且宰相”,“素轻张说,与相恶”),不讨朝廷喜欢。所以他或许向上推荐过李白,但必定不为当局所看重。不过,不论李白渝州之行的结果如何,他与李邕一定建立了友好甚或亲密关系。他书法张扬飘逸的风格,很可能受到李邕的影响。天宝中,一生豪放自肆的李邕被宰相李林甫妒害,惨遭杖杀。李白为此一直愤愤不平。他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于吴中所写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发出悲鸣:“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对他所敬仰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礼。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即李白在安州冒犯李长史(因写《上安州李长史书》)前后,李白曾有机会拜谒到安州都督府都督马正会,向他呈上自己的几篇得意之作。当时的会面气氛应该比较好(不像见李长史那般尴尬)。事后李白通过好友、道士元丹丘(常为豪门座上客)获知马都督对自己有良好评价,十分高兴。他在第二年(公元730年)所写《上安州裴长史书》[3]里向裴长史报告了这事:
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
李白在给裴长史的汇报中,还提及开元八年(公元719年)他在成都受到苏颋赏识的事。他将苏、马二公前后两次的鉴评并在一起向裴长史分析:“若苏、马二公愚人也,复何足尽陈?傥贤贤也,白有可尚。”大意是说,像苏、马二公这样的人,是不会讲骗人的谎话的。如果他俩对我讲的是真话,那说明我确实是有才。文中的李京之,即李白在开元十七年酒醉冲撞的安州李长史,从时间顺序看,应是裴长史的前任。李白这篇给裴长史的上书,在他入京供奉翰林之前的著名的三封干谒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中写得最长,内容也最丰富——将自己的身世、交往、为人、才能、抱负一古脑儿地和盘托出。看来李白对裴长史印象不错,特别是在经历了与李长史的风波以后,李白尤其觉得应让作为父母官的裴长史了解自己;再者,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位可能与李长史不一样的属于伯乐级的人物。所以他在末段便重重地抛下明志诀世的狠话,以期彻底打动裴长史:
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弹长剑乎?
末句用《史记·孟尝君列传》冯弹长铗(剑)试孟尝君之典,倒逼裴长史非拿出诚意荐举他不可。不过,裴长史的重贤很可能是虚应故事。李白等了好一段时间,未见任何动静,就是连一句令他高兴的好话(像苏颋、马正会夸他的那样)也未听到。这跟“好客”的孟尝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让李白空弹了一阵长剑。李白大失所望,于是背起背囊,离开安州,果真向长安进发了。四百多年后,宋人洪迈读到这个故事,不禁感叹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容斋四笔》卷三)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春夏之交,李白经南阳(访诸葛亮故居)到长安,准备拜谒以“喜推藉后进”而名满天下的左丞相张说。时张说年六十四,正病卧在床,由次子、员外卫尉卿张垍出面接待李白。张垍也是一位才子,聪明伶俐,颇得玄宗钟爱,特将爱女宁亲公主(系第二十一女,原齐国公主)下嫁给他,让他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珍赐不可数”(《新唐书·张说列传附张垍》)。不过此人品行不端,鸡肚心肠。玄宗曾对他许以宰相之位,拟让他替代即将辞职的陈希烈;后因杨贵妃、杨国忠的阻止,未能兑现。这便让张垍对玄宗心生怨恨,遂与安禄山开始亲密接触。“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与陈希烈一道跑到安禄山伪朝廷,终究圆了一回宰相梦。只是好景不长,很快他就倒毙于乱军之中,未得善终。这当然是后话了。但当开元十八年张垍接待李白这位来自西蜀的年轻人时,他那埋藏于身体深处的劣根就已蠢蠢躁动了。李白的文名当时已从蜀、楚传至关中。这对以文讨巧的张垍来说很是不好受。他奉父命接待李白,却将后者安置到离长安八九十里处的终南山麓楼观(宗圣观)内的玉真公主别馆。玉真公主是唐玄宗的三妹,字持盈,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出家为道士,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又喜结文人。别馆系她接待道士和文士的一处地方。不过当李白来长安时,玉真公主已好久未来过此处了(或许已到洛阳长住);而何时回归,谁也不清楚。张垍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李白却蒙在鼓里。
李白当初被张垍带到这里,还想着见不到张说就见玉真公主也好。哪知这座别馆因长期无人居住,已处荒废状态:四处野草萋萋,青苔幽幽,蛛网密结,蟋蟀出没。厨房早断烟火,一日三餐全靠邻近慕名来访的村老士绅携来。加上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李白无处可去,只得随意翻翻别馆内遗留的书卷打发日子。李白穷极无聊,自然心生怨意,便写了两首诗送给张垍间或派来的童仆转给他,中有“吟咏恩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一)句;又有“投筯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裔沧洲旁”(同上,其二)句,明眼人一看便知李白是在借典自喻,借典譏人;讥刺的对象,自然是待他不恭的张垍了。张垍看罢二诗,也当然明白了。他知道李白已看穿自己慢客背后的“小九九”,恼而转怒,不过暂时隐忍下来,却为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埋下了伏笔。
李白在玉真公主别馆里还写了一首歌颂别馆主人的诗,题作《玉真仙人词》。诗云: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
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此诗中的玉真仙人,当以道教上清派的女高仙——上元夫人[4]为模特儿进行描绘,以博玉真公主一粲,而且也带有干谒献诗的意味。
李白以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为落脚点,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秋之交开始,至开元十九年春夏之交,在长安地区盘桓了整整一年(中间曾西游岐州、邠州,北访坊州,东至潼关,又曾在长安北门与一群纨绔子弟打过架),却终归未睹玉真公主真容。当他怀着落寞无主的心态离开长安,由黄河东下初游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之地时,途中在嵩山将《玉真仙人词》交给老朋友元丹丘,托他相机转呈玉真公主。(后者也常来嵩山。)玉真公主后来大概看到了李白这首称颂她的诗,明白李白的意思,加之也风闻李白的才名与相关故事,这才有了以后她向唐玄宗推荐李白之举。

玉真公主塑像(在安徽宣城敬亭山)
李白第一次长安之行原本雄心勃勃,希望通过权贵而直接博取上位,结果碰了软钉子——最想见的张说丞相死于开元十八年冬天,其子张垍则以酸溜溜的心态将他晾在荒郊野外,被他视为仙姑的玉真公主却始终不肯露面……这就是他所说的“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的历史真相。李白由是心生愤慨,在开元十九年离开长安赴梁宋途中用乐府古题写下著名的《行路难》(共三首)的前二首。其第二首吟道: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陰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这首诗的前半段连续使用了战国至汉初冯、韩信、贾谊的典故,抒发自己在昌明的大唐社会连遭小人妒嫉、权贵冷落的郁闷与不平;后半段则援引燕昭王易水畔置黄金台招贤纳才,使乐毅、邹衍、剧辛等贤士纷纷来归的故事,寄望于朝廷能敞开胸怀,大胆接纳天下有识之士为国效劳。这说明李白虽遭挫折,却心有不甘,还对朝廷抱着良好的希冀。所以他在《行路难》其一的末尾高声唱道: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气概轩昂之声,表明此时的李白虽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他相信自己只要坚持梦想,则干谒必会成功,朝廷必会召见自己,自己出将入相的报国理想总有实现的一天!
这里还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李白一直倔强地坚持干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当时并不是一件丢人、可耻的事,而是唐代官场的一种正常风气。这首先是秦汉以来的荐举制度促成的。隋朝以来,虽然科举制度渐成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但荐举仍为选官一途。朝廷鼓励各级官吏出于公心,在科举之外向中央荐举贤良和吏干人才,使之成为大多数官员的职责和荣誉。这就是说,荐举乃是一种政府行为。[5]葛晓音先生说:“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最终在盛唐开元年间成为朝野的共识,以及衡量政治清明的主要标准。这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独特的干谒方式的根本原因。”[6]所以,李白说苏颋、马正会都很赏识他,要向朝廷推荐他,这并不是诳话。也正是由于朝廷求贤若渴,大张旗鼓地倡行荐举(从唐太宗,中经武则天直到唐玄宗,都屡发诏令求贤),才使得唐朝各类干谒之士[7]能有恃无恐,口出狂言,不怕官员生气,不怕得罪朝廷,如《新唐书·员半千列传》所记员半千、《唐才子传》所记王泠然、薛据……
李白以布衣干谒,其干谒诗文中的良好自我感觉并不逊与体制内的干谒者,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令一些理学之士颇为气愤的还不在此而在于:李白尽管在干谒中自吹自擂,但毕竟是干谒,是屈己求人;可他偏偏不这么看。你看他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是如何说的: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在理学之士的眼里,李白讲自己“不屈己,不干人”,实在是在耍赖:他明明自开元八年(公元720年)20岁上就懂得向益州长史苏颋“路中投刺”了,甚至还千里迢迢地跑到渝州向刺史李邕献诗,怎么不算屈己、干人呢?这么不认账,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不过,我们今天来看李白的这种近似无赖的话,一是觉得有趣,可爱;二是真的是他的内心话。因为在他和他以前的初、盛唐的干谒者看来,干谒并不可耻,更谈不上丑恶,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进而可以说是一种给朝廷帮忙,为国家分忧的行为,所以他们要大声讲话,大声讲自己的好话、真话,以期不枉没自己的才华而圆出将入相之梦。葛晓音先生有一段分析准确地找出了以李白为代表的初盛唐干谒之士的心理支点:
初盛唐文人在上书陈启时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干谒,总是竭力将自己的行为与一般的干谒区别开来。这固然与干谒书启的写作技巧有关,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改变了干谒者的心理状态。统治者求贤礼贤的姿态使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被干谒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点,从而在干谒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气壮地将干谒视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为。……盛唐文人所高唱的“平交诸侯”,实质上正体现为在干谒中凭文章道义与王公卿相保持平等的心理。“不屈己,不干人”的理想与干谒的实际行为也正是这样取得统一的。[8]
而李白在干谒中所表现出的文章才华与道义担当在初、盛唐诗人群体里尤为突出,其人格自信与傲岸风骨也最强烈,可以说到了盛气凌人或者咄咄逼人的地步。这便令许多本来有意荐举他的公卿、长官们望而却步。像张垍这样本来就心胸狭窄的小人自不必说了,即便像“喜识拔后进”,“当时士咸归重之”(《新唐书·韩朝宗列传》)的韩荆州大概对他也是虚以委蛇,懒得管他的事。所以李白的干谒从20岁开始,直到43岁,23年间尽管很辛苦,却几乎是瞎忙,在经邦济世这方面可谓蹉跎岁月。
注释:
[1]《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装满一车)。”
[2]宋《宣和书谱》卷八著录李邕:“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也。尝作北海守,故世号‘李北海。……邕资性超悟,才力过人,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李阳冰谓之‘书中仙子。裴休见其碑云:‘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大抵人之才术多不兼称:王羲之以书掩其文,李淳风以术映其学。文章书翰俱重于时,惟邕得之。当时捧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巨万余,自古未有如此盛者也。观邕之墨迹,其源流实出于羲之。议者以谓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于实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为世之所仰慕,率皆如是。”
[3]该书也是因遭“谤詈攒毁”,自辩清白而上裴长史。这与《上安州李长史书》的起由大同小异,为干谒寻找借口。
[4]《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八《道部》载《茅君传》中上元夫人出场:“及上元夫人来,闻云中箫鼓声,龙马嘶鸣。……上元年未笄,天资绝艳,服赤霜之袍,披青锦裘,头作三角髻,余发散于腰。戴九晨夜月之冠,鸣六山火藻之佩,曳凤文琳华之绶,执流黄挥精剑,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呼之与同坐。”李白有《上元夫人》诗:“上元谁夫人?偏得王母娇。……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
[5]参见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页。
[6][8]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第223—224页。
[7]唐代干谒类型很多,大体分为科举体制内的干谒与体制外的干谒,后者多为布衣行之,如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