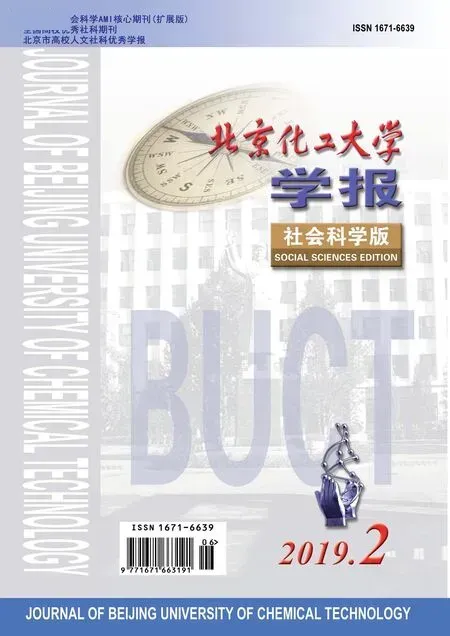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扬弃观
宋聚磊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一、引言
乔姆斯基(Chomsky)是“当代思想大师”[1],被誉为语言学界的牛顿和爱因斯坦。1957年,乔姆斯基的第一部专著 《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问世。这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的诞生和乔姆斯基革命(Chomskyan Revolution)的开始。此后,该理论很快发展成为现代欧美语言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时至今日,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对他人甚至自己的无数次扬弃后,生成语法理论依然青春不老,它拥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真正原因当属其蕴含着深层的哲学思想基础和扎根于厚实的哲学理论沃土。那么,在理论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指引乔姆斯基虽历经磨难却依然勇往直前呢?本文从这一理论的背景着手,联系现当代语言学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哲学层面对乔姆斯基理论的多次扬弃进行了梳理、归类和分析,希望对今后的理论创新有所启示。徐烈炯曾言:“研究他的思想时不仅要考虑他继承前人之处,更要看到他的独创性。”[2]乔姆斯基的创新正是源自其对不合理的观点的批判和对合理的见解的继承与发展,通过扬弃和超越,最终实现创新。
二、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本体论扬弃
恩格斯(Engels)说过:“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3]对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回答,是一切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4]。沙弗斯曼(Schafersman)曾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物质或物理的世界、非物质的世界以及超自然的先验世界①参见:李侠.有关自然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辨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50-54.。其中,非物质的世界包括心灵、观念、价值、想象和逻辑关系等。唯物主义(materialism)相信第一世界而否认第二世界的存在;自然主义(naturalism)则同时相信这两个世界,并认为没有必要否认第二世界。乔姆斯基主张自然主义的“本体一元论”,他是尝试将心灵自然化并试图巩固其本体地位的践行者。
(一)对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弃
对乔姆斯基的本体论立场影响最早、最大的当属笛卡尔(Descartes)。早在17世纪,笛卡尔提出“心灵实体的设定”,这一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当时的科学和哲学尚未分化,因此这是他在所处年代所遵循的科学发展方法的产物。由于心智的存在无法获得机械力学的解释,将其设定为第二实体的确是无奈之举,比如人的思考、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等现象。尽管如此,笛卡尔是试图将心灵研究纳入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第一位尝试者[5]。然而,其不足之处也是他对心智的设定。“实体二元论”容易遭到批判是因为心智现象的实在性无法获得后续经验的证实,而无法证实其实就是否认心智现象的存在。乔姆斯基反对笛卡尔关于存在一个精神实体和一个物质实体的二元论观点[6],他认为,笛卡尔所谓精神实体的心智应是人脑的一部分,人类的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并非源于上帝,而是由人脑决定[7]。乔姆斯基摒弃其二元论观点,坚持理论与方法上的一元论原则,把语言看作自然客体(natural object),把语言官能视为人脑天生内嵌的生物器官[8]。乔姆斯基不会在获得证实之前就对任何事物的客观性或可靠性加以设定的态度,体现了其对笛卡尔思想的批判,而这种基于自然科学方法对待心智现象的态度很可能是更科学的。
(二)对罗素“中立一元论”的扬
罗素(Russell)承认:“他人具有心灵这一假设不可能通过类比论证而得到任何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否定其真实性,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当作一个有效的假设。一旦承认这个假设,就能使我们通过证言来扩充我们关于可感世界的知识。”[9]他通过对物质和心灵的深入分析,得出了自己的“中立一元论”思想,把感觉看作是比物质和心灵更基本的材料。他认为,我们无需假定心和物的存在,只要承认两者是感觉的逻辑构造就足以合理地解释整个世界了。不过,感觉似乎在本体论上并不处于根本的地位。关于“中立一元论”的本体论问题,学界亦存在争议。金岳霖曾批判罗素的这一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论[10]。张家龙则认为罗素的思想是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因果实在论[11]。罗素的本体论其实体现了其对任何事物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在获得科学的证实之前都不要盲目加以设定的科学态度,乔姆斯基在对待心智的现象上与他所持有的态度是一致的。
(三)对蒯因“本体论承诺”的扬弃
1943年,蒯因(Quine)最先使用“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的概念,将本体论研究概括为“有什么”(What is there? ),并将本体论分为事实问题和承诺问题两大方面。他认为,本体论研究应该专注于承诺问题,其实质是一个与语言和逻辑有关的问题[12],本体论与自然科学处于同等地位,应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哲学领域,从而使哲学本身自然科学化[13]。秉承自然主义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必定不会忽略蒯因这归根到底与语言相关的本体论。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虽已具有初步反基础主义的立场,其实是认可一种相对的基础主义的存在,并未将反基础主义贯彻到底,因为基础主义必须经得起自然科学与更多后续经验事实的检验[14]。他要求把认识论与心理学、生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直接联系起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认识的合理性。而乔姆斯基的本体论立场则宣示了另一种反基础主义的可能,他拒绝在科学未及之处对何物存在的问题予以回应。因此,他的本体论立场既有助于认识论研究的顺利开展,也不会为某人所设定的基础或规则所羁绊。
可见,乔姆斯基自然主义本体论立场的贡献在于其批判了论断本身。当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证实任何一个有关“何物存在”的一般论断时,勿妄下论断正是追求自然科学之细致严谨的体现[15],如“心智/大脑”(mind/brain)这一术语的提出便是于此。他之所以坚持使用这一术语而不统一使用brain,是因为不排除可能同时存在可以称之为brain和mind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可能[16]。可以说,乔姆斯基的研究态度很可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更基本的态度。
三、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认识论扬弃
认识论是关于知识和知识获得的研究,是在探讨真理之前首先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和可能进行探讨的哲学分支,长久以来一直是哲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乔姆斯基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认识论者,他反对经验主义的知识获得方法,继承了理性主义的知识天赋观念,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先验逻辑进行改造。
(一)对斯金纳“行为主义认识论”的弃和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扬
1959年,乔姆斯基出版《论斯金纳的〈言语行为〉》(A Review of B.F.Skinner’s Verbal Behavior),该评价敲响了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丧钟,被认为是书评中极具毁灭性的评论[17]。在思考语言知识的习得过程时,刺激贫乏(poverty of stimulus)现象的存在和语言创造性(creativity)的事实极大地撼动了行为主义理论的根基,也几乎颠覆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行为主义认识方法。乔姆斯基把儿童语言获得的这一现象称为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表明了其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唯理论立场[18]。
1966年,乔姆斯基出版了《笛卡尔语言学:唯理主义思想史之一章》(Cartesian Linguistics: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重新解读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深化了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内涵,复兴了这一重要传统思想[19]。他从不避讳自己的思想理论来源于笛卡尔的哲学或至少受到了笛卡尔的启发。作为唯理论的主要代表,笛卡尔提出天赋观念说(innate ideas),即“内在思想”和“固有结构”学说。很明显,乔姆斯基认同人的语言直觉知识是存在于人脑的“固有结构”,其天赋原理、天赋结构、天赋机制和天赋语言能力等概念都是继承笛卡尔而来。他否定了洛克(Locke)的白板说(Theory of Tabula Rasa)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观点,从而引发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诞生[20]。 在对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继承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扬弃性地提出了具有明显自然主义倾向的天赋语言观,将语言学研究纳入自然科学(主要指生物学)的体系加以理解。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源于心智器官(mental organs),虽与生俱来却可以独立于物质而存在,能够在经验环境的引发下正常地生长和成熟。
(二)对布龙菲尔德“刺激反应论”的弃和对洪堡特“语言本质观”的扬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语言学理论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背景,把语言看作是说话人的刺激(speaker’s stimulus)和听话人的反应(hearer’s reaction)的结果,是一种“习惯”。他反对心灵主义和泛灵论,认为人并没有“思想”,只是发出声音(说话),这种语言声音足以激发其他人的神经系统,成为一种外部刺激,从而影响他人的行为[21]。“当孩子不断重复发音过程时,声波就冲击他的骨膜。这样形成一种习惯。这种无意义发音动作教会他照样去发出冲击他的耳朵的声音”[22]。著名的例子当属吉尔(Jill)通过言语刺激使男朋友杰克(Jack)为她摘苹果的故事。乔姆斯基显然不同意布龙菲尔德关于语言是刺激反应的“习惯性”结果这一论断。
在关于语言本质和习得的思想上,乔姆斯基与洪堡特(Humboldt)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洪堡特认为,事实上我们并不真正教授别人语言,而只能提供语言发展的一些条件,语言在这种条件下以自身的方式在思维中同时得以发展[23],语言能力是由个人内部发展而来的。乔姆斯基以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为视角,认为语言机制就像身体其他器官一样由遗传决定,可以在适宜的语言环境中生长、发育和成熟[24]。因此,语言本质上可能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一方面由生物遗传所决定,另一方面又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信息交流,这一系统自组织的语言理据观体现了乔姆斯基对布龙菲尔德和洪堡特语言观的弃与扬。
(三)对康德“先验认识论”和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扬弃
康德(Kant)在其《任何一种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中将先验(a priori)这样表述:“先验的不是指我们的认识对物的关系说的,而仅仅是指我们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说的。”[25]在康德看来,正是先验的知识存在才使得我们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成为可能[26]。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规则(principles of universal grammar)正是设定了这一先天知识结构的存在。由于康德主张从人的角度来理解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他对知识的追求“囿于心理主义的层面”,这是康德的时代局限性使然。于是,乔姆斯基对先验逻辑进行自然科学式的改造,在应该提出假说的地方不作论断,从而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1969年,蒯因在 《自然化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Naturalized)中通过对观察句进行定义,构建了以观察语句为基础的行为主义认知论模式,为知识和真理的正当性提供了直接的证实依据。乔姆斯基以其对语言与心智的研究为基础,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蒯因的自然认识论提出了批判,旨在全面修正并超越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27]。乔姆斯基认为,蒯因的认识论缺乏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使理论与自然科学分道扬镳,否定了认识论作为人类知识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尽管乔姆斯基反对传统唯理主义认识论,唯理主义依然是乔姆斯基语言观主要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乔姆斯基认同语言具有物种属性(species character),将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看作是漫长的生物化过程的结果,走向了自然化的理性主义方向[28]。可以说,乔姆斯基肯定了认识论对人类知识的积极指导作用,复兴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科学部分。
四、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扬弃
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它涉及人们用什么方式和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涉及对一系列具体方法如何进行分析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乔姆斯基的方法论思想离不开前人对他的影响,批判地继承是他能够开创和探索新方法论的法宝。
(一)对皮尔士“溯因推理”思想和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思想的扬弃
皮尔士(Peirce)在继归纳(induction)和演绎(deduction)两种推理形式之后,首次提出“溯因推理”(abduction)①此处选用陈波和陈保平的译名。“Abduction”的其他中文译名有:“不明推论式”(熊仲儒,张孝荣)、“不明推论”(丁尔苏)、“直觉推理”(熊学亮)、“外展推理”(徐向东)、“假设推理”(江天骥)和“估推”(沈家煊)等。,其实质是猜测本能(guessing instinct)。归纳只是确定某种量值,演绎只能从纯粹假说推论出必然结论,而“溯因推理”是形成解释性假设的过程,他认为,只有“溯因推理”能够产生新知识,而且是获得新知的唯一道路[29]。乔姆斯基早在《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一书中对“溯因推理”进行过论述。他曾坦言自己“几乎是皮尔士的释义者”[30]。他将“溯因推理”解释为心智基于某一原则形成一些假设,并根据证据或某些事实在假设中作出选择的过程[31]。他以“溯因推理”为基础,认为语言习得同它一样都面临着刺激缺乏的问题。他还借鉴了皮尔士理念中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将其理论称为假说(hypothesis),从而确定了“假说-验证”这一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路线。
20世纪上半叶,叶姆斯列夫(Hjelmslev)在他的《语言理论导论》(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中提出“语符学”理论,推崇演绎法。他认为,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演绎地建立语言系统,真正的语言学必须是演绎的②参见:万琼.叶姆斯列夫和乔姆斯基的演绎法对比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29-131.,理论本身完全独立于任何经验,是一个纯粹演绎的系统,只有将语言学与数理逻辑紧密结合才能做到精确科学地坚持语言的演绎研究。乔姆斯基反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推崇的归纳法,认为其研究工作从实地调查(field work)开始,不可能完整地描写语言,倡导用演绎法建立生成语法规则系统[32]。于是,演绎法得到了新的发展。可见,生成语言学历来强调唯理论的演绎法胜于经验论的归纳法在语言认识论中所起的作用[33]。虽然乔姆斯基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叶姆斯列夫的演绎思想,但并非狭义的继承,更非一脉相承[34]。乔姆斯基对叶姆斯列夫演绎思想的扬弃也体现了其不迷信前人和超越前人的科学精神。
(二)对“伽利略-牛顿主义”的扬弃
“伽利略-牛顿主义”指西方科学发展史上伽利略和牛顿两位科学巨匠的研究思想、研究行为或作风以及他们在科学事实与理论建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5]。两位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其中包括理想化、抽象化和无视反例等[36]。
乔姆斯基坚信语言是大自然的完美产物,是一个完美的系统(perfect system),是人类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中接近完美无缺的产品。他在《句法理论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③此处选用刘润清的译名。该书的其他中文译名有:《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林书武,沈家煊)、《句法理论面面观》(石定栩)和《句法理论诸方面》(胡朋志)等。一书中写道:“语言理论关心的是生活在同质的语言社区中的理想语言交际者,他们完全掌握了自己语言社区的语言。”[37]不过,乔姆斯基其实并不否认对语言学其他相关要素研究的必要性。出于认识事实本质、尤其是认识语言官能这一人体器官的生理本质的需要,将语言研究对象相对独立并理想化可能是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后期,乔姆斯基在最简主义思想的驱动下提出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体现了乔姆斯基建构完美理论的科学精神。可见,乔姆斯基对研究方法、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三方面的理想化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体现了对“伽利略-牛顿主义”风格在语言层面的继承和创新。另外,抽象化研究方法的关键是理论构建方法的形式化[38]。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研究中,各种符号、公式、字母和图形等充斥其中,随处可见,可以说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描写和演算过程的抽象化。正如伽利略无视大量事实论据的存在一样,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也无视了很多语言学现象中的反例。乔姆斯基赞成“伽利略-牛顿式”研究得到的理论,不被现象引入歧途,因为他认为世界原本与常识感觉并不一致[39]。
(三)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扬弃
美国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或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是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和萨丕尔(Sapir)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印第安人土著语言,通过有效地记录没有文字的语言而诞生的。1921年,萨丕尔在其著作《语言论》(Language)中描写了美洲印第安语的种种事实,这种对语言事实的尊重精神,是“留给以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遗产之一”[40]。十二年后,布龙菲尔德的同名著作《语言论》(Language)出版发行。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描写方法,勾勒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总体理论框架,标志着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正式诞生。1951年,哈里斯(Harris)出版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 》(Methodsin StructuralLinguistics)。纽 曼(Newman)认为它是“继布氏《语言论》之后,对描写语言学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一本‘巨著’”[41],这“标志着美国结构主义达到了它的成熟期”[42]。该书把“分布关系的逻辑”作为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并建立了一整套描写语言学的严密技术[43]。乔姆斯基作为哈里斯的学生,必然在研究方法上受到老师的影响,如注重形式分析等,甚至转换(transformation)一词就直接来自他的老师。还有,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其实正是为了描写语感[44]。
描写语言学虽为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制定了一套严格、精确的程序和方法,但缺乏对语言现象和人的语言能力进行解释的能力[45],而解释力大小是衡量语言理论的主要标准。乔姆斯基说过:“以解释的充分性为目标的语言结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语言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的解释。 ”[46]因此,他的生成语法试图解释语感,强调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对语言现象进行充分而又合理的解释。乔姆斯基尽管从1957年的《句法结构》到1995年的《最简方案》频繁地修改其语法模式,但他揭示人类语言中普遍创造型原则的理论目标没有改变,为语法赋予的解释性使命也没有改变[47]。语言理论的解释充分性明确了生成语法的语言哲学理论,也确立了其理论的追求,从而推动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进程。乔姆斯基认为,“最简单性研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重新审视以前理论模式中所有那些用于描写和解释语言特征的规则、原则和其他理论构件,努力代之以界面条件和一般性运算特征的解释[48]。可以说,他通过创建原则与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的理论框架,提供了解决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和解释的充分性之间矛盾问题的希望,首次开创了由显著地超越解释充分性达到原则性解释的现实性前景[49]。因此,乔姆斯基不但对美国描写语言学实现了扬弃,也超越了自己所提出的解释的充分性原则。
可见,乔姆斯基“假说-验证”的自然科学研究路线、构建理想化的科学理论以及追求对语言理论的“描写和解释的充分性”原则,无不体现着他贯穿始终的“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科学精神。
五、结语
本文从众多思想、流派和人物中选取相关代表来阐述其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并逐一分析乔姆斯基对他们的扬弃,以期梳理出其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方面的发展脉络。正如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的[50],任何一位伟大人物也都是在继承和创新中成长的,因为学问之道应该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革新的[51]。乔姆斯基的理论正是以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为基础[52],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乔姆斯基的批判并非对某个人观点或哲学思想的批判,而是对前人不合理因素的集体批判,并非对前人某个观点或哲学思想的继承,而是对前人合理因素的综合继承和发展,从而最终提出自己的科学独创之见。换言之,乔姆斯基继承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传统与这个传统承继过程中的普遍合理性[53],是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的批判、继承、发展与创新。总之,乔姆斯基突破常规、勇于批判、不断创新的精神和不畏权威、敢于挑战、否定自我的魄力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正如陆俭明所言:“乔姆斯基的思想值得从事语言研究的人重视和琢磨。”①参见:石定栩.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新理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1-4.本书由陆俭明作序。(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