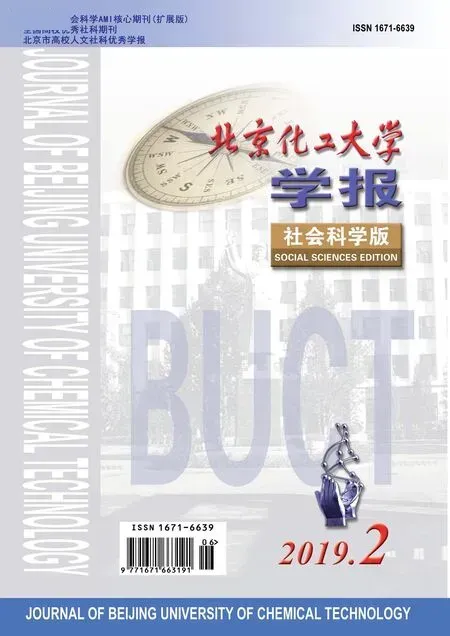论王安石文章的美学风格
刘洋
(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北京100081)
清代桐城派古文名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把中国古代的文章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1]。这种文体分类的方法虽然和现代的文体分类有些差别,但便于古代文章的研究,本文就沿用姚鼐的文体分类方法来研究王安石的文章。现存王安石的文集,目前最好的版本当属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出版的 《临川先生文集》,此文集以嘉靖三十九年(1560)抚州何迁翻刻南宋抚州知州詹大和1140年刻印的《临川先生文集》本为底本,参照铁琴铜剑楼藏南宋绍兴刊本等补校,每卷之末附有校记,并有岛田翰(日本)、陆心源、朱祖谋、唐圭璋诸人辑佚的诗、文、词合为一卷,名《临川集补遗》,附在文集最后,作为附录,本文即以这一版本为据。《临川先生文集》正文目录第一至第三十四卷皆为诗,第三十五卷为挽辞,第三十六卷为集句诗,第三十七卷为集句诗和词,第三十八卷为四言诗、古赋、乐章、上梁文、铭和赞,第三十九卷为书疏,第四十卷为奏状,第四十一至四十四卷为劄子,第四十五至四十八卷为内制(包含册文、表、青词、密词、祝文、斋文、诏书、口宣等),第四十九至五十五卷为外制,第五十六至六十一卷为表,第六十二至六十九卷为论议,第七十卷为论议和杂著,第七十一卷为杂著,第七十二至七十八卷为书,第七十九至八十一卷为启,第八十二至八十三卷为记,第八十四卷为序,第八十五卷为祭文,第八十六卷为祭文和哀辞,第八十七至八十九卷为神道碑,第九十卷为行状和墓表,第九十一至一百卷为墓志。从《临川先生文集》的卷次目录和上举清代姚鼐的文体分类名称比较来看,从宋代到清代,除了个别文体的名称有些出入外,中国古代文章的文体变化不大。王安石现今留传下来的文章有1500多篇,大致包括了中国古文的各种文体。不同文体的写作方法和美学风格不尽相同,本文拟对王安石有代表性的文章风格加以探讨。
一、书信之文有刚劲峭折之美
王安石的书信之文以刚劲峭折的美学风格见胜,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2]。
熙宁三年(1070),正当变法在激烈斗争中推行时,司马光接连三次写信给王安石,要求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司马光的第一封信写于这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全文长达三千多字。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新法,是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派遣官员到各地去推行新法是惹事生非;“青苗法”等新法只是征敛财富的手段;拒不接受反对派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四大罪状。王安石接到这封信后,只是略作回答,未与之辩论。司马光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王安石这才写了这封回信。对于司马光的数千言,王安石仅以359字作答。书信第一段,开头措辞很有礼貌,“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接下来笔锋一转,“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指明了和司马光矛盾的关键所在,是治国方略、治国之术的不同,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自己的立场。接下来又客套了两句,但软中带刚,柔中见硬,为下段驳论作铺垫。第二段和第三段是书信的正文。书信第二段为驳论部分,开头即刚健有力,引用儒家的话语辩明名实关系,表明变法师出有名。然后逐一批驳司马光指出的四大罪状,文风峭折,文笔犀利。每条驳论虽只是寥寥数语,却能击中要害,使人感到气足神完,义正词严。书信第三段对“天下怨诽”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士大夫们因循苟且、不愿改革、同俗自媚于众是其根源,并以“盘庚迁都”作比,表明了改革是“度义而后动”,是合乎道义的,是高瞻远瞩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长远发展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不同流俗、不畏人言、坚持己见的精神。书信最后声明,只接受“未能助上大有为”,不能接受“一切不事事”,实是进一步有力地回击,表现出推行变法的决心和无所畏惧的气概。文章结构谨严,语言简练犀利,刘熙载尝评此文说:“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两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3]这封书信理足气壮,全文洋溢着“刚劲峭折”之美,为千古名篇。
又如《答曾公立书》: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兴,邪人不利,一兴异论,群聋和之,意不在于法也。
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粜,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奸人者因名实之近,而欲乱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之怨何?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
公立更与深于道者论之,则某之所论无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哓哓者,不足言也。因书示及,以为如何[4]?
本文是王安石继《答司马谏议书》之后对“反变法派”的又一次反击。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朝廷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推行“青苗法”,但受到一些大臣的抵制,本文则是王安石反驳曾伉而写的一封回信。在封建时代,有人爱标榜儒家的“仁义”,非难某些经济革新措施,认为是“图利”,王安石这封信开门见山,只就青苗法立论,有针对性地强调“理财乃所谓义也”。孟子所说的“利”,是指有利于国家的利益,理财和儒家仁义虽然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但作者侧重从抑制兼并、从改变“狗彘食人食”和“野有饿莩”的社会现象的方面,来阐明推行“青苗法”的意义,让人感到这种“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确实符合“仁义”的精神。“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王安石信中一再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理念,并且重点向曾伉解释说一定要收取二分利息是为了能够长久推行“青苗法”,是有利于百姓生活和国家运转的长久之策。全文颇有气势,给“青苗法”找到了理论根据,驳论充分,遒劲有力。
王安石这样的书信还有很多,如,《与刘原父书》既对开河之举的劳人费财、无果而终表示愧疚,又含蓄地批评了士大夫中因循苟且的风气;《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二》中,王安石先写了一封邀请信,请杜醇到县学教书,杜醇引用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和柳宗元“不敢为人师”来推辞,于是,王安石又写了第二封信,对杜醇的观点一一驳斥,希望杜醇不要顾忌世人的诽谤或赞誉,而秉承“适于义而已”的信念,以培养后进为责任,去县学担任老师;《上田正言书》开篇先宣称田况“介然立朝,无所跛倚”,然后回顾田况当年在对贤良方正策时敢于直言,无视名利,进而批评现在的田况虽然身为谏官,反而不进一言,有违初衷,最后向田况提出了“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疵,蹇蹇一心,如对策时”[5]的要求与希望。以上诸篇,皆理直气胜,义正辞严,刚劲峭折。
二、奏议之文有雅正庄重之美
奏议之文是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条议是非的文字的统称,有时也包含官员向比自己官职大的上级上的条陈。王安石的奏议之文论理充分,言之有据,具有雅正庄重的特点。
如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全文洋洋洒洒,长达万言,是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任三司度支判官时上给宋仁宗的奏疏。文章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了当时国家内外交困、风俗败坏的现状:“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6]王安石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不懂得建立法度,而当时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大多数都不符合古代先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必须效法上古三代的治国精神,进行变法革新。他强调指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人才问题:“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7]接着人才问题,王安石又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8]接下来文章围绕陶冶人才这一中心,逐次展开,系统阐明为革除种种弊端应采取的具体措施。这篇文章表明了王安石执政变法的总体纲领已基本形成,他登上相位后,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进行改革的。全文结构经穿纬织,条分缕析,行文雅正畅达,有条不紊,说理引经据典,纵贯古今,是长篇政论文中的典范。梁启超评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9],明代茅坤评此文说:“此书几万余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而钩考部曲,无一不贯。”[10]
又如《上时政疏》: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已困穷,天下之民固已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浇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徼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11]?
本文是王安石在嘉祐六年(1061)任知制诰时所作。全篇章法谨严,颇见法度。文章首先引述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这三位历史上著名的君主在位时享国日久、不思进取,最终导致危机甚至有的丧失政权的史实,进而加以分析,得出因循守旧必然招致危亡的结论。接着,文章借古喻今,将宋仁宗时代的社会状况与这三位皇帝的时代加以比较,揭露了当时在太平景象下掩盖的深重政治危机,希望给仁宗敲起警钟。最后,文章再次强调了进行以“大明法度,众建贤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的必要性。全文以史论今,结构完整,雅正庄重,掷地有声,词简意深。
王安石奏议之文中体现这种风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进戒疏》警戒刚即位才一年的神宗,只有“不淫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才能“精于用志”,然后才能“明于见理”、“知人”和“疏远佞人”,最后才能达到“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的盛世;《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首先叙述并解释了从宋太祖至宋英宗这百余年间国内太平无事的情况和原因,接着全面剖析了宋仁宗在位时政治措施的得与失,最后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在太平景象掩盖下的社会危机,从而论述了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上五事札子》向宋神宗汇报了五项改革措施的施行情况,其中“和戎”“青苗”二法已初见成效,而免役、保甲、市易三法,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12]以上诸篇都议论恳切,郑重醇厚,体现了王安石一心报国、一片赤诚、忠心为主的真情,也体现了他渴望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和壮志。
三、杂记之文有哲思逸兴之美
杂记之文,包罗最广,或描摹祠宇亭台、登山涉水之景,或记载宦情隐逸、遗闻轶事之迹,或记载读书览史、品评人物之感,皆可称之为“杂记”。
王安石的杂记之文,总是能发前人所未发,蕴含哲理,如《游褒禅山记》。此文是王安石同几位亲朋游览褒禅山后所写的游记。文章前半部分记事,写褒禅山各种异名的来源和游后洞半途而废的经过。后半部分展开议论: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13]。
王安石通过观山揽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世上奇伟瑰怪的风景,常在险远而人迹罕至之地,想要游览这些风景要具备有志向、体力、不随便怠惰、有物以相之等各种条件,人生路上想要成就大事亦同此理。同时,王安石还因为看到路边碑文漫灭,联想到很多古书散佚不存,而后世谬传,提醒学者深思而慎取之。本文以游记的形式,寄托人生哲理,是宋代游记散文的名篇。明代茅坤评此文“逸兴满眼而余音不绝”[14],正指出了本文令人回味无穷的思想深度和哲理之美。
又如《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15]!
本文是王安石在庆历三年(1043)回临川故乡或其后不久时所作。方仲永五岁时未曾读书识字,却能写诗,号称“神童”。可是他的父亲为了牟利,终日让他拜见他人,却不让他加强后天的学习,以至于他十四五岁时“泯然众人矣”。于是,王安石非常有感触:方仲永有受之于天的通悟,却因后天不学习而成为众人,如今天生普通的人们,再不加强后天的学习,恐怕会连众人都不如。王安石在文章中阐明了他的学习观点: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学习是成才的关键,比天赋更重要。本文先叙事,后议论,由感性到理性,叙议结合,因事言理,事理统一,蕴含哲理逸兴之美。
再如《龙赋》:
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惟不可见,所以莫知其向;惟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则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为仁。为仁无止,则常至乎丧己;而未始至乎丧己,夫此所以为智。止则身安,曰惟知几;动则物利,曰惟知时。然则龙终不可见乎?曰:与为类者常见之[16]。
这篇小赋借龙喻人,托物言志。全文通过描述龙能显能隐、不能驯服的性格和为仁为智、知几知时的能力,赞颂了一个知时利物、识见超卓的非凡人物,寄托了作者宏大的胸怀。通篇用隐喻手法,寓意让读者体味,是一篇富有哲理之美的短文。
王安石的杂记之文名作很多,如,《芝阁记》通过比较真宗仁宗两朝对灵芝的不同态度,抒发了士之贵贱与机遇有关的感慨;《石门亭记》通过记述石门亭修建的由来,提出了“好山,仁也……求民之疾忧,亦仁也……成人知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17]的高远观点;《扬州龙兴讲院记》通过对高僧慧礼以一己之力修建成一所佛寺的事迹的记述,赞颂了慧礼高洁坚韧的品行,并慨叹儒门当中可以像慧礼这样吃苦耐劳、守道不苟的君子越来越少了;《送陈兴之序》借兴之的仕途坎坷不顺发出了“悲大公之道不行焉”[18]的慨叹;《读孟尝君传》一反古人对孟尝君的评论,提出了孟尝君只是依靠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根本算不上“得士”的见解;《读柳宗元传》借八司马屡遭贬谪尚能自强求列名于后世,为失意者鸣不平,并嘲讽了当时那些有始无终、与世俯仰的所谓君子;《知人》篇引用王莽、隋炀帝、郑注的历史故事,说明奸佞之人善于伪装,以假象迷惑别人,从而论证知人知难的道理;《兴贤》篇运用史实,从商周两汉到唐朝,指出“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19],阐明国君只有选贤任能才能实现三代之治。以上诸篇,皆论述精警,颇有见识,蕴含哲理之美。
四、结语
王安石的书信之文有刚劲峭折之美,表现出他卓然自立的鲜明个性;奏议之文有雅正庄重之美,表现出他变法图强的雄心壮志;杂记之文有哲思逸兴之美,表现出他读书广博又能独抒己意的高远见识。如果要作进一步概括的话,王安石的文章具有的主体美学风格应是“刚劲峭折的阳刚之美”。
姚鼐在《复鲁絜非》一文中谈到:
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20]。
应该说,王安石文章的“刚劲峭折的阳刚之美”是符合姚鼐所说的“阳与刚之美”的基本特征的。钱基博先生也曾经评论王安石的文章说:“……笔力天纵,以折为峭,特峻而曲,辞简而意无不到,格峻而笔能使转,愈峭紧,愈顿挫。”[21]钱先生对王安石文风的评价是比较精准的。
王安石文章的阳刚之美来源于他对儒家经学尤其是《孟子》的学习和继承,来源于他对韩愈文章的学习和借鉴,再加上自己的改造和实践,不懈地刻苦努力,最终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当然,王安石的文风和他襟怀坦白、高瞻远瞩、淡泊名利、率直刚强的人格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应该说,刚劲峭折的阳刚之美是王安石文章的主体风格,但雅正庄重和哲思逸兴与刚劲峭折是有一定关系的。由于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行文特点,例如奏议之文往往是写给皇帝或自己的上级的,就不宜行文太过刚硬,需要适当温和庄重一点,所以王安石的刚劲峭折一变而为雅正庄重。又如杂记之文多为随笔、杂感、游记,包含较广,可以随意抒发,侃侃而谈,也不必过于刚硬,所以刚劲峭折一变而为哲思逸兴的风格。不过,王安石的哲思往往是斩钉截铁,议论精警,王安石的逸兴往往是意气风发,元气充沛,也能体现出他行文刚劲沉雄的一面。总之,王安石的文章以刚劲峭折的文风为主,以雅正庄重和哲思逸兴的文风为辅。王安石的文章简洁有力,刚劲峭折,充满了阳刚之美,足以成为我们后人学习作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