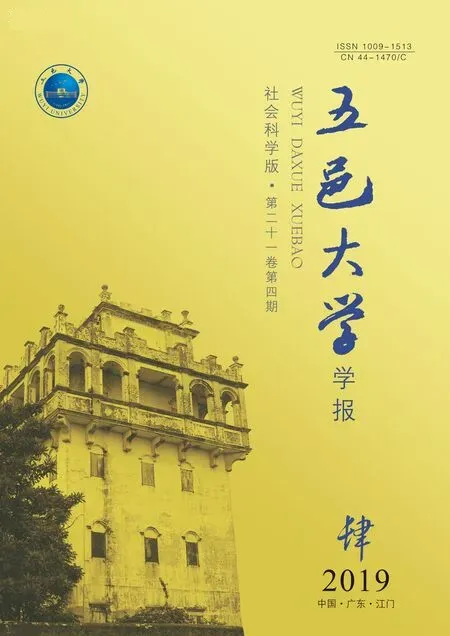“会通中西”视野下的戴学:论梁启超的戴学研究①
陈小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戴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与西方的涌进似乎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戴学在近代之所以引起诸多大家的关注,与其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亲缘性有重要关系。这些戴学研究者想借助对戴学的研究与褒扬来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衔接,以会通中西文明。本文以近代戴学的重要提倡者梁启超的戴学研究为例,来说明此一过程。
一直以来梁启超关于戴学的研究一直被研究者放置于清学的大脉络中予以关注,很少对其进行单独研究,且研究者的视线始终关注的是1920年代梁启超的戴学研究,并突出梁启超在戴震的方法论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间所做的沟通,①这一理解的缺陷在于对梁启超的戴学研究中突出戴震伦理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契合性这一面挖掘不够,另外由于不注重梁启超前期的戴震研究,而忽略了梁启超对戴震哲学思想评价出现的转变,进而不能很好把握到梁启超研究戴学背后的目的。
梁启超对戴震学说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丛报》时期,《近世之学术》一文为此一时期他研究戴震思想的代表作,但此段时间的梁启超对戴震思想评价并不高;第二阶段为1920年代,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分别撰写有《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以及《戴震的哲学》、《戴东原先生传》与《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在其中他关于戴震的评价明显转变许多,大赞戴震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精神,还认为戴震的哲学“欲为中国文化转一大方向”。两次研究评价转变的背后是梁启超发现了戴震学说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可相通性,他想借助对戴学的研究与提倡来沟通中西文化,以转化中国传统文化。
一、《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戴学研究
《近世之学术》一文可算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据其自述,约于1902年动笔,而刊于1904年的《新民丛报》。此时的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在经历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后,他转而以培育现代之国民为己任,此一时期创办的《新民丛报》正是基于培养“新民”的目的。
《近世之学术》是一篇简洁叙述清代学术源流的文章,所以其中对于清代学者思想的阐释都不甚详细。梁启超以乾嘉之学为清学之主干,认为乾嘉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做学问的标准,可与西方科学精神相通,二者相似之处在他看来有四点:一是善于怀疑而有求真的精神;二是喜欢穷根究底探寻事物的条理来帮助自己的证明;三是其学术能“如一有机体”一样,前后相续成长;四是“善用比较法”;[1]609-610他认为这四点是促使近代西方科学兴盛的缘由,而清代考据学具备这四种精神。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现代社会的分工来看待清代考据学的特征,认为清代考据学者的治经有专业化的特点。从以上可知,梁启超在极力拉近清代考据学与现代社会的距离。西方文明最吸引梁启超的莫过于科学文明,科学对于国家富强的推动作用与其背后的理性精神深深吸引了梁启超,而引入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也是他启蒙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从这一点看,他其实比后来在五四时期声名鹊起的一批启蒙学者更早在大众中提倡科学的重要性。
而谈到近世西方之所以有大进展,其动力在梁启超看来是由于培根所创立的归纳法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创下来的演绎法传统,以为对事情的论证必经历多次实验无误才能确认其结论,而没有以前先悬设一理作为论证前提所造成的武断论证毛病。梁启超对西方兴盛富强的原因分析是较简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西方了解程度的有限,另一方面在于这种简单的框架分析有利于梁启超将它与清代考据学精神结合起来。他认为清代考据学一反宋学谈虚、陷入空想的弊端,而求客观之研究,此种反动,与西方近世文艺复兴以后,以培根的经验归纳法纠正以前神学的玄思默想求学方法很类似,因而梁启超以“中国的文艺复兴”[2]3069来比附清代研究方法与宋明理学的差异。虽都以归纳法为研究方法,但东、西方社会却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西方以有归纳法而走向富强高效的现代文明国家,中国却因考据学而日益走向消沉,这其中缘由在梁启超看来是由于二者研究方法使用范围的宽窄所致。清代考据学仅将其研究方法用于琐细的经文考证,学者的研究可说是变得相当精细且专业化,但同时他们的精力日益耗散于此种细致的考证中,以致学术变得支离琐碎,匮乏思想。由此,梁启超虽对清学研究方法十分赞同,但认为由于清代学者对此种方法途径的误用,使得这二百多年来优秀的脑筋都用于故纸堆里的考证,成为避开政治、明哲保身的手段,而道德感也日益退化。梁启超因而对其批评甚多,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整体上对清学评价不高。
在《近世之学术》一文中,对戴震的学术方面,梁启超首先承认其在考证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范围涉及经史、历算、舆地、天文等。他注意到戴震求学的方法是“由字以通经”,并将戴震看作乾嘉学者中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1]613的第一人。但这里梁启超只是提到求学,并未说到“求道”,可见此时的他并未真深入了解戴震的治经方法。但戴震所谓“由字以通经”的方法,其目标显然是为获得“道”,这是清代治经学的学者的普遍看法,考据只是为还原经文本义的手段,而其终极目的是为获得经中的义理。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戴震的两本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中“体情遂欲”的思想类似西方的乐利主义。但他对于戴震这一强调人之“情欲”满足的观点评价很低,认为这是“教猿升木”[1]613,多此一举。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戴震应为近二百年的学者道德感沦丧负责任。
那么为何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对戴震哲学评价不高呢?首先,从内容上看,《近世之学术》一文中的观点深受章太炎清学研究的影响,周予同便认为梁启超清学研究中的许多观点来源于章太炎的《清儒》一文,[3]这点梁启超本人也不避讳。我们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其实并未对戴震哲学有深入了解,其观点多受章太炎影响。章太炎对戴震考据学的成就予以褒扬,但对其哲学思想评价不高,尤其对戴震批评佛老思想这一部分意见最大。②梁启超在未深入研究戴震哲学的情形下,自然易受章太炎观点的影响,而对戴震思想评价不高。其次,从思想倾向上看,梁启超受康有为影响而推崇传统的陆王心学,他曾于1891至1897年于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授传统学术,并表示在万木草堂时期的听学是自己“一生学术和事业的大基础”[4]。受其影响,在德性问题上,梁启超对以格物致知之法来解决德性问题的朱熹表示不满,认为“智育”的方法不能用于“德育”。由此我们可知,这一时期还笼罩于康有为思想影响下的梁启超对戴震以智性建立道德的方法并不满意。
总的来说,《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戴学并未深入了解,其研究多受章太炎观点所影响,而对戴震的评价不高;另一方面由于他将清代考据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比附于西方培根的归纳法,开启了对考据学内在精神与西方科学精神间关系的论述,而戴震是清代考据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关于戴学与西方科学文明的沟通问题由此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二、1920年代梁启超的戴学研究
在经历政治上的起落之后,梁启超“弃政从学”,后期转而专注于学术研究,1920年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在其中他关于戴震的评价明显转变许多,不仅大赞戴震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精神,还认为戴震的哲学作品《孟子字义疏证》“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2]3081,可谓评价甚高。到1923年,梁启超发起“戴震生日二百年纪念会”,分别为此次纪念会写了《戴震的哲学》《戴东原先生传》《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将其对戴震的研究推向高潮,此时梁启超对于戴震的认识更加细致与深入。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近代研究清学史的典范之作,他自叙该文原是为蒋方震的著作《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所写的序言,不料下笔后不能自已,写成几万字的长篇文章,于是便又独立改成一书出版。在序言里,他自称该书与自己十八年前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清代学术部分根本观点无大差异。[1]613诚然,《清代学术概论》继承并细化了不少梁启超十八年前的观点,如书中对于清代各学派间的划分与传承基本延续了前期看法,将这二百多年学术思潮的意义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提出清学缘于宋明理学之反动的观点,这一说法在十八年前的《近世之学术》一文里还处于模糊状态;另外,清代乾嘉之学具有科学精神这一观点在该书中得到强化,此时科学精神可说是贯穿该书的主轴。但细究起来,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明显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以戴震为首清代考据学派的评价明显提高许多,前期对于清代考据学陷入琐碎研究,并导致当时知识分子消沉、荒废德性的批评在此书中已不再见,增加的是对于清代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科学精神相通的褒扬。
其次,梁启超对于戴震的评价明显改变许多,不仅表彰他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精神,还对其哲学思想评价甚高,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字字珠玑”,其中内容可概括为戴震欲建立一种“情感哲学”,以替代宋明的“理性哲学”,并将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潮联系起来,认为戴震建立的“情感哲学”与欧洲近代反“禁欲主义”的意义相似,其结果是“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2]3081-3084这样戴震哲学在梁启超眼中还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
再次,梁启超对于乾嘉时期吴派与皖派间的关系与评价有所转变,《近世之学运》中梁启超认为戴震曾受学于惠栋,所以二者可算同源,此时的他更强调两派间的联系,而非差异。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他则更刻意凸显二派间学术风格上的差异。从评价上来说,他是批判吴派,褒扬皖派。他以八字总结吴派的治学方法,即“凡古必真,凡汉皆好”[2]3080,凡汉儒所说的便都是对的,不能加以指责,愈靠近古代,便愈接近真理,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一种“盲从”“偏狭”的治学态度,这样的治学是排除批判与怀疑精神。与此相对的是皖派,对于二派间的差异,梁启超沿用了章太炎的说法,认为吴派之学的特征是淹博,而皖学的特征是精深且注重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清儒》中,章太炎对于这两派间的差异只是简捷地点出,梁启超却在这里对于这二者间的差异做了更多延展性说明。他将戴学的治学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联系起来,考证学“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成了现代科学的“求真”精神。对梁启超而言,只有具有“求是”精神的戴派才是“清学”,吴派只能称为“汉学”。
综上可知,与十八年前的《近世之学术》相比,《清代学术概论》更加凸显清代乾嘉之学具有科学精神这一观点。
1923年是戴震诞辰200周年,该年10月梁启超发起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并撰写多篇有关戴震的研究文章。在其撰写的《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中,梁启超将戴东原与朱熹、王阳明并列,认为戴东原在哲学史上的位置与价值值得为其隆重举行一回纪念会。就具体内容来说,他认为戴震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两部分是他的研究法与情感哲学,这两点基本是延续《清代学术概论》中戴震部分的观点。梁启超认为戴震的研究法可概括为“‘去蔽’与‘求是’两大主义”[5],认为这两点“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5],在戴震的著作中正是渗透着这种带有科学精神的研究法。他叹息过去此种研究法只被用于考证经文,今后则应该扩展到各门科学的研究中。显然,梁启超这里乐观地认为清代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之间的相通是不成问题的,他并未深刻理解到二者间的差异。而对于情感哲学,则主要在他写的《戴东原哲学》一文中得到阐发。梁启超将戴震的哲学视为一种情感哲学,所以其阐发戴震哲学的内容侧重从这一角度展开。他认为情感哲学的提出是戴震对于以前宋明理学倡导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戴震以前的学者的反动工作基本上是一种破坏工作,戴震则有一种建设的活动。而梁启超如何将戴震的情感哲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沟通,将在下节予以说明。
总之,相较《新民丛报》时期的戴学研究,梁启超在1920年代对于戴学的研究明显深入许多,对其评价明显也明显改善,并夸赞其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当时,科学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梁启超极力彰显戴学中的科学精神其实也是挖掘传统中的合理资源来实现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
三、“会通中西”与梁启超的戴学研究
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中,梁启超将戴学内容划分为两项,一是戴震的研究方法,一是戴震的情感哲学。在梁启超整个戴学研究中,他都是遵循这一划分法来展开研究。他认为戴震的考据研究方法具有客观认知精神,因而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通,而戴震的哲学内容,则是戴震“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2]3082,他把这种“戴氏哲学”概括为一种“情感哲学”,认为它可与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相通。
关于戴震的研究方法,梁启超曾以“去蔽”与“求是”两方面来概括,“去蔽”则应做到既“不为人蔽己”,又“不以己自蔽”,③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梁启超最后还是将其方法归结到“求是”上面。“实事求是”被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具体而言是清代戴派的治学精神,其治学精神有与西方科学精神相通之处。
梁启超举出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来说明他的方法如何与西方科学方法相通。所谓“十分之见”指要证明自己的观点为正确,必须使得自己考证的每一字、每一观点都符合古代经书中发现的各种证据,在各种经书中反复参证,而没有任何疑问,才能算是“十分之见”。在梁启超看来,这是一种十分严谨而又客观的治学过程,几乎就是西方科学家为求得某一定理而必须对其开始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严格验证的过程。
梁启超又在论及戴门后学的研究法时,对戴震的这一研究法进行了细致说明。他将这一研究法分为六部分,第一是“注意”,第二是“虚己”,第三是“立说”,第四是“搜证”,第五是“断案”,第六是“推论”。[2]3085这显然是受当时胡适所提倡而风行中国的“实验主义”方法的影响。胡适将杜威的思想方法概括为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出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假设的谬误,使人不信用。”[6]梁启超总结的戴派研究法的六个步骤除第二点“虚心”在胡适所说的“实验主义”方法中没提到外,其余五点几乎是一致的。五四时期,经过胡适等人对“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大力宣扬,“科学”观念已深入人心,梁启超在此风潮中也不免受影响。但当时所提倡的科学观念与方法不止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一种,还有马克思主义代表陈独秀所提倡的“科学观”,郭颖颐将其称之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观,而胡适所说的“实验主义”方法可归之为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观”,相较而言,“经验主义”的科学观比“唯物论唯科学主义略少一些教条气息”[7]。从梁启超早期对于科学的认识来看,他将西方科学的兴起归之为培根所创立的经验归纳法,并认为清代的考据学近似于西方的经验归纳法,因而与西方科学精神是相通的。而胡适所总结的杜威的思想方法是以杜威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在科学观念上的经验主义倾向使得梁启超容易接受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他对于戴派研究方法的总结也受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很大影响,其用以嫁接清代考据学与西方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
关于戴震的哲学内容,梁启超以“情感哲学”来概括,而在早期的《近世之学术》一文里,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近似西方的“乐利主义”,但此时梁启超并不欣赏戴震的“乐利主义”。1920年代,梁启超以“情感哲学”来代替“乐利主义”来概括戴震的哲学,高度赞扬“情感哲学”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转变,这种评价上的转变主要缘于此时梁启超对戴震哲学理解的深入。在未深入了解戴震哲学时,梁启超将其道德主张仅仅归结为一种对人欲望的满足的尊重,这就有了梁启超对戴震“教猱升木”的讥讽。但在1920年代,梁启超则对于戴震哲学内容有了细致了解。在《戴东原哲学》一文里,梁启超的研究表明他把握到戴震的哲学虽追求对人“情欲”的满足,但对只注意满足个人欲望而影响他人欲望满足的自私行为批评得厉害,戴震所关注的是天下人的情欲得到均衡满足,这与梁启超所欣赏的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8]的功利主义一致。这其中也反映了梁启超要借戴震的情感哲学来会通西方的功利主义的目的。
梁启超将戴震的“情感哲学”概括为五方面,分别是“客观的理义与主观的意见”[9]4193、“情欲主义”[9]4194、“性的一元与二元”[9]4195、“命定与自由意志”[9]4197与“修养实践”[9]4198。由前四部分处理的内容的共同线索来看,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主要破除宋儒的二元结构而回到一元论,“主观意见”的产生源于理与事物的二分结构,性的二元论源于“天理”与“气质”的二分结构,由此导致“理”与“欲”的二分结构与紧张关系,惟有消除此种二分结构回到一元论才能使得天下人都能“体情遂欲”。古典的严肃道德哲学倾向于将代表人“情欲”的形体与超越的形上世界对立,并由此导致道德哲学的禁欲特征。而西方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多用一元论来反对传统道德哲学的二元论,梁启超对戴震道德哲学中一元论的挖掘,也意味着从中他发现了戴学可与西方现代文明沟通的新资源。
另外,可以发现此种批判二元论而回归一元论的思路与王阳明心学的建构路径很类似,而梁启超自接触陆王心学思想起,便一生服膺心学,由此可理解梁启超对戴震哲学高度评价的另一层思想缘由。由梁启超所概括的戴震情感哲学的第四点“命定与自由意志”,我们更能看清这一点,“自由意志”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关键概念,梁启超曾写过《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来向国内人介绍康德的思想,在其中他以王阳明的“良知”来比附康德的“自由意志”,认为“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10],在他看来,二者都强调人的“真我”的独立与自作主宰。由此可知,梁启超所了解的戴震哲学与王学有亲近性,当然,这种亲近也并非梁启超的主观比附,戴震哲学是通过对儒家经典《孟子》文本的阐发而展现出来,而阳明也凸显自己的哲学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对于《孟子》文本的共同关注是二者具有契合性的基础。
但总的来看,梁启超对戴震“情感哲学”的研究与提倡,其主要意图在于与西方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进行沟通。
综上,梁启超研究戴震哲学的目的是与他的整个学术活动相一致的,正如他对“国故”的研究不止是对传统的批判,同时也有其建设一面,即通过转换传统中他认为合理的因素,使其与西方现代文明接轨。他的戴震哲学研究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既要借戴学来批判传统中不合现代文明的一面,又试图通过对戴学的创造性诠释来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
注释:
① 丘为君的《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一书算是难得的特例,书中有对梁启超的戴学研究进行个案研究,但其主要凸显梁启超的戴学研究中戴震考据学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知识体系形成产生的影响。(参见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7-100页。)

③“不为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两句语出戴震的《答郑牧书》。这里被梁启超引用来说明戴震研究方法上的“去蔽”特征。(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