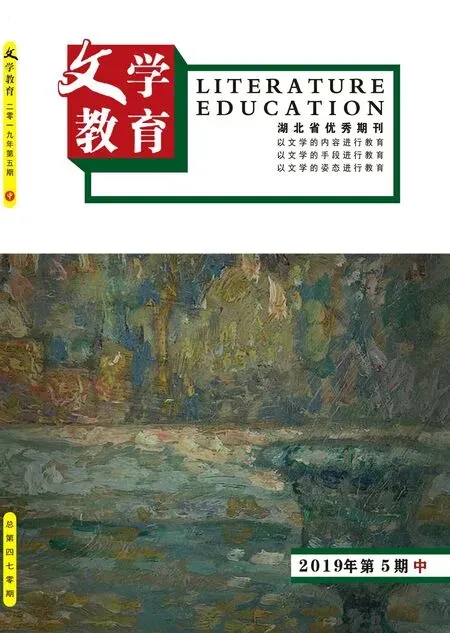论赛金花人物形象的演变
杨 丹
赛金花,原名赵彩云,为妓后改名“富彩云”,取其富贵之意,后被误传为“傅彩云”。出生日期说法不一,1936年去世,具体年龄不可知,生平事迹记载存在出入,可粗略概述为:青年时期,嫁与光绪年间状元洪钧并随洪出使西欧,曾朴的《孽海花》对这段经历着墨较多;中年时期,因“赛瓦公案”备受争议,时值八国联军侵华,争论焦点在于赛是否对于保护北京城民众起到作用,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主要围绕此展开;晚年时期,被许多学者、记者采访,但存在多处口径不一的情况,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刘半农、商鸿逵所著的《赛金花本事》。
《孽海花》、《赛金花本事》、《赛金花》是较有代表性的从不同视角表现赛金花不同时期人生经历的文学作品,这三部作品也通过人物形象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历史风貌。虽然都是描写赛金花,却表现出迥异的文风,人物形象也具有较大的差别。这不仅仅是因为赛金花本人真相的扑朔迷离,也因为作家们关注的历史阶段不同赋予了人物形象不同的时代内涵。
一.不同的赛金花人物形象
“彩云这个人物,有见地,有手腕;又温顺,又泼辣;刚毅果断,伶俐聪明;既苦于受人虐待,又善于虐待他人。”[1]在曾朴的《孽海花》里,“傅彩云”是赛金花的化身,而“金雯青”则影射洪钧。“傅彩云”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妓女形象,她美艳放诞而又心思缜密,巧舌如簧又善使手段。从嫁与雯青到勾引阿福,从邂逅瓦德西到委身质克,从追随孙三儿到周旋四金刚,被彩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男人不可胜数。她前一刻还在同阿福调情,见了仆妇赶过来便立马翻过脸来训斥仆妇行动缓慢;她在船上同质克偷情的事情被外人说破,却凭伶牙俐齿把雯青从“一盆火”说到“软了五分”,最后也只好作罢;在渴求孙三儿又得不到手时识破其诡计,“今儿个既猜破了你的鬼计,也要叫你认识认识我的手段”[2];四大金刚中的活阎罗和金狮子同时找上门来时毫不慌张,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地耐心周旋博得人人满意。另一方面,她从小为妓身世可怜,从而形成了狡黠乖张、欺上媚下、心狠手辣的复杂性格。初与雯青相见被问及年龄,想起身世可怜与雯青相对而泣;及至当了公使夫人,在丫鬟身上出气却是“下死劲一拉,顺手头上拔下一个金耳挖,照准她手背上乱戳,鲜血直冒。”[3]帮雯青劝和夏雅丽时还不忘自己多拿雯青五千马克,撞见毕叶卖疆界图与雯青却不高兴,“这东西倒瞒着我,又来弄老爷的钱了。我可不放他!”[4]曾朴把赛金花的美和狠都写到了极致,“妓女”赛金花形象在《孽海花》中被符号化、标签化,与其说曾朴在写赛金花,不如说曾朴在写一个妓女的传奇经历。
“我本姓赵,生长姑苏,原籍是徽州,家中世业当商。”[5]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原意在为赛金花作传,所以从赛金花的家世写起,采用自叙体的写法,有娓娓道来之意。书中以赛金花的口吻,解释从小为妓的原委,“我是只做清倌,应酬条子”[6];否认在欧洲活跃的交际,“又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跳舞场里去,那却是一派胡诌。”[7];解释仪鸾殿失火她同瓦德西裸奔的流言,“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确实清清白白”[8];认证自己劝说克林德夫人的义举,“这时候我心里喜欢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9]。在《赛金花本事》中,对于历史大事,采取的更多的是澄清的态度,而书中写的最有趣的却是拌猪油的状元饭、“打招”的双橹船、妓院的等级之分等生活细节。在离开北京城逃难过程中,遇到一位好心的老者不避嫌隙伸手搭救更是感慨万分。
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也是写赛金花的传,文章体例以及叙事手法同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都极为相似,但“我眼见少年们的秦楼笙歌楚馆笛舞,觉得不过是一刹那的风流而已”[10]在《赛金花本事》里是没有的。《赛金花本事》的立场是完完全全的赛金花,不同于《赛金花外传》里还添了一个“我”的视角,所以《赛金花本事》里展现出的赛金花更为平易近人,“妓女”的符号被淡化,“平民”的形象凸显出来,她一生坎坷却以一种近乎平淡的态度来对待苦难,而没有过多的感叹和哀怨,也没有过度的抒情,这其中表现的是动荡中普通民众的坚韧和顽强。
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主要取材于曾朴的《孽海花》及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所以在话剧里的赛金花形象,首先还是个“妓女”,同孙家鼐顶撞时一点儿不减《孽海花》里的泼辣,“大人真爱说笑话,好像整个天下的衰亡,完全是娘儿们的衣服穿坏了似的!”[11]国破家亡的时候她还在同清廷的官员寻欢作乐,“趁火没有烧到身上的时候乐一下”[12];其次她又是个“平民”,“总算替皇上做了一点儿小小的事”[13]是清末国人奴才心理的写照。在话剧中,她同孙家鼐、李鸿章等形象最大的区别在于还有“良知”。当伏在尸堆中的妇人向她求救时,她请求军官让她将妇人带走;甚至在面对谄媚讨好的魏邦贤的时候,她也是“怜悯”的。瓦德西表示代表在北京的外国军队感谢赛金花时,赛金花表示自己“代表千千万万的老百姓”[14]感谢他。这里的赛金花一半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一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剧中,从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到魏邦贤这样的小官却是完全站在慈禧太后或者说封建政权的立场上,“现在要争的只在老佛爷一人的体面”[15]。赛金花也是奴才中的一个,但她是一个良知还未泯灭的奴才。在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中,赛金花是一个有良知的平民式的妓女形象,被作者给予极大的同情。
二.时代背景对人物风貌的影响
《孽海花》第一回发表于1903年,最后一回发表于1930年,展现了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三十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变迁。1902年“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被正式提出,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新小说”中以“谴责小说”成就最高。
曾朴在写《孽海花》时没有摆脱传统文人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把赛金花写成了风流放荡的妓女形象,来尽量贴合晚清社会对于妓女的定位。“因为作者认识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到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16]单就赛金花而言,书中戏谑的成分远比真相的成分多。作者用嘲讽的态度表示,即使妓女成了公使夫人,还是不能摆脱其卑劣的品行,这无疑是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所谓孽海花,不过是费勒斯中心主义的一个投射——孽海浮沉全因红颜祸水,因为有着某种身份原罪所以需要付出一生的悲剧去偿还。”[17]曾朴对于赛金花形象的选择和定位极大地受着晚清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一方面,文人狎妓作为风流韵事常被晚清小说津津乐道,而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起着很大的连接作用。“她们既不为社会主流接受,也被社会拒斥的人群拒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她们游荡在社会上流人士和底层小人物中间,作为不同阶层的连结者,她们以特有的‘边缘人’方式书写着自己的历史。”[18]赛金花以妓女的“边缘人”身份联系了上至政客、学者下至戏子、地痞(四大金刚),把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角色都串进故事中,作者这样的选择和定位对于展现三十年间历史的广度上有很大的意义,但在广泛的截取和一味的批判暴露中始终没有出现带有理想色彩的正面人物形象。“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很广泛,但不够彻底。”[19];另一方面,社会的新变也带给妓女改变身份地位的机会,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也在唤醒国内女性意识的萌芽。“随着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人们开始接受一些西方的进步思想,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20]赛金花由妓女而至公使夫人的身份转换,以及对纲常思想的反抗可以看作是社会思想近代化的投影。“自19世纪70年代,即同治光绪之交开始,社会思想即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之后,此种色彩越来越明显,先进思想家们从倡导‘变法’、‘维新’到宣传‘民权’、‘自由’、‘平等’乃至‘立宪’、‘民主’和‘共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想即是晚清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生动反映,也是转型过程的必然产物。”[21]人物身上复杂的性格特点其实也反映了复杂的社会背景,是作者试图深入发掘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思潮的表现。在《孽海花》中,赛金花形象身上既有旧思想的束缚又有新思潮的鼓动,“晚清中国的社会思想主要是同两种观念材料相结合而逐步发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思想,一种是西方近代思想。”[22]
《赛金花本事》的写作始于1933年,成书于1934年。商鸿逵在小序中说,“庚子外交,尤其糟糕,应付大感辣手矣!而能有这么一个妓女出来帮帮,虽不必怎样颂扬她,但总还是值得一道罢!”[23]可惜的是在写作过程中,赛金花的主体意识淹没了作者的客观态度,全书都是赛金花个人意识的流露。赛金花对于曾朴把她写成风流放荡的妓女形象极为不满,在《赛金花本事》中极力辩解,但在提到与瓦德西交际因而保护北京城民众,劝解克林德夫人从而割地赔款的义举时,却保持了审慎和谦逊。这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里的大力宣扬又是不一样的。《赛金花本事》无疑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评判赛金花,外带加一些文过饰非的因素,而话剧《赛金花》则是站在民族救亡的立场上审视赛金花,努力放大赛金花身上值得肯定的那一面。
在1935年春节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明确提出:“在战略上要开展建立剧场艺术的运动,扩大我们的影响,显示我们的力量。”[24]在1935-1937年间,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大剧场”演出热潮,演出的剧目中就有夏衍的多幕剧《赛金花》。《赛金花》剧本于1936年发表于《文学》月刊六卷四号。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赛金花热,众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妓女身上,这自然不仅仅是因为她作为妓女的传奇经历,更是因为她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所做出的贡献是鼓舞民众极好的素材。1929年到1933年爆发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侵华。而在国内,国民党仍把精力集中在围剿共产党上。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左翼剧作家夏衍通过赛金花表现出的正是呼吁抗战救国的主题思想。30年代的“赛金花热”是救亡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回归的投影。[25]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就是对于庚子事变的反思,以及对当时紧急局势的担忧。
刘半农给予赛金花以极大的同情,夏衍肯定了赛金花的良知。《赛金花本事》及剧作《赛金花》都在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审视赛金花这个旧时代的妓女,在国际国内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对于她可能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刘半农希望借此唤起国民抵御外辱的意识,夏衍则更多地在讽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但在某种程度上讲,话剧中夏衍想要表现出的历史背景被赛金花一个人的形象所遮蔽了,观众更多地去关注赛金花的传奇故事。话剧中的赛金花形象既借鉴于《孽海花》又借鉴于《赛金花本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杂糅再加上剧作家个人过于明显的情感倾向使得人物塑造并不是十分成功。夏衍在谈到《上海屋檐下》的创作时,认为之前剧作的人物刻画的不够。“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的对政治的看法。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和,写‘秋瑾’,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26]人物形象的创作直接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脱离了戏剧化的场景和情节,只有慷慨激昂的话语,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必然会受到削弱。
茅盾对于种种赛金花形象的差别认为,“总是容易把主观的思想或情趣反射到对象上。”[27]无论是曾朴的《孽海花》还是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抑或是夏衍的《赛金花》,其中的赛金花人物形象都具有浓厚的历史时代意味,距离真实的整体的赛金花已经相去甚远了。“主观的思想或情趣”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作家们,从宏观上讲,其中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的因素也占很大比重。时代背景对人物风貌的影响是由表及里的,从戏谑到肯定甚至赞扬,人物风貌最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注 释
[1][2][3][4]曾朴.孽海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前言第10页,第301 页,第130页,第105页.
[5][6][7][8][9][10][23]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第7页,第13页,第39页,第41 页,第104页,小序第2页.
[11][12][13][14][15][26][27]安徽大学中文系教学参考书.夏衍〈赛金花〉资料选编[C].合肥:安徽大学印刷厂,1980,第153页,第161页,第195页,第175页,第182 页,第70页,第13页.
[16][19]艾华编.中国近世文化思潮[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第132页至第133页,第132页.
[17]别业青.我的真相,在春天抵达[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序第3页.
[18][20]李欣.历史叙事与语言虚构对赛金花人物历史意义的影响[J].名作欣赏,2017(8):49,48.
[21][22]郭汉民著,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4,第116页,第118页.
[24]茅盾:《剧运评议》,《文学》第9卷第2号,1937年8月1日转引自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73页.
[25]杨士斌.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热的文化现象探究[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