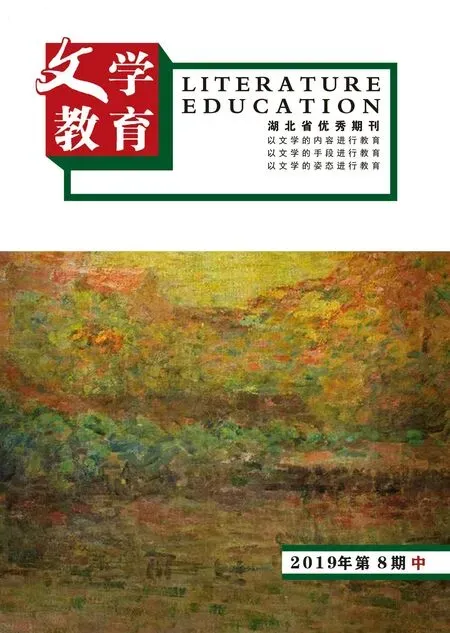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反叛与突破
杨淑惠
创作于1982年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香港西西的成名作。在这篇小说中,西西作为女性作家,以其敏感的性别意识,关注被忽视遗忘的女性职业和被错误书写的女性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小说中,西西将叙事和性别视角融为一体,从各个方面显示出了女性主义叙事的特点,即对传统叙事的反叛与突破。
一.自我赋权的话语体系
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以下简称《像》)中,“我”的职业是一位给死人化妆的入殓师,这里就存在一层隐喻,将“给死人化妆”隐喻为给“给死文字、死语言化妆”,进而操控语言、激活语言,运用语言的力量,建构女性自我赋权的话语和叙述声音,显示出了女性为了建构主体性话语而寻求独特叙述策略的努力。
(一)命名的自我赋权
在《像》这篇小说中,“我”作为一名女性,具有独立的命名权,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命名,实际上是“我”精神世界的具象体现。
首先是对职业的命名。“入殓师”在香港又被称为“殓仪师”,是一种为死者整修面容和身体,使其面容和身体尽可能完整还原的社会职业。在小说创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殓仪师”这一职业在香港地区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指称。但是这篇小说通篇没有使用“殓仪师”这一专业称谓,在第一次引出“我”的职业时,“我”是这样为自己的职业下定义的,“我的工作是为那些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人作最后的修饰,使他们在将离开人世的时刻显得心平气和与温柔”[1]。以“最后的修饰”作为命名职业的核心词语,其语气更为和缓,并将“我”的思想与认识融入其中。如果“殓仪师”这一命名带来的更多的是偏见和恐惧,那作者在这里更希望通过“我”对这一职业的重新命名唤醒读者的反思意识和对这一职业的重新体认,而这种自我赋权的职业命名正包涵着“我”的反抗精神。
其次是对他人的命名。怡芬姑母和夏是整篇小说中唯一出现名字的两个人物。从生活真实经验来看,“怡芬姑母”和“夏”这两个名字或者缺名,或者少姓,都呈现出不够完整的特点。两人的名字,实际上是来自于“我”的创造或者主观截取,更像是一种意象化的命名,以此表现“我”的精神心理。“怡芬姑母”和“夏”这两个名字运用了美好的词汇,包涵着美好的意象,一个让人联想到春日的芳香,一个让人联想到夏日的阳光,这似乎与全文惊悚、悬疑、忧愁的情感基调并不相衬。但“我”与怡芬姑母的最大联系是职业,“我”与夏的最大联系是爱情,以美好的意象和词汇命名怡芬姑母和夏,实际上是在以美好的意象和词汇命名“我”的职业和“我”的爱情,在无声中表达出“我”对职业和爱情的双重向往与追求。“我”独立地拥有并使用对他人的命名权,并以他人的名字传递自己的声音,实际上是“我”作为一名女性,在构建和操控话语的体现。
(二)叙述方式的自我赋权
整篇小说可分为“我”的心理独白和“我”与夏的对话两个部分。两部分都采用了特定的叙述方式,具有了女性自我赋权的特点,实现了对小说人物的改造。
在心理独白部分中,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固定内聚焦视角,以“我”为出发点,叙述者与小说主人公“我”是没有界限的。这些的心理独白始终凭借“我”的感官去感受、去观察、去呈现,以此作为获取信息和评估信息的唯一来源。这就使得此部分的叙事呈现出专制强势的叙事特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述的内容是“我”的意识流动,所有的事件都经过“我”的视角的过滤,所有的人物都经过“我”的视角的改造。也就是说,“我”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都在我的意志之下展开,并不能够反映其本来面貌,只能表现“我”对事件、对他人和对人生的理解。二是叙述的目的是“我”的内心声音的被倾听。叙述者的声音被“我”的声音完全覆盖,不给叙述者客观评论的机会,于是创造出一种真实的幻觉——读者仿佛正面对一个平凡的女子,感受她真实的生活困境,倾听她内心的声音。同时这些心理独白是大段落大篇幅的,这要求读者的倾听是持久的;这些心理独白是围绕几个基本主题回环往复、絮絮叨叨的,这要求读者的倾听是耐心的。这种对读者求真权利的剥夺和倾听义务的要求共同构成了“我”在心理独白部分的自我赋权。
同时,小说穿插了多段“我”与夏的对话,与完整而冗长的心理独白不同,每一次的对话都简明扼要,仿佛碎片。但这些对话呈现出自由直接引语的特点,即“不加任何引导句及引号的直接引语”[2]。自由直接引语是生发现代小说中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相关的重要概念,“从功能上说,它无疑超越了单纯直接引语无法表达的局限,又克服了作为局外人的叙述者所推测的不可信性,让人物真正地自己解释自己,增加了再现人物内心深度的真实程度”[3]。可以说自由直接引语意味着被转述的话语转经验的真实为情绪的真实。在这篇小说,自由直接引语呈现出以下的特点和作用:一是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使所转述的人物对话依旧笼罩在“我”的叙述之下,经过了“我”的加工和过滤,为叙述者“我”的叙述所服务,因此不再具备其原本的话语真实性,以此为根据去探究说话人性格心理,尤其是他人的性格心理,是十分不可靠的。在这里,作者再次利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帮助“我”进行自我赋权,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他人的语言权。二是各处的自由直接引语去掉了引号,却保留了引导词,还特别将“我说”、“他问”、“他说”等引导词单独占行,表现了一种强调的意图。强调这种经过“我”处理与过滤的自由直接引语需要被读者所重视和听见。
二.对“弃妇”叙事传统的突破
“弃妇”是中西文学共有的母题。两千多年前,从《诗经》中的《氓》《我行其野》开始,中国文学就已经开始书写妇女被男性始乱终弃的模式。弃妇现象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除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因为男性话语的构建。但在《像》这篇小说中,作者西西表现出了对“弃妇”叙事传统的突破,“我”以表面上极度自卑的“弃妇”形象为掩体,实际上却是极度自尊,有着强烈操控欲的独立女性。“我”的职业是给死者化妆,由于缺少反馈与监督,“我”对死者的妆容具有绝对操控权,这只是“我”个人的一项游戏。而对死者妆容的操控实际上就隐喻着“我”在其他方面的操控。这种具有操控欲的“非弃妇”形象这在前文所分析的自我赋权话语体系中已经得到体现,同时也表现在文本内容层面。
(一)对命运的态度
全文中“命运”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3次,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命运的力量,相信命运早已注定、不可抗拒,这种宿命论的话语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我想,我所以能陷入目前的不可自拔的处境,完全是由于命运对我作了残酷的摆布;对于命运,我是没有办法反击的”[4],这样的论调与《雷雨》中鲁侍萍的控诉,“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是大体一致的,似乎“我”也应该是与鲁侍萍相似的弃妇形象。但在文本的深层上,通过对死者的评价,又反映出“我”对命运的另一种观点:对屈服于命运的人感到不屑,认为应该勇敢地对命运进行反击。这种对命运的积极反抗精神实际上是“我”对命运操控欲的体现。
(二)对爱情的态度
在文本表层,“我”在爱情中处于被动地位,是在爱情中承担恐惧和忧愁的主体,是在爱情中注定被抛弃并等待被抛弃的那一个。但文本深处,“我”对爱情是积极主动进行操控的。一方面,“我不对夏解释我的工作并非是为新娘添妆,其实也正是对他的一种考验”[5],可见,“我”在爱情中主动设置考验,检验我的爱人是否能像“我”的母亲一样“因为爱,所以不害怕”[6],这种勇敢的品质是“我”所拥有和看重的。另一方面,“我必定会对夏说,我长时期的工作,一直是在为一些沉睡了的死者化妆。而他必须知道、认识,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子”[7],这里连用“必须”、“知道”、“认识”,表明“我”有坚定的爱情信条,要求彼此坦诚和了解,不能彼此坦诚完全接纳的爱情是“我”所不屑的。
(三)对职业的态度
在文本表层,“我”对自己的职业是悲观的、怀疑的、也想过要更换职业。但在文本深处,“我”表现出一个鲜明的职业女性形象,有着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控制欲。首先,虽然“我”的工作是入殓师,但是“我”认为这个工作是重要且必要的;其次,入殓师的工作凝聚着“我”身上最独特且最重要的精神——勇敢无畏,潜意识的话语是在肯定这份工作对“我”的适合度;接着,“我”对自己的职业是有职业追求的,虽然无人欣赏,但“我”希望能够创造出最安详的死者;最后,这个工作对“我”来说还有其他的积极意义,例如,“当别人的心都停止了悲鸣的时候,我的心就更加响亮了”[8],又如,比起那些温暖甜蜜的工作,更能显示出“我”坚定的步伐。
(四)对他人的态度
在文本表层,“我”自怨自艾,认为一切已经失败和注定失败的人际关系,其错误根源来源于“我”和“我”奇异的职业。但在文本深层,“我”对他人对所抱有的偏见感到非常很气愤不满并进行了反抗。起初,“我”对朋友是坦诚的,“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也曾经把我的职业对我的朋友提及,当他们稍有误解时,我立刻加以更正辨析”[9],但“我”所受到的误解和偏见并未因此减少,于是“我”开始保持缄默并最终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以此作为反抗的武器。
可见,表面上,“我”与传统小说中的“怨妇”形象无异,自怨自艾、自我怀疑、被动接受命运、职业和被抛弃的爱情结局。但在文本深层,“我”则处于反抗命运、反抗他人、操控职业、操控爱情甚至操控话语权的地位,是一个具有强烈操控欲的“非弃妇”形象。
三.重构女性叙事文本的美学标准
对于女性作家作品的评价,经常会出现一些刻板印象。在小说风格上,常认为女性小说风格抒情纤柔、敏感自闭;在小说思维上,常认为女性小说感性思维有余,而理性思考不足;在小说题材上,常认为女性作品只能叙述鸡毛蒜皮的琐事,驾驭不了复杂题材。这是都是反女性主义的观点。西西在《像》这篇小说中,展现出突破刻板印象,重构女性叙事文本美学标准的努力。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树立了两个概念,一是“解放政治”,“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追求”[10];二是“生活政治”,“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是生活方式的政治,以反叛生活方式作为反抗压迫的手段和改变国家权力的行为”[11]。解放政治向来被正统文学多青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日常生活中本就充满风险性交易,生活是不可解的一团麻。因此,后现代文学普遍转为再现生活政治视野下的模棱两可、矛盾和悖论”[12]。西西在《像》这篇小说中,通过书写生活政治题材,引发读者的思考,主要表现出以下两点突破。
(一)以生活政治视野为根基,反观多重社会问题
小说通过设立多层对比来凸显各类社会偏见。首先是“我”和怡芬姑母的对比,此时的“我”正在重复着怡芬姑母年轻时候的爱情悲剧,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入殓师这个职业的偏见并没有随之减少和消弭。其次是男性入殓师与女性入殓师的对比,小说中“我”的父亲作为一名男性入殓师尚有获得爱情的机会,但“我”和怡芬姑母作为女性入殓师,生存处境则更为恶劣,获得爱情的机会也更加渺茫。前文分析“我”是一个极度自尊,有着强烈控制欲的人,但这种自尊与控制欲其根源在于“我”内心中的极度自卑。“我”家庭状况特殊,父母双亡,父亲和姑母都是入殓师;知识水平低,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无法里其他人竞争;同时又是一名年轻的女性,从事着入殓师的工作。可见作者塑造了“我”这样一个社会边缘人形象,并通过“我”反映出了职业偏见、阶层偏见、性别偏见、年龄偏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以生活政治视野为根基,反观多重人生主题
《像》作为一篇意识流小说,全文随着“我”的思绪而流淌,以“我”坐着咖啡室等待夏并展开思绪开始,以夏手捧鲜花的到来打断“我”的思绪作结。物理时间并不长,心理时间却十分漫长。小说形式是一个普通女子的絮絮叨叨的诉说,但小说却展示出了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许多宏达主题:生死、爱情、命运。这种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张力,小说形式与小说主题的张力,使这些宏达主题的表达更能震颤读者的心弦。
四.结语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显示出女性主义叙事的反叛精神,作者西西将性别视角融入叙事,实现了叙事多方面的突破。这种突破首先表现在自我赋权的话语体系中,通过命名权的夺取和叙述方式的改变,叙述者“我”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其次表现在对“弃妇”叙事传统的突破,通过表现“我”对命运、爱情、职业、他人四个方面的态度,将“我”塑造成一个虽然极度自卑,但具有强烈操控欲的“非弃妇”形象。最后表现在重构女性叙事文本的美学标准,小说通过书写生活政治,反观多重社会问题,表现多重人生主题。
注 释
[1]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洪治纲.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小说叙述技巧漫谈之七 [J].山花.1993,(2):74-77.
[3]洪治纲.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小说叙述技巧漫谈之七 [J].山花.1993,(2):74-77.
[4]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0](英)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夏璐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英)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夏璐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2]凌逾著.跨媒介叙事 论西西小说新生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