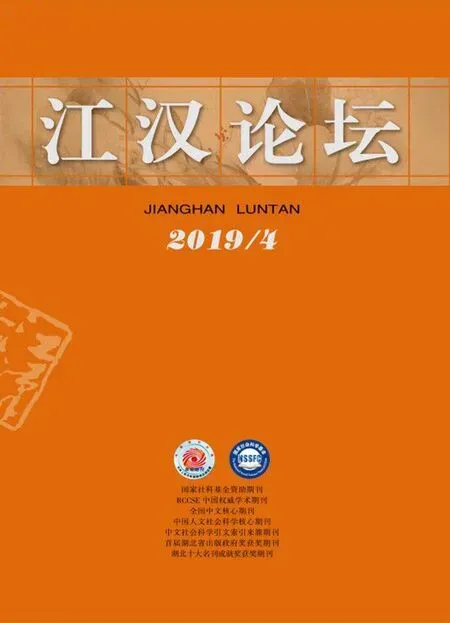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毛 铖
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复合交叉的内涵,共融了治理与现代化的理论精髓。农村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场域,治理与现代化的结合如何与这一场域相适应,从而发挥出指导实践的效用,将是一个变革、融合与发展的过程。政府—市场—社会平行网络结构关系的构建,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农村治理现代化依赖于为解决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问题和有效供给农村社会化服务而形成的功能性网络,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参与和共同投入。在这种网络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既非“国家本位”,也非“社会中心”,而是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参与主体地位的平等、关系的融洽、合作结构的稳定。持续而有效地供给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社会化服务,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包括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问题应对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而后者当处首位,这也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突出服务功能和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属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平行的网络结构关系的根本任务即在于克服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失灵,从而满足农民的差异化服务需求。
农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变革、融合与发展的过程,需要一条耦合性的实现路径,既需要寻求一个有效的突破口,依赖于一个有力的“抓手”,更需要平台、机制与纽带等关键要素的支撑。囿于“就事论事”的惯性思维,农村治理现代化将始终步履维艰。如何突破知识与思维的禁锢,在创新性探索中寻得耦合性变革的有效路径,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也许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突破口
农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变革过程,需要排除体制之困、制度之阻、机制之难,必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有“破”有“立”的变革需要有效的突破口,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则正是这一突破口所在。
1.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有效突破口
农村治理现代化并非是从政治学到管理学的语义学意义上的激进转向,不仅仅是政府的“退”与“放”,市场、社会的“进”与“接”。农村治理现代化也并非简单的为农服务劳动再分工,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转移,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服务供给的参与、服务责任的承接。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①体制机制困境严重阻碍着农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体制与机制变革,需要有“破”有“立”,从而实现并保障“转移”与“承接”过程的有效性、平稳性,实现并确保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关系的稳定、融洽。体制机制变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流水线作业过程,而是一个对既有政治与行政体制提出挑战,必然会经历阵痛期的艰难分娩过程。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并不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必须遵循渐进主义原则,区分轻重缓急,从局部出发,寻找一个有效的突破口,进而从局部到整体,从渐进量变与质变到整体质变。②
2.“正向突破”与“侧向突破”的选择
农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内容与目标从汲取型治理到以社会化服务为中心的变革,也有从政府“一家独大”、“大包大揽”到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参与的治理主体与主体关系变革。破除以政府行政化管控为中心的现有政治与行政体制阻碍,突破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化供给为主的单一服务供给体制机制,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突破口。政治与行政体制是“根”,服务供给体制机制是“干”;“根”为“主”,“干”为“辅”。从变革的角度而言,政治与行政体制突破是“正向突破”,主要且最为艰难,但最终必须面对,变革的最终成效也取决于政治与行政体制的突破成效。而依托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从突破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入手,是一种“侧向突破”。“正向”与“侧向”的优先选择至关重要。
从正面直接进行政治与行政体制上的突破,是一种“硬突破”、“强变革”。倘若成功定然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正向突破”无疑千难万阻,风险巨大。既有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破除旧有体制弊病需要一个旧有体制由“合理”到“不合理”,变革的条件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而从旧体制的“破”到新体制的“立”,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从当前的农村实际看,条件还未成熟到足以突破政治与行政体制的阶段,既有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仍有其生命力。从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入手,依靠服务供给体制机制的变革与突破推力,逆向倒逼政治与行政体制作出以渐进性变革为主的回应,是一种“软突破”、“柔变革”。这样既直接回应了农村治理现代化内容与目标的要求,也有效避免了“正向突破”所不可避免的政治与行政风险。“侧向突破”的优势在于化外在的突破冲击力为内在的改革生长力,通过逆向倒逼来推动“正向突破”。因而,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的突破口应当选择“侧向突破”。
3.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有效突破口
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突破口,实现“侧向突破”,具备“正向突破”所不具备的客观现实条件。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成为一股倒逼农村治理变革的逆向推力,承担起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使命。家庭承包经营(税费)时代,农村治理变革推动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塑。而农村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转向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塑,对农村治理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客观上又产生了一种反向的农村治理变革倒逼推力。至此,农村治理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间的二元双向性互构关系初步形成。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从本质上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了要求。后税费时代,要求农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以服务为中心、以社会多元协同参与为导向的变革。以服务为中心的变革,所指涉的服务不再仅仅是公共服务,而是包含公共服务在内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农村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并推动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最终将是农村治理现代化有效的支撑。③在十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并在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都具有一定的认同基础,这从近些年来中央重要文件中对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所提出的要求就可见一斑。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多元化的动力
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构建起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格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需要具备一致的目标、利益的相关与相连、和谐共存的内外部环境等条件,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满足这些要求,能够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与合作,从而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多元化的动力。
1.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政府、市场与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政府—市场—社会平行网络结构关系的构建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也是能否实现社会化服务功能目标的关键影响因子。农村治理现代化摒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对立与冲突的一贯主张,强调三者之间平等、协同与合作的重要性;摒弃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管理思想,倡导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的交融,强调政府之外的市场与社会力量,呼吁市场、社会主体同政府携手共担治理使命;致力于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组合中搭建更为有效的治理平台,关注多元主体之间形成的多中心、平行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多元共赢的互动过程。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是农村治理现代化能否实现变革目标的关键行动。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突出了市场与社会参与的重要性,注重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方法,通过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来有效提供社会化服务,回应农民的客观服务需求。这对政府职责权限的明晰与厘清,运行效率、监督约束能力的提高提出了要求,更重要的是对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行动过程提出了更高要求。
2.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基础要素
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得以有效而持续的基础是具备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一致的目标、利益的相关与相连、和谐共存的内外部环境。
一致的目标是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得以发生的核心前提。合作的本意即是为达到一致的目标而开展的联合或者配合行动过程。依据属性的不同,合作可以有同质性合作与异质性合作、正式合作与非正式合作等各种分类,但无论是何种属性与类型,合作得以发生的核心前提都是一致的目标,以及对一致目标的共同认可和遵循。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无疑是更高形式的合作,自然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利益的相关与相连是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得以发生的关键。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问题,深含利益玄机。④利益与合作本身呈现内缘性结构关联,关乎合作行动的发生。当合作主体间利益无关时,自然合作无望。当利益相关时,合作具备基础,但这时的合作可能为松散无效型合作,也可能为紧密高效型合作,这取决于利益能否相连。只有当利益相关而又相连时,合作才会紧密而高效。有利益就有博弈,利益的博弈与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存在内缘性结构关系。无相关利益,合作无望,自然无博弈。当合作发生时,利益博弈便产生了。博弈是否均衡,取决于合作状态。只有当合作紧密而高效时,博弈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
和谐共存的内外部环境,是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得以发生的重要保障。一致目标的实现,利益的存在与关联,皆依赖于内外部环境。内外部环境有“硬环境”与“软环境”之分,“硬环境”通常指合作展开所必须依赖的内外部通讯、交通工具等物质性基础条件,“软环境”通常指保障合作开展、利益合理分配的内外部运行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等约束性条件。
3.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实现
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一致的目标、利益的相关与相连、和谐共存的内外部环境三要素。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同时满足以上三要素的要求,且能够从中发挥出有效的协调作用,从而支撑农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于应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问题和有效供给农村社会化服务。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核心任务与目标在于以有效回应农民的服务需求为前提,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可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村治理现代化有着一致的目标。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利益诉求融入一体。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厘清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责权边界,客观上理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结构。责权的厘清,互动关系的构建,实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组合,也实现了不同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有效连接。市场化、社会化的运行机制与健全的制度规约,在赋予市场与社会主体更多的责任及参与权限的同时,实现了三者之间的利益调和。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依托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导的互动监督体系,规范了对政府的监督行为,强化了市场与社会主体的相互监督,从而能有效规约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利益博弈行动。而有效的法律法规配套保障体系与持续性的政策扶持体系,则开出了利益最优调和的“药方”。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市场化运行体制与机制、多元化组织枢纽与平台的架构,以及配套的政策、制度体系,为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提供了内外部“软环境”。而多元化的网络信息系统,以及其他诸如办公场所、道路交通等物质性条件的建设,则充分保障了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内外部“硬环境”。
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台与纽带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成为承载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化、系统化平台,强有力的平台中心磁场形成一股由外沿向中心聚集的磁力,牵引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向平台集中,行动、互动于平台之上;牵引政府、市场与社会向治理的中心目标内聚,协同、合作于平台之上。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将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连接纽带,勾连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突破松散的治理形态,形成网络化的紧密治理结构,变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分离、隔阂的关系结构为合作、紧连的关系结构,变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之间单向性的治理关系结构为双向互动性的关系结构。
1.汇聚中心的平台
农村治理涉及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针对的是“原子化”、千差万别的农民客体,是一种“多对多”的多重层级、多重互动关系与合作关系交叉重叠的治理。仅仅依靠治理主体与客体自身的自治理行动,必然是一种分散与错层的治理结构、松散与泄力的治理形态。
农村治理现代化追求的是合作与平行的治理结构、紧密与合理的治理形态,即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平等的网络化合作,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间平行的网络化互动。这就需要借助于有效的网络化平台,形成有效牵引力,满足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内外部条件。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种网络化、组织化与系统化的体系,能有效充当这一平台角色。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社会化服务为中心,构成一个强有力的服务中心磁场,将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吸附”于平台之上。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运行体制机制,形成一股强大的磁力,规约着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的行为,牵引着治理主体与客体向平台聚集,进而有效行动、互动于平台之上。共同的治理目标、紧密的利益连接、和谐的内外部环境,形成一股由外沿向中心聚集的内聚牵引磁力,牵引着政府、市场与社会沿着内聚性的趋同方向,向农村社会化服务这一治理的中心目标内聚、发力。
2.深度勾连的纽带
现有农村治理形态中,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之间有着分离与松散的连接。政府与农民的连接、市场与农民的连接、社会与农民的连接相对分离,属于单点对单点、单线对单线的连接,缺乏点与点、线与线的串接,更加缺乏点与面的结合。多元治理主体在相互隔离中参与农村治理,难以有效开展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难以形成治理合力。农民也只能被动接受点或线的连接,既无连接选择权,也缺乏主动参与和互动参与的基础。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纽带勾连将克服现有治理缺陷,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之间互动治理的点面结合。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社会化服务供给链为纽带,通过合作链条的勾连、供给主体权责的勾连,将政府、市场、社会连接起来,将政府、市场、社会与农民的点线关联串接起来,在形成平行的网络化服务供给结构的同时,构建起平行的网络化治理结构。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隔离被打破,分散的治理力量汇聚、整合成集约化的力量,分散、分离的治理行动演变成为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整体性行动。以农民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构建起了农民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的治理关系结构,农民有了主动参与的基础与权利。在双向点面结合的多重勾连中,农民增强了自身点线连接的选择权与话语权,也强化了自身在治理过程中的监督权,突出了互动参与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在农村治理现代化中锻造成为强有力的勾连链条,实现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重勾连,既紧紧勾连着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也紧紧勾连着政府、市场、社会治理主体与农民这一治理客体。
3.农民组织化的共同体
农村治理现代化对农民这一治理客体提出了组织化的要求。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组织化。⑤以兼业小农为主体、以农民利益为重的农民组织化格局,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的前提、重要路径与方法。⑥而农民的组织化将直接决定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成效。农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农民通过组织化实现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双向互动,在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的同时有效监督治理主体。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够有效降低多元治理主体与农民双向互动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提高治理效率。
农民的组织化无外两种途径:一是外生型组织化,即通过外部压力作用将农民纳入组织体系中;二是内生型组织化,即农民以自愿为基础而组建自组织。⑦唯有实现两种途径的整合,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的组织化目标。但农民恰恰缺乏的是自组织能力,而仅仅依靠外部压力作用,又不可避免地会因农民的认同不足而生发逆组织化张力。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实现内生型与外生型组织化的有效整合,构建农民的组织化共同体。首先,内生型组织化构成农民组织化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利益缔结—责权匹配”为核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重塑,变现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松散型的组织结构为紧密型产权共有组织结构,重构以股权联合为核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共有体制与机制,将使分散的家庭农户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一个共赢共损的农民利益共同体。⑧其次,外生型组织化构成农民组织化的保障,实现农民组织化的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组织体的身份参与到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进而参与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互动行动之中,作为有效的组织单元,被赋予供给的枢纽与载体角色,将实现与政府、市场、社会的组合和有效对接。作为组织细胞的农民,是服务客体与治理客体。通过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一平台与纽带、枢纽与载体,分散的农民将被紧紧联结起来,最终被紧紧勾连在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网络体系中。
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为农村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为农村治理现代化奠定三重基础:认同基础,即市场、社会与农民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认同;合作基础,即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的形成;目标与价值基础,即以有效供给社会化服务为中心的目标与价值的实现。
1.认同基础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⑨认同关乎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市场与社会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认同将直接决定二者参与变革的主动性、积极性,也将决定政府、市场与社会能否有效开展合作。市场与社会的认同,取决于二者能否公平、平等地参与变革,并且有效保障自身的正当利益。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在多重体制与机制的保障作用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将基于共同的目标、相连的利益而开展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进而在参与激励和利益保障上,确保市场与社会的认同。
农民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认同将直接决定变革的意义与价值。农民的认同首先取决于变革能否带来自身服务需求的满足。农村治理现代化有多重目标,但回应并满足农民的服务需求,从而保障农民的根本权益是核心。其次取决于农民对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认同。农民生于长于“熟人圈层”之中,对“圈子”以外的陌生人有着天生的防范和抵触心理。⑩他们对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不信任是必然的。农民对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认同,取决于信任,而信任来源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在与农民的互动中对农民服务需求的满足和根本权益的保障。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依托于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满足农民差异化、多元化的服务需求,这即是农民对农村治理现代化认同的基础所在。
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今天,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宁静的夜晚,请你凝神远望,展开你联想和想象的翅膀,说说现代的天上街市是怎样的。
2.合作基础
一致的目标、利益的相关与相连、和谐共存的内外部环境重在探讨如何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而奠立这一协同与合作基础则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另一层面的价值。
如何有效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促进三者间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是当前农村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难题。政府、市场与社会分别代表三种治理力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运行逻辑,即行政化逻辑、市场化逻辑与社会化逻辑。如何实现三种运行逻辑的有效结合与融合至关重要。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孕育于整合与融合的需求之中,并在不断努力推进三种治理力量与运行逻辑的整合与融合。
在历史的变迁中,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孕育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变革中,从而开启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尽管初期合作有限且难以克服政府“一家独大”的弊病,也未真正实现三种运行逻辑的整合或融合,但随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三种治理力量与三种运行逻辑的整合与融合渐渐深入。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将日渐成形。
3.目标与价值基础
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价值突出服务功能和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供给水平,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性衡量标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核心目标在于以农民的组织化合作和参与为重点,以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合作和协同参与为核心,满足农民差异化、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本身与农村治理现代化有着趋同的目标和相同的使命。尽管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并非为农村治理现代化而产生,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在建立健全过程中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助推,无疑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与价值的实现夯实了基础。
五、余论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有效支撑农村治理现代化,这突出表现在二者之间的四重逻辑关系中。但农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并不意味着农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自然实现,且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尚待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治理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在变革与发展中协同共进,这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共同努力。
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并给予足够的支持。应当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上升到关系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突出地位,形成从国家到地方,从中央到县、乡,共同重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氛围,真正从政策上给予应有的支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中,应当引导和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引入、对接与融合,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与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耦合发展。
必须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上付诸努力。第一,进一步建立健全现有的体制机制,弥补和完善体制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从目标、机制、主体、枢纽与监督体系等各个方面实现变革与创新。第二,以农民的服务需求为中心,组织化合作参与为重点,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同与互动合作参与为核心,构建起网络化的组织体系、供给体系与保障体系。第三,依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利益缔结—责权匹配”和系统化、体系化为核心,推进农民组织化重塑与再整合。第四,实现纵向上政府自上而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下而上监督,横向上市场与社会主体左右相互监督的有效结合,构建起多元化的互动监督体系。第五,着力构建以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扶持体系、可持续性的改革创新孵化机制为重点的多元化保障体系。
注释:
①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② 俞可平:《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③ 毛铖:《我国农村治理变革与农村服务体系变迁》,《求实》2017年第8期。
④ 王伟光:《利益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⑤ 杜润生:《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⑥ 温铁军:《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⑦ 罗兴佐:《农民合作的类型和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⑧ 毛铖:《利益缔结与统分结合: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统分两极化向统分结合的理性与回归性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⑨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