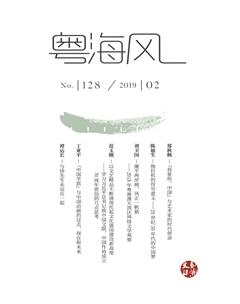由反讽到共同体
唐诗人
一
对于当代文学,我一直有个很主观的判断。即当代文学是反讽的文学,它是作为一种反讽的角色、力量而存在于当代历史、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大而无边的判断自然有其不可信的一面。但这里的意思并非指“当代文学是什么”这样的判断句本身,而是说,我们的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当其面对当代历史时,普遍都是一种反讽的存在。文学在当代,早已是无足轻重同时又自以为很重要的边缘角色。这种边缘状态,我们可以说成文化回归了历史正常状态,但却无法摆脱它作为反讽角色而存活着的本质特征。
之所以下这个判断,与我对“反讽”概念的理解有关,也与我对文学、对时代的总体性理解相关。对于“反讽”,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一种修辞方式,这是从语言内部的关系结构来给出的理解,相对于字面意义的直接言说,反讽是间接的。但如今我们对反讽的理解,已经超出了语言修辞,更是一种文本状态或写作姿态的反讽,是文学性和文化性相交融的一种接口。布鲁克斯对反讽的解释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反讽与否,与语境关系密切,这语境可以是文本内的,其实也可以延伸到社会文化语境。为此,语言的修辞结构中的反讽,可以延伸到文本之外来理解。比如延伸到社会结构中,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或者更宽泛一些,作家、作品、时代、社会、历史,等等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些结构关系内部,文学的角色如何是反讽性的?因为文学并非直接参与历史实践。或者说,文学人物、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历史角色。他们所拥有的理性和知识,基本上无法直接作用于时代社会。不管作家们主观上是积极批判还是消极嘲讽,客观上都“外在于”这个实用主义盛行、一切都功利化了的世界。借用黄平的话,应该就是一种“脱历史”状态。不管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积极加入社会实践、响应时代号召的现象,还是那些站在历史现场外围观看、审视式的写作,相对于只需要行动和掌声、不需要甚至不允许反思和批判的社会现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反讽性存在。
积极希望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写作,它们的反讽性不是写作本身的特征,而是这种参与的“渴望”,或者说它们的叙事状态与最终达到的社会效果,以及真正的歷史需要之间,这里面的悖论决定了写作的反讽本质。而且,即便是激烈地正面批评或者反抗,微弱的个体同阵容庞大而坚硬顽固的现实世界对比起来,也是如鸡蛋对石头一样反讽。而且,面对这个商业化到了一切都可以计算利益的资本时代,正儿八经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反讽的现象。对于在历史现场外围的审视性写作,它们的反讽性,在叙事上可能具有更明显的反讽手法。另外,他们作为旁观者这一历史角色本身也是反讽的。旁观即意味着抽身而出的平视,甚至是站在精神高地的俯视,不管什么口吻,都带着一种冷眼旁观、冷嘲热讽的嫌疑。
必然,上述这种宽泛的反讽判断,除开带了一些虚无色彩,最大的问题在于因过于宏大而显得空洞无比。这也是一直阻止我展开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宽泛得令人无法下手。这种困惑一直存系着,为此当我看到黄平的新著《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以下简称《反讽者说》)时,颇为兴奋。此著是黄平多篇论文组合起来的,严格来说不算专著。但他用“反讽”“虚无”贯穿当代文学那些“边缘作家”,梳理出一条当代文学的反讽传统。这种有问题感、有精神主线、有文学史意识、同时还能不断迸现全新思维见解的架构、论述,比起当前众多看似系统性强、只梳理却没有问题感、更没什么创新之见的所谓专著来,它更能称之为专著,有着更为清晰的思想发现和文学史参考价值。
理解、认识黄平《反讽者说》,首先需要把握黄平对反讽概念的界定。序言通过闵行客(其实就是著者黄平)的口吻直言:“黄平对于‘反讽的理解与定义和以往不同,在他这本书里反讽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或文本的结构要素,他讨论形式层面的‘反讽始终和思想层面的‘虚无相联系。”[2] 据此说法,可见黄平的“反讽”与我理解的“反讽”含义相近。黄平这里的“反讽”,不仅仅是修辞技巧,不限于文本内部,它是反讽形式与虚无思想的融汇论述。反讽的形式,多为文本内部的叙述特征,虚无思想多为作家对自我对时代对历史的精神理解。这两个层面的结合,可看做是形式分析与思想阐释的融会贯通,不是单纯的技术分析,也不是简单地缩写一个故事然后做思想主题概括,这本身即是文学作品研究的理想状态。黄平把作为文本内部的“反讽”和作为文化表征的“反讽”融合于文本细读里,同时联系起相关的文学史、社会史资料,灵活地出入于文本内外,很有说服力地阐释了路遥、王朔、王小波、韩寒、郭敬明、李洱等“边缘”作家作品,以及电影《大话西游》的反讽特征。
二
具体而言,第一部分《起源时刻的虚无者》就有很大胆的新见。绝大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当代文学与反讽关系,主要还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尤其会以王朔、《废都》等作为典型,最多也是追溯到现代主义开端处的《你别无选择》等。而黄平把这个“反讽”的起点放在了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以北岛《波动》中一段表现虚无状态的话作为论述起点,从这虚无精神中看到历史的变化,从小说多视角的复式叙述特征看出总体性的瓦解,并结合当时关于《波动》的众多评论观点,论述起源阶段的存在主义热源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原有的价值体系瓦解,在虚无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与自由的可能。”为此,黄平指认存在主义热更是一种虚无主义热,并由此提出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诞生于‘虚无之中的‘自我,将是一种怎样的‘自我?”[3]
从探讨虚无到探讨自我,直接链接到了“潘晓讨论”。“潘晓讨论”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大话题,围绕“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直接作用于个体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亚当·斯密“经济人”观念,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人物都参与其中。黄平追溯、重新阐述这一历史话题,也就从另一个方向堵住了我们对虚无思想的积极期待,追问诞生于虚无中的自我如何不陷入纯粹逐利、无视德行的现代犬儒,也即探讨“经济人的边界”何在。针对这一问题,黄平随即对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形象展开分析。高加林的难题就是“经济人”的边界问题,他毁了与农村女孩巧珍的婚约走向了城市女友黄亚萍,这在“经济人”观念看来是毫无过错的,但在乡村伦理中就是“把良心卖了”。高加林最后通过关系成为城市人,随即被情敌的母亲、同时也是官僚系统的人物举报而重新打回乡村。黄平判断他是“新时期文学最后一位主人公,也是新时期文学真正的世界意义上的主人公”,“这位改革时代的新人虚无而自我”。[4] 高加林面对了多重力量,他所面对的经济人边界问题不是道德、乡村伦理问题,而是官僚系统的强力排挤,他的虚无有多重根源,他的自我复杂多面,他是一个未能完成或者说转折时代的经济人形象。
这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虚无精神的起源有着特别的帮助。但黄平在这部分似乎并没有特意讲出《波动》和高加林形象的“反讽”特征,尽管他的论述其实都在触碰反讽问题。比如对于《波动》小说中的各种否定,它不仅是表现虚无,更是在这种虚无中嘲讽着自己或一代人的历史存在。而高加林,他的反讽是多面的,内在于经济人形象的更是他作为个人的命运性反讽。高加林的经历相对于当时还是官僚把控一切的历史现实,其所谓经济人特征是对改革开放、对新时期社会理想的极大反讽,他的命运遭遇拉平了20世纪70年代末个体获得自由后所能拥有的美好希冀。另外,张克南母亲举报行动的正义凛然和自私目的之间所形成的冲突,这点黄平有过直接的阐述,也是文本内部一个典型的反讽情节。
从反讽视角来看,《波动》和《人生》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我的反讽判断也有牵强的嫌疑。但此著剩余的分析对象,王朔、王小波、韩寒、李洱的作品,以及电影《大话西游》,则都有着清晰的反讽特征。第二部分探讨王朔。王朔小说的反讽形式,是特别明显、已被公认的美学判断。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逐渐兴盛的历史转折期,在知识分子普遍热衷于言说西方话语观念时,在青年们参与历史的激情欲望遭遇完全的颓败后,王朔看到了内在于这些现象背后的虚假与伪善,感受到历史转型期内大多数人的迷茫和虚无。黄平从反讽与共同体关系出发,侧重论证内在于这些反讽形式中的“自我”特征,那是一种拒绝宏大历史编织、“脱历史”的虚无自我。但黄平不限于对小说人物的“自我”进行评断,他列述各种关于王朔作品的解读,更结合王朔自身关于大众文化的观念,以及王朔认定自己为反英雄的英雄、“恶魔式的英雄”等自我期许,也即综合了作者、文本、读者(评论者)三种材料来阐述王朔式喜剧性反讽美学及其命运遭遇的历史文化意味。
王朔的反讽是失败的,他必然陷入虚无。黄平对这种失败的解释极有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写作的暮年,王朔既滑稽又悲壮地苦苦追求‘永恒,这一幕令人瞠目结舌,又无限感伤。他最终奔溃于自己的‘反讽,走向了症候性的精神分裂——作家被自己的藝术形式所摧毁,反讽的‘轻最终无法承受历史的‘重。”[5] “反讽”是叙事目的与叙事形式的故意相悖,这需要特殊的时代语境和读者基础,否则只能出现叙事形式的直接效果,也即只作为喜剧得到一场欢笑然后瞬间消逝。而作家的叙事目的往往被忽视、不被信任。而且,形成反讽美学的最大动力,也是历史现实,它需要直接的时代关切点。唯有面对时代性话题,即有明确的“讽”的对象,“反”才具备心理基础,反讽才能够成立。“反讽”的叙述逻辑和精神结构,注定了王朔,以及更多热衷于反讽表达的作家无法理想地纳入传统的文学史书写观念。在文学经典化思维中,这种反讽也是危险的,时代过去,具体的历史痛点过去,“讽”的对象消失,“反”的意义也跟着消失,再去理解这类文本,似乎也只能剩下纯粹的喜剧之笑。即便“讽”的对象不消失,而是更顽强化,那“反”的内涵也即更难以阐发,同时也更加不可能进入正统的文学史。
三
“反讽”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王朔的结局,也决定着王小波、韩寒等人的命运。王小波应该是对反讽美学操作得最为娴熟的一位,他比王朔更清楚自己的历史位置,且也更清楚写作本身的位置。王朔和王小波,包括韩寒,都可算是一种智性写作。而比较之下,王朔的“智”是相对笨拙的,王小波的“智”最为精湛。王小波能够把“智”灵活地应用在叙述艺术层面。比如叙述者身份的设定问题上,“王二”和“我”的关系到底怎样?他们似乎是同一个人,但其实并不能肯定,这是很游离的。这种身份的游离,在黄平看来,是“脱历史”的表现:“王小波的文学是虚无的文学,与任何立场无关。在王小波这里,历史既不是左翼所理解的,也不是右翼所理解的,历史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实际存在,他不在历史之中,而是在历史之外。”[6] 这一理解无疑解构了王小波神话。就因为叙述者层面的游离,只就一个局外人视角的叙事技巧,左右翼赋予王小波的思想光辉就全部被端除了,这似乎有些难以服人。但黄平这种解构,目的是建构起新的意义理解:王小波的后现代式反讽叙述,治愈了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他的反讽性的虚无,蕴含着对于“真的人”的向往。
王小波是虚无主义者,但并非犬儒主义作家。在治愈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层面,他这种“脱历史”是一种真正的“伤痕文学”写作,这不同于新时期开始阶段的作为受害者身份的讲述,而是走出了历史、处于后革命时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讲述伤痕,更希望超越、治愈伤痕。王小波与“后革命”时代的关系,类似于村上春树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关系。为此《革命时代的爱情》“不是自由主义式的爱情对于革命的解构,而是后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困境,以及对于这一困境的超越”。理解这种超越,核心就在于理解王小波的叙述中具有对“真的人”的向往。
这所谓“真的人”,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黄平从王二和×海鹰/姓颜色的大学生之间的爱情关系中分析出王二想要摆脱“革命”阴影的纯真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是悲剧性的,“追求”本身即意味着王小波非犬儒的精神实践。而这种不可能,本身也就是“脱历史”的不可能,“局外人”的视角也就只是一个玩笑而已。游离的叙述者最后不得不合二为一:“‘我就是‘王二,‘我不是在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王小波的‘局外人视角——‘我重新成为‘王二。”[7] 黄平引用小说最后那段“我”胳膊受伤留下了伤痕来说明,这种人称的虚拟也即结束,回到现实,伤痕依旧。
不得不说,黄平这个阐述非常精彩。但如果我们从结论倒回去看论述一开始的问题的话,能够在最后时刻合二为一的“王二”和“我”如何在文章一开始时却可以完全分开来并以此为基础支撑起如此系统化的观点?毕竟文学作品的技巧、故事、思想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最后部分和最开始以及中间部分的叙述技巧、故事性质也都是一个完整体的不同侧面。如果能在最后合二为一,那小说最开始的分开叙述也只是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多维视角而已。最后能够整合,也就无所谓“某种程度上,叙述人无法整合‘我和‘王二这种双重视角的冲突”[8] 。指出这一可能的矛盾,并非不同意黄平的全新解读,而是我相信王小波小说所能指涉的问题或者说思想魅力是更为宽阔的。可以有黄平的解读,也可以容纳之前的自由主义等思维评论。这种思想张力,同时也表明王小波的反讽美学比之王朔等人是更为成功的。
王小波使用的双重人称的叙述技巧,这种技巧下的反讽,既能应对题材故事中的历史文化,以反讽的美学形式对那些作为过去时的革命话语进行否定。同时,它又能够兼顾讲述这一故事时的语境,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状况,以表现“脱历史”欲望的不可能,来反讽90年代文化逐渐轻型化的状况。前者是作者与故事时代的结构关系,后者侧重的是作者与讲述故事时代的关系。这是两种不同的时间,对应着不同的精神结构。“王二”与“我”都是叙述人,都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不能直接对应。王二和“我”关系的游离、模糊,说明作家在处理历史的时候,是游荡在旁观叙述和自我回忆两个层面的,也可以说是综合了他人与自身的历史。这种综合,是小说创作论层面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标示着作家对历史书写的反思,不管是第三人称历史旁观者视角,还是第一人称的历史参与者视角,都是一种“脱历史之不可能”。对这种“不可能”的表达,恰恰彰显了王小波的反讽是后现代、后革命时代积极的、负责任的反讽。
四
肯定王小波的反讽美学不难,它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但如果“肯定”郭敬明、韩寒的反讽美学,要遭遇的阻力必然更为巨大。“和以往通俗作家相比,郭敬明的写作,非常有力地介入到当下‘新人的生产。在文学史的脉络中,郭敬明自己恐怕都没有察觉到,他的写法不无怪诞地弥合了‘抒情与‘资本的冲突,这是‘浪漫主义兴起数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9] 这一评判非常需要勇气,它反转了文学界对郭敬明文学的印象。黄平给出如此高评价,他的依据是郭敬明书写的那种高度抽象化的生活,恰恰落实了个人与历史脱钩的具体性,“无论承认与否,郭敬明是这个抽象时代真正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同样,对于韩寒,黄平也是通过论述他的写作和剧变之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破碎化特征的对应,指认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中产阶级的美学倾向和社会处境。韩寒这种“大时代”写作,因为面对的是“大时代”终结之后、只有伟大遗骸的破碎的“大时代”,所以它必然是一场文化游击战:“韩寒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处游荡,不断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并且对这一切予以讥讽。”[10]
创作把握了时代精神,实现了与时代特征的高度对应,这一经常被纯文学界强调的非常难以实现的创作理想,在郭敬明、韩寒身上却得到了完美体现,这貌似会是一个让纯文学界惊讶到不可接受的观点。但其实也差不多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解,即郭、韩的作品是实现了与时代的对应,但纯文学界还有一个“拒绝”接受他们的理由:深度。郭、韩的创作是吻合了时代性的精神状态,但其问题也是这种吻合本身。在反讽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情绪状态下,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就不再能够停留于表现反讽本身。没有从深刻性层面实现超越这种轻型的反讽情绪,吻合就是一种讨巧,甚至就是一种商业时代的资本游戏。
出于这种深刻性的匮乏,黄平最终否定了郭敬明、韩寒作品的反讽意义。对于郭敬明,黄平认为他那种重视人物形象、叙述技巧和语言修辞的写作,是一种教科书式、教条化的文学观念,这种写作面对当前这个确定性已经消逝的、转型阶段的历史时代,走向的只是“幻城”,離文学所推崇的“真”愈来愈远。而韩寒的反讽,看似姿态高贵,但他只是表达了一种合符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反讽形式,这种表达没有对自身的反思,而是让自己游弋其中。本质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反讽,他只是用反讽来疏离真实,并且慢慢滑向了犬儒。他不是担负起对中产阶级那种只为疏离现实的反讽心理的反讽,而只是迎合那种姿态性的、只满足个体精神自由幻象的反讽。“韩寒笔下游荡的‘个人,不像鲁迅那么决绝,那么黑暗沉重。”[11] 失却沉重性的反讽,也就只剩滑稽,成为资本的俘虏,如此韩寒也就只是附着在另一片粉丝群上的郭敬明。
五
在论述王朔的一章里,黄平有一段话这样写道:“在这个漫长的喜剧时代,有两种笑声的叠加:空洞的笑与戏谑的笑。大众文化所代表的‘空洞的笑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21世纪的韩寒,他们是‘反讽美学不同阶段的代表。‘反讽美学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应对着‘脱历史的疏离与分裂。对于这场隐藏在笑声中的文学革命而言,王朔选择了语言,王小波选择了叙述,韩寒选择了政论;王朔的故事越来越虚无,王小波的故事越来越艺术,韩寒的故事越来越重复。随着社会愈发失衡,参与性危机加剧;或者随着社会变得平衡,参与性危机缓解,‘反讽美学都将耗尽自身的能量。无论哪一种可能,社会都要重新经历‘政治化的阶段,一代人将重返到历史之中。”[12] 这是一个极好的概括,指出了反讽美学的内在困境,随着时代变迁,它们的生命力将迅速耗尽。在这种必然“失败”的命运面前,反讽美学需要通往何处去?作家们自身该如何面对这种注定了失败的历史宿命?这里,除开对我们传统的“没有笑声的文学史”观念有所反思之外,更加重要的还是反思反讽美学本身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深度化的思维来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只有深刻把握这个时代,反讽才有可能穿透虚无。
穿透虚无,这是一种能力,更是一份信仰。黄平从李洱《花腔》提供的“午后诗学”里发现,“横亘我们的,是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侧,而不是那一侧,承担着历史的结果,而不是憧憬着历史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未必是做出选择以穿越虚无,而是直面选择之后所带来的更大的虚无”。[13] 黄平希望我们从午后回到正午,也即从虚无回到选择——重新选择,同时这也意味着走出后革命氛围下的瞌睡状态,再次塑造革命氛围,重建历史总体性。
这种重建可能吗?黄平通过分析《大话西游》,为我们树立了信心。“《大话西游》架空了历史,但却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历史性的作品,在荒诞不经的表象下,《大话西游》忠实于自己的时代。而要准确地传达我们的时代,有赖叙述技法的重新发明,在形式强度上,《大话西游》以复杂的四层架构……四层故事背后,是永恒的神的意志,以及永恒的荒诞。然而个体绝非毫无作为,以偶在的爱,人对抗着神意,在洪荒般的时间绵延中标识出自己的存在。”[14] 《大话西游》打动了一代人,这一代人里主要是“80后”。“80后”从叛逆到犬儒到虚无,忍受着破碎而无聊的后革命文化,承担着后现代生活的荒诞与野蛮。但是,“80后”一代也并非沉于虚无就自甘堕落,而是在坚持着爱、坚守着最初的梦想。
“‘无可以生‘有,‘虚然而不‘空。”[15] 黄平的这种乐观,并非只是基于文本分析的期待,他还“指明”了实现这种期待的可能性道路。在分析完郭敬明、韩寒的反讽后,有一节专门阐述“80后”写作的可能性。黄平认为“80后”写作的可能性,在于“中国梦”的可能性。要实现“中国梦”,就不能继续满足于表面的反讽,而是由反讽走向团结。“团结”就意味着创造新的共同体。“在最高的期待上,何谓‘80后文学,真意在此,历史终究没有中介,历史将再度敞开。重建共同体的那一刻,就是现实主义归来的那一刻。”[16] 唯有重建共同体,才有真正的现实主义。
从反讽走向团结、通往共同体,这是需要“80后”努力承担起来的历史使命。历史裂变中成长起来的“80后”,一直处于“脱历史”状态。他们尚不是历史的主人,但又承担着历史的重任。历史过于破碎,使命过于沉重,羽翼稚嫩的“80后”只能通过反讽来实现疏离,用暧昧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一块漂浮的飞地,在自我与时代之间收放自如。反讽状态下的“80后”们,“收”或许就是独善其身,“放”也许就能兼济天下。那么,“80后”会停于“收”还是会走向“放”?黄平通过分析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概念来暗示一种必然走向“放”的趋势。
其实,“80后”能够给这个时代提供反讽的文本,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具备渴望参与历史建构的一面。我以为,一旦时机成熟,参与性危机缓解,“放”將会是普遍的选择。穿越反讽之后,反讽作品本身可能会失去生命力,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种更值得期待的、更负责任的精神实践。南帆在谈论负责的反讽时说:“人们置身于语言,相当程度上亦即置身于历史。因此,哪怕是间接的和曲折的,负责的反讽从来不会忘却语言描述的那个世界始终坚硬地存在。”[17] 不会忘记这个世界的坚硬,也即还对这个世界抱持热情。还有热情,就还有希望。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注释
[1] [美]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2] 黄平:《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代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3][4][5][6][7][8][9][10][11][12][13][14][15][16] 黄平:《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第30页,第54页,第132页,第151页,第113页,第200页,第209页,第211页,第55—56页,第280页,第303页,第304页,第227页。
[17] 南帆:《无名的能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