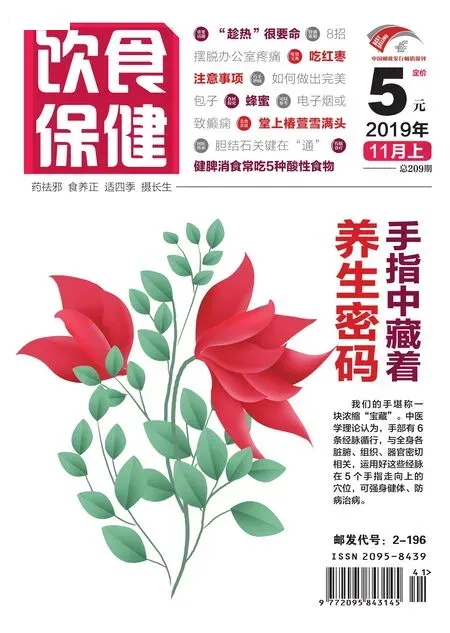贻贝
佚名 文
贻贝又名淡菜,而淡菜其实是贻贝肉的干制品。许多人都有些不解,淡菜有咸味,那怎么还会以“淡”相称呢?我们从徐珂的《清稗类钞·饮食》中似可找到答案:“淡菜,蚌属也。以曝干时不加盐,故名。”那么它明摆着是贝类,又何以冠“菜”名?大家不要以为,“菜”一定就是蔬。淡菜就是上海人下饭的“小菜”。尽管这里说得有理,可是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困惑。大连人叫它“海红”,因为撬开贻贝的壳以后,露出来的肉都是红黄色的,把它晒干以后,就叫“海红干”。香港美食家蔡澜在他的《蔡澜食材字典》中称贻贝为“青口”。这就要说到我们的三种主要贻贝品种了,它们是紫贻贝、厚壳贻贝、翡翠贻贝。广东沿海产的是翡翠贻贝,“青口”之名应与其颜色有关。我在上海的超市里买到过从新西兰进口的盒装“青口”,个大色绿,鲜嫩度令人满意,当然价格也不菲。
贻贝与牡蛎一样是双壳(贻贝为双壳类当中比较兴旺的家族,其分布的范围与产量仅次于牡蛎)。贻贝的壳呈三角形,它的生活方式介于牡蛎与蚌之间:它的足会分泌黑色发状物,称足丝,能固着于岩石及沙砾上,但是也能运动——在固着体上作小范围活动。我每次买到贻贝后,都要先拔除足丝——怕它不干净。浙江东海的枸杞岛,因盛产贻贝而被当地人称为“淡菜之岛”,渔民可带一把短柄铁铲潜到水下铲贻贝,也可一人在岸上先用篙子去捅,水下另一人则用网兜去接。

以前,烟台大连那边的贻贝都不值钱,南方人前去想吃海红,东道主很尴尬,因为这东西在当地,都被搅碎用来喂养鱼虾了。我到过舟山群岛的一个渔港——沈家门,吃中午饭时我找了家饭店,要了一碟贻贝一瓶啤酒。在这里,贻贝算是最便宜的海鲜了。蔡澜也曾提到过:“从前香港庙街有一档卖生灼青口的,是醉汉最便宜的下酒小菜。”他还告诉我们,贻贝在欧洲的身价大不同,法国人在十三世纪时把它当宝,宫廷宴席中也有供应。
昔日,上海街头有小贩拉着板车——上面放了一大堆乌黑的贻贝,虽然卖得很便宜,但却少有人问津。我特别喜欢,绝不会错过,买几斤回去略煮一下,待其壳张开时即起锅,挑出肉来蘸以鲜酱油送入嘴里。它的风味略逊于熟牡蛎,但还是感觉很鲜美。讲究一点的吃法还有:锅中放一片牛油,先爆香蒜茸,再倒入贻贝、料酒并加盖焖一分钟,最后撒盐、香菜等即可。记得有一回客人来访时,我做的菜肴中有一款汤菜,那是用瓶装西湖莼菜与贻贝肉烧制而成的汤,当天竟让客人赞为“真正的鲜汤”。
在《清稗类钞》中,作者介绍了“炒淡菜”的方法:取干淡菜一两,先用清水泡两小时至涨开后,洗净并断成小块,投入沸水锅里焯一下,捞出来沥干待用。另取青萝卜(去皮)二两,切成骨牌片;取摘去根的水发金针菜一两五钱,取水发木耳一两,分别投沸水锅里焯过。锅置火上,添入猪油、姜末及蒜末炸一下,再把淡菜、萝卜片等一起放进去煸炒,其间调入盐、酱油、味精等,最后用湿淀粉勾芡并淋上香油,即成。至于“煨淡菜”,则是用姜葱末先炸锅,下猪肉片炒至断生时,加入酱油、肉汤,最后下淡菜段入锅煨制成菜。
在民间,淡菜与萝卜是理想的伴侣:把萝卜切成方形,与发好的淡菜(置锅内先煮沸,再慢火焖至软熟,捞出来浸入清水盆里)一起入锅旺火翻炒,待其熟后调入味精、葱花,这下便可起锅。这样做出来的汤浓白,嗅感与味感都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