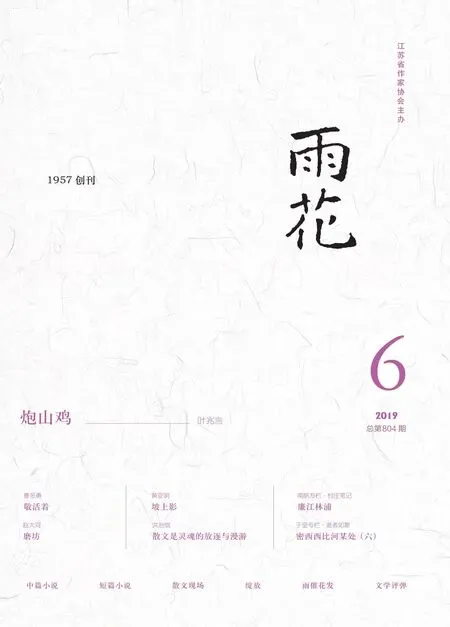散文是灵魂的放逐与漫游
洪治纲
散文是一种充满诱惑的文体。它可以写实,也可以抒情;它可以质朴,也可以妖娆;它可以感性,也可以思辩;它可以片言只语,也可以长篇宏论;它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遐思翩翩。很多时候,散文就像一个自由的精灵,无拘无束,收放自如,既能够尽情彰显作者的才情和思想,也可以充分展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散文的写作,与其说是传达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的体察、感知和理解,还不如说是呈现作者自我灵魂的漫游、放逐与怀想。优秀的散文,纵然写尽千山万水,远古今朝,终究还是为了体现“随魂赋形”的语言妙境,让我们从中体会到人生的诸多况味。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性情写作罢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所谓“性情写作”,原本事关性灵,追求的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遗憾的是,如今它已基本上变成一种作者感觉和情绪的滑行;虽也能形成一些佳作,但大多难以抵达作者灵魂的深处,也无法击穿创作主体的身躯,久而久之,甚至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感官化和同质化之境。说实话,这类写作曾经风靡一时,借助一些小风月、小情怀、小史实、小思辩,给人以“下午茶”般的轻松或释然,很难看到作家灵魂的妙曼之姿。有时候,性情还会变成矫情,散文的写作也就自然沦为风花雪月了。朱光潜先生甚至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学上的低级趣味,即“雅到俗不可耐”。我对这一看法举双手赞同。
就我的理解而言,重提“言志”写作,可能比“性情写作”更能切近散文写作的要义。因为“言志”能够更好地抒张创作主体的心性与灵魂,也可以有效杜绝滥情主义带来的低级趣味。袁枚就认为,好文章都是从心底流出来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故也。”我的爱好与袁中郎差不多,对“疵处”尤为在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打破了写作的惯性模式,颠覆了我们的日常经验,甚至给人以“另类”之感,可以洞察创作主体的心灵之质,发现作者灵魂漫游的特殊姿态。一个作家的散文,如果让我们看不到其特有的“疵处”,那是非常可怕的,要么是绝顶高手,人剑一体,绝无破绽;要么就是迷恋因袭,工巧而魂丧。
我之所以推崇“言志”写作,是因为它可以超越某些“载道”写作的局限,也可以规避滥情主义写作的危害,能够较好地呈现作者灵魂的独特与丰饶。事实上,也有不少作家自觉推崇“言志”式的写作,譬如周作人。周作人曾毫不含糊地说,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有篇文章叫《盘谷序》,名气很大,其实写得不怎么好,因为里面渗透了载道派的老毛病,相当的无趣。“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的,当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是不是韩愈的代表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章让周作人看到了一颗真实而生动的灵魂。所以,周作人认为,“写文章时不摆架子,当可写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边总是摆着官僚架子,在家里则有时讲笑话,自然也就是很真诚了。”写散文,原本确实不需要摆架子的。你的心志和情怀有多大,文章自然就会呈现怎样一种格局;你的思想和人格有多高,文章自然也会展示怎样一种境界。但中国是一个讲究诗教传统的国度,所以作家们总喜欢端起大架子,苦心孤诣地建构文章的所载之“道”,甚至养成了“思想不够,道统来凑”的写作习惯,导致很多散文都难尽人意。
唯因如此,我对那些端着架子的写作常常保持警惕,而对那些自由舒展的“言志”式写作充满迷恋。这类散文格调高不高,我倒不是特别在意,关键是有没有作者特有的机趣,有没有惹眼的“疵处”,能不能让我们与作者率性的灵魂进行“情与志”的碰撞。在我看来,三毛就是这样一个率性的作家。她的散文从来不摆架子,更不追求所谓的“载道”,只求将灵魂赤裸裸地安放在她的文字中,为世人呈现了一个自由精灵的飞翔之姿。说实话,她的散文当然也有“疵处”,尤其是她常常将想象与现实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界线,以至于凭借既有的现实经验都无法做到很好的理解。但也正是这些“疵处”,让我们看到了三毛那颗永不安分的灵魂,看到了她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将红尘中终日逐鹿功名的俗世男女甩出了几条街。
好吧,我们就以《撒哈拉的故事》为例,说说三毛散文的独特魅力。《撒哈拉的故事》是一部让很多青年人爱不释手的散文集,十几篇散文,讲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琐事,当然也有一些异想天开的冒险,超凡脱俗的情爱,旖旎奇谲的大漠风光。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里的每一句话都迸发出三毛的生命激情,每一篇文章都焕发着自由浪漫的气息,每一个事件中都跃动着一颗不安分的灵魂,这才是她的非凡之处。在她的笔下,沙漠中的每种景象都是如此的新奇;每种简单的生活都洋溢着异域的乐趣;千疮百孔的大帐篷或铁皮做的小屋,同样也有着格外的情调;单峰骆驼或成群的山羊,都体现出生命特有的气质。质朴而率性的荷西,相信粉丝就是人间特有的“雨”;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婚礼,却充满了人间无如伦比的幸福感;艰苦的日子里,他们用笨拙的方式在海边打鱼,同样让日子过得欢快异常;使使小性子、耍耍小脾气,流淌在笔端都成为浓浓的爱意……可以说,三毛是在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融入到大漠之中,才使她笔下的那些荒凉事物和落寂的人群变得摇曳多姿,充满欢乐。
在三毛的散文中,没有世俗人情的磕磕绊绊,没有独影自怜的哀哀切切,没有仰天俯地的怨声骂语,闪跃在文字之中的,永远是一颗率真、坦诚、自由、浪漫的不羁之魂。她的脱俗是源自生命深处的,她的浪漫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所以,读她的散文,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字的华美或妖娆,也不是故事的新奇或冒险,而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自由和浪漫,是作家的灵魂在无拘无束状态下的一种自我放逐与漫游,是作家的生命在不断出发和寻找中所体现出来的秉赋。有人说,她的写作是一种行走的文学,我基本上能够认同。但是,我觉得“行走的文学”这一提法,包含了某种危险——似乎三毛的散文是一种旅行散文。鉴于我们经常读到的山水游记之类,多半是没心没肺的浮光掠影式文字,间或还倡导一下人与自然的虚假和谐,我不太愿意将三毛的散文定义为行走的文学。
三毛的散文的确在行走中建构了自身的美学,但她的行走方式,不是身体的简单抵达,而是生命的全部融入;不是眼光的猎艳寻奇,而是心性的内在交流;质言之,是一种灵魂气质与行走之地在精神上碰撞出来的花朵。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梦想、有情怀的浪漫主义写作。在那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作家内心的某些无奈或感伤,但它不是以撕心裂肺的方式展示出来,而是在深深的怀想与欢愉的接纳中呈现出来的;在那里,我们同样也可以读到落寞和孤独,但其中却闪烁着理想的激情和自由的快乐,浸润着一颗感恩世界的心。它时时刻刻地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神话般的尊重,对自由精神的执着追寻,而不是终日面对世俗的欲望进行暧昧地叫喊,或提着道德的宝剑四处乱舞。
这便是我对三毛散文的理解。她的散文之所以华美,是因为她的生命本身就充满了浪漫情怀。她的文字有着超凡脱俗般的轻盈和欢快,是因为她的生命从来不会在人间烟火里唉声叹气。正因为她的灵魂是无羁无绊的,所以她的文字便显得天马行空。反观我们当下的散文写作,这样的境界却并不多见。太多的散文驻足于日常生活中的恩恩怨怨,驻足于城乡之间的差异性生活,驻足于现代人际间功利性的纠纠缠缠,或哀之叹之,或忧之怨之,或怒之斥之,虽也“言志”,但终究端着道德的架子,让人读到的都是怨妇般的脸色,却看不到让人怦然心动的灵魂气质。
我对散文阅读有限,但以我对当前散文有限阅读的经验来看,同质化的、浅生命投入的写作实在太多。华美的文字中,时常裹着一颗苍白的灵魂,而且这种苍白还似曾相识,甚至千篇一律。统而言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一些历史秘闻或史料八卦的还原性言说。这些散文似乎出奇的多,而且津津乐道于权术和诡术,把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融入其中,甚至还动用一些黑幕小说的叙述手法,以迎合市场的大众趣味。这类散文,偶读一些,还觉得十分有趣,读多了就倒胃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史料或轶闻,都是作者自觉去“发掘”的,猎奇的成分居多,并且与作者自己的心志并未产生内在的共振,导致写作中只能留下一些所谓的感悟或思考,看不到作者真切的情思。在这方面,张发财就很聪明,他常常以世说新语式的笔法,三言两语就表达得一针见血,智慧、眼光和风骨都可以显现出来。但有些作家就是喜欢东绕西转,一定要弄成一篇像模像样的散文才肯罢休,殊不知这种做派,隐含的无非是作者的一些小机趣罢了,连“载道”文学都算不上。说实话,我当年写作《清平乐》时,也干过,但写了三五篇之后,便觉得极为无聊,甚至有自损人格之感,遂不再写这类东西了。
二是对历史或现实苦难的聚焦式书写。中国作家很喜欢苦大仇深,十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谈当代作家的苦难焦虑症,虽然谈论的对象是小说,但在散文创作中也是过之而无不及。我看过很多关于打工生活、乡村生活的散文,绝大多数都是以悲苦为主旨,贫穷、无奈、无望,是其基本的情感路径,充满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和异常纯正的道德感。有些作品确实非常好,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在之痛。但问题是,这样的散文太多了,读着读着,就有一种苦难焦虑症的感受,好像中国作家都在关心民生疾苦,充当社会问题的代言人,希望引起社会疗救者的注意。有些散文,也难免出现一些虚假的道德关怀,希望以悲苦性的叙事,赢得读者在道义上的情感共鸣。我甚至想,哪怕这种现实的关怀真实无比且深刻无比,哪怕它诉说的苦难惊心动魄且梦魂牵绕,它都只能永远停留在“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初级境界。
三是对乡村自然生活的迷恋性表达。自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流行之后,十多年来,有关乡村的神话性表达变得越来越多。一座庭院,一驾马车,一把锄头,一头驴,或一棵树,一株野菜,一棵水稻,都成为一个巨大的载体,承载着作者对乡村生活或乡村伦理的无限推崇,也洋溢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某种诗意的人生理想。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别有意味的优秀之作。但是,读多了,仍然给人以同质化的感觉。它与乡村的苦难叙述,构成了两极的审美追求,虽然隐含了现代人回归自然的理想意愿,但在这种迷恋性的遥望之中,未必能映现作者生命的本质面貌。
简单罗列上述几种散文写作情形,当然不是为了否定它们的审美价值,而是基于我有限阅读的真实感受。我也想读到一些三毛式的激情散文,欣赏那些带着浪漫的灵魂四处飞翔的文字,品味那些自由精灵永不歇息的奔波历程,遥想那些不拘于尘世恩怨的烈焰般生活,遗憾的是,我视野狭小,很少读到这类散文。在我看来,中国那么大,世界那么宽,作家那么多,应该不缺乏各种样式的散文,尤其是不应该缺乏对生命的浪漫式怀想,对人生梦想的坚守。如果我们的散文始终过于强调现实性,强调经验性的同质化,我们就很难品味到作家超凡脱俗的创造精神,也很难真正地感受到文学的神性力量,当然也不太可能真切地领略到作家们博大精深的内在心智。
“我只是在描述我自己生存的时代之神话与梦幻。……我们需要用这些神话去照亮现实。”1996年7月的某一天,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兼布朗大学“写作自由”项目的主持人、教授罗伯特·库弗,曾对几位前来访问的中国作家如此说到。这里,库弗用了一个非常生动也非常有力量的词——照亮。是的,用神话去照亮现实,用梦想去照亮人生,这才是我们向往的一种写作,也是人们将永读不倦的作品,因为我们早已被千疮百孔的现实压得气喘吁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