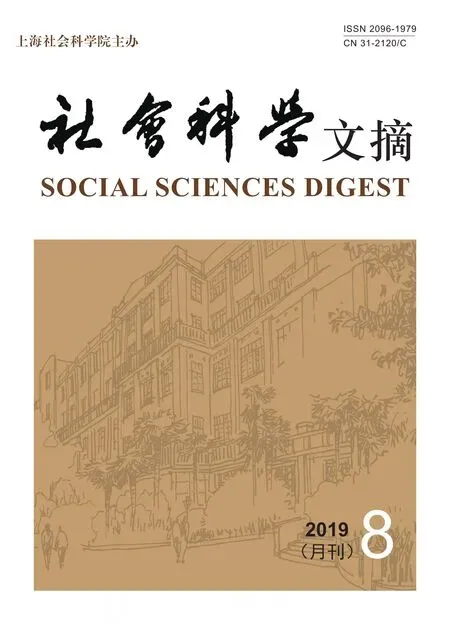公共安全产品视角下的国际维和行动供给
文/程子龙
国际维和行动是一项重要的冲突管理手段,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国际维和行动因其产生的集体安全效益而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但并非是一种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国际联合公共安全产品。联合产品(Joint Product)是指可以产出多种不同程度的公共性结果的公共产品,或者说是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组合成的中间产品。国际维和行动兼具了国际公共安全效益和供给方的私有利益。从国际公共安全效益来看,国际维和行动又兼有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的安全效益。在全球层面,维和行动可以抑制局部冲突引发的全球性威胁;维和作为干预手段往往还能避免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在地区层面,维和行动可以维护一个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减少地区大国不受欢迎的干涉行为,确保地区内稳定的商业发展环境,管理冲突地区内的难民外溢等问题。在国家层面,维和行动,特别是建设和平行动可以在当事国冲突停止、国内秩序尚待恢复之时,提供临时性的安全、政治秩序保障,往往扮演临时公共部门的角色。而且,建设和平环节中对于国家机构的恢复、重建又重塑了国内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分配,间接地促进了当事国的国家能力建设。然而,国家供给维和行动的初衷并非仅仅出于公益,更多地夹杂着供给国家的私利(contributor-specific benefits),例如,与冲突方之间的贸易、投资、安全等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或是单纯地从参与维和行动中获益。因此,国际维和行动是不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种“联合产品”,它既能产生针对于国际社会的纯公共安全利益,又能为特定国家集团带来不纯粹的公共利益,还能为参与国家带来具体的国家利益。维和行动只是一种中间公共产品,在全球安全范畴内,和平与安全才是最终公共产品。维和行动作为一个整体,或者维和行动中的具体任务,以及相关的国际机制和规范,都是为了生产和平与安全的中间产品。从这一角度来看,维和行动也具有“联合产品”的性质。
国际公共产品普遍存在着供给与消费不对称的特点,维和行动则尤为显著。通常情况下,维和行动都由两个以上的国家提供,而直接消费该项维和行动的则仅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他国家更多是免费享受维和行动带来的间接正外部性效益。因此,供给维和行动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较为独特。在提供维和行动的过程中,大国也存在着“搭便车”现象,而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小国,反而较为积极地参与维和行动,尤其是在提供维和军事人员方面,这主要是由于供给维和行动所特有的激励机制所导致的结果。最后,虽然消费方在消费公共产品时,不会轻易地被“排他”和“竞争”,只会选择放弃对产品的消费,但是,在某些国家享用维和行动时,有时会出现被动消费的情况,被强制手段强制实现和平,也就是说,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借维持和平之名行武力干涉内政之实的现象。
国际维和行动的供给模式分析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分工模式
维和行动供给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分工模式非常明确:西方发达成员国集中于为维和行动供给决策和资金;广大发展中国家集中于通过提供维和人员供给维和行动。以2015年为例,仅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八个国家就贡献了78%的维和经费,其中仅美国一家就贡献了28.36%,但这八个国家的维和人员贡献率则仅为3.3%。相比之下,前十名的维和人员派出国贡献了约53%的维和人员。从维和资金贡献来看,在1974年之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主要来自于联合国经常预算和自愿捐助。但是,自愿捐助原则引起了成员国间明显的“搭便车”现象,造成维和经费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为此,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12月11日通过《3101号决议》,不得不将自愿捐助改为维和摊款加自愿捐助制度。联合国根据每个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制定不同的分摊比例,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摊款份额,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正常分摊配额上多增加了22%的摊派任务。因此,联合国发达成员国贡献了绝大多数的维和经费。
从维和人员贡献来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贡献大国通常并不是人员贡献大国。有别于强制性的维和经费摊派制度,成员国贡献维和人员完全出于自愿原则。鉴于此,贡献国派出维和人员一定是基于多方面因素考量的结果,例如,冲突的性质、危险程度、潜在的伤亡率、出兵国的军事实力、与冲突当事方的关系以及与冲突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都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如果排除掉其他因素,仅考虑维和人员的派出成本,成员国间的供给存在着很大的成本差异。因此,维和行动往往划分为富裕型维和行动与贫穷型维和行动。虽然联合国会为维和人员提供补贴,为提供的装备进行一定比例的报销,但仍不足以贴补到发达国家的供给成本水平。尽管如此,大量发展中国家往往还是能从维和行动中营利,这也是导致成员国间出现维和行动分工最重要的原因。维和行动的危险性和伤亡情况以及一些政治因素,是导致发达国家减少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维和行动的代理供给模式
联合国是维和行动最为主要的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全球大国、地区大国都在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还出现过大量联合国框架之外的非联合国维和行动。根据维和行动供给者身份的不同,这些行动大致可以划分为独立国家领导的、国家自愿联盟(或临时性的国家自愿联盟)(coalitions of willing or ad hoc coalitions of willing)的,以及区域组织安排的维和行动。这些行动中部分得到了联合国授权,而有些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在2014年之前,非联合国维和行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人员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联合国框架内的维和行动。
从国际维和产品供给这一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本文认为两者间存在着一种代理的关系。维和行动的代理供给模式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有必要创建一项行动,但没有一个行为体有能力或意愿承担这项维和行动,或是完全承担该项行动的全部任务时,作为主导该项行动的行为体,会将全部维和行动或部分任务交付于另一方来执行。根据该定义,维和代理模式包含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存在一个需要建立维和行动的紧张局势,该局势涉及诸多攸关方,建立行动具有必要性;二是各攸关方都仅具有部分意愿、部分能力来实施维和行动,而其中的潜在主导方也只是在相对层面上更有意愿和能力实施维和行动;三是代理模式的实质是将全部或部分维和行动进行外包,例如部分维和物资的筹措、具体专业事项的委托以及强制和平职责的移交等。以联合国为主导方的维和代理可以理解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但出于某种原因导致它们决定不能或没有意愿建立一个必要的维持和平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将这项行动交付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自愿联盟或国际组织加以实施,并通过授权决议建立联合国与被委托方之间的代理关系,明确规定由代理的接受者来组织并执行该项行动。
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之间的代理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非联合国维和机制作为代理人,由联合国委托从事一项维和行动,或履行一项维和行动中的部分功能。这一类代理关系的典型范例包括:一是北约2015年1月开始在阿富汗执行的“坚定支援行动”(Resolute Support Mission),该项行动是应阿富汗政府要求而向阿富汗安全部队和机构提供培训、咨询和援助的非战斗任务,并从联合国安理会2014年12月通过的《2189号决议》中获得授权;二是北约1992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执行的任务,体现了北约代理履行联合国在亚得里亚海执行武器禁运和设立禁飞区的某项具体职能。第二类是联合国作为代理人接受非联合国维和机制委托来履行某一项维和行动中的部分功能。鉴于联合国是国际维和行动中最为重要的权威机构,因而不可能出现联合国获得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之外的授权而执行维和行动这种现象,但联合国可以凭借伙伴关系为其他机制的维和行动提供支援。这一类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两个:一是联合国应布隆迪副总统邀请于2004年接替非盟驻布隆迪特派团(AMIB)执行任务;二是联合国自2009年起通过维和行动经费为非盟在索马里行动(AMISOM)提供大部分后勤和装备资助等。
国际维和行动供给模式产生的动因及其影响
(一)国际维和行动供给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动因
导致国际维和行动特有的供给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和产品“联合产品”的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际维和行动的供给模式是维和供给方私有利益占维和总体利益的比重计算的结果。一个贡献维和行动的国家的效用(utility)取决于它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的收益、贡献非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收益,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总体贡献水平之间的计算结果。而这个国家贡献维和行动的根本动机则是其私有利益占维和行动总体利益(维和公共利益+贡献国私有利益)的比重,这个比重越大,该国贡献维和行动的动机就越大。在国家确认贡献维和行动会有很大收益时,该国仍会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还是非联合国维和行动间进行抉择,因为非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加偏向于私有利益导向。
其二,代理模式是强力维和手段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运作。联合国一向主张维和行动是一项政治手段,但为了确保维和的有效性,并积极发挥“保护平民”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维和任务包含了强制和平的因素。联合国中的部分成员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仍然坚持并鼓励使用强制和平手段。它们在联合国决策受阻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往往会通过其他国家或组织来运用强力手段。因此,发达国家在减少联合国维和人员供给的同时,却扩大了非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的数量。随着维和环境越发严峻,维和人员和平民受武力威胁的状况越发严重,维和行动中的武力使用已不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该如何使用”的问题。联合国将强力手段代理出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权宜之计。
其三,国际维和行动供给模式是维和机制间资源、能力互补的结果。随着维和行动任务更多地向民事活动和国家能力建设等建设和平维度的转向,专业性较强的功能正在外包给一些专业的公民社会组织。这样,各维和机制之间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相提供资源,实现了能力互补。此外,对于“地方自主权”(local ownership)的强调以及区域组织执行的维和行动更易被区域内国家接受等因素,也都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维和代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二)国际维和行动供给模式产生的影响
现有的维和行动供给模式形成后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导致联合国维和权力一定程度的流散,但是并未削弱西方国家,反而增强了其自身参与维和行动的灵活性。联合国维和权力的流散主要体现在维和行动的决策和部署权力日益流散到地区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以及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甚至是跨国公司手中。其二,导致维和行动人员贡献总体呈现出不稳定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装备质量和人员素质也都难以得到保障。其三,极大地模糊了维和行动中的武力使用原则。在联合国框架内,由于多数国家坚决捍卫联合国维和“三原则”,维和武力使用仍能受到较好规范,但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其他维和机制对于武力使用规范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更容易受到西方大国或地区大国的左右。从根本上说,国际维和行动供给之所以呈现出现有的模式,除了其自身的公共产品属性外,也体现在联合国对于维和行动演变的妥协,在联合国无法满足部分成员的利益时,或是暂时无法实现理想的维和行动改革之前,部分成员国可以灵活地跳过联合国,采取对自身更为有利的维和行动。
对中国供给国际维和行动的几点看法
中国在冷战期间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抱持谨慎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从谨慎和不参与,逐步发展为越发关注和深入介入。中国参与的维和行动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代理模式,但支持联合国建立广泛的全球维和伙伴关系。未来,随着中国的维和政策越加灵活与开放,不排除中国成为国际组织的维和代理方,或委托其他行为体执行维和行动的可能。
(一)中国增加国际维和资金与人员供给是否会引发大量“搭便车”问题
中国扩大维和产品供应存在着其他供给方因而减少或不愿提供供给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可避免地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克服该问题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中国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对于维和行动的供给。中国应减少参与行动方过多且已经包含了贡献大国的行动。因为这类行动较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并且,中国很难在此类行动中承担领导角色,获得额外收益。二是中国应创造更多的选择性激励机制(selective incentives)。中国可以选择为他国的维和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一定的装备支持,或是在冲突后重建中为供应方营造更多的贸易、投资机遇等,也可以通过在非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激励他国增加维和供给的手段。
(二)中国应在通过建立代理模式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护国际维和行动的规范和原则
联合国仍然是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主要平台,在此基础上,中国应通过代理模式保持维和行动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在联合国之外的维和行动中,中国既可以是行动发起者、重要参与方,也可以是某些任务的代理方或委托方,这取决于维和目标对于中国自身利益的权重大小。中国通过代理模式贡献维和行动,将有助于维护国际维和行动的规范与原则。中国应将合作重点集中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援助、医疗救助、扫雷等。
(三)中国应思考如何在既有供给模式中精细化维和行动内容,同时建立更加广泛的维和伙伴关系网络
中国应该因时、因地提供相适宜的维和行动产品。中国当前的投入仍过于集中在“硬”基础设施层面,在诸如维和制度设计、塑造和平安全理念,以及传播治国理政经验等这些“软”基础设施层面还存在很大欠缺。未来,中国应进一步精细化、精准化维和产品的设计与供给。维和产品的充分供给和维和行动的有效执行更需要建立全球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从国家层面,中国应加强与其他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的维和合作关系。从国际组织层面,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应强化与地区组织、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注重和尊重东道主的地方所有权(local ownership),以便更好地协助地区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中国还应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重视这些组织在维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这有助于传播中国的维和贡献。再者,中国还可以适当鼓励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前往维和任务区协助执行人道救援、冲突预防等领域的任务,这既顺应了自下而上的安全治理发展趋势,也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人道主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