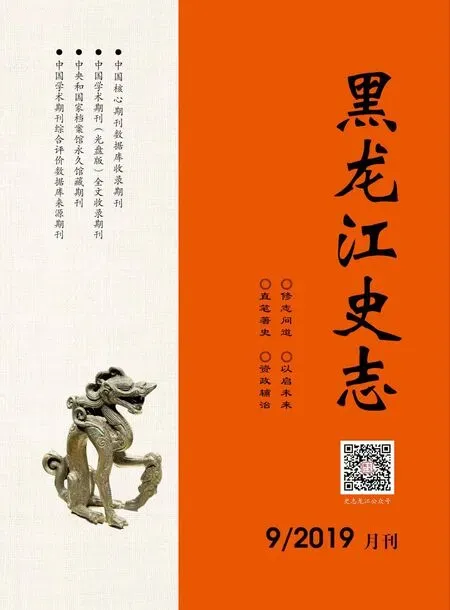淹博而贯通 思辨有情怀
——读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邢誉田
(武威市第十八中学 甘肃 武威 733000)
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自出版以来,广受赞誉。笔者一直较为留意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通”“论”结合,卓见纷呈,正好满足了笔者的这一需求。时隔多年,再次翻阅,现将几点读书笔记分享于下,以备同仁一晒。
一、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学界因旨趣各异,歧见纷呈。《中国历史通论》也突破教条,接续前贤,深入思考,将三皇五帝之后的中国古代史划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三个阶段。
关于部族时代的概念,作者借鉴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谷城与吕思勉二先生的思路,采用了抉发于中国典籍的旧词,立足于本土概念的阐发,阐述了人类社会以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聚落”为基点,由小家庭—家庭—氏族宗族到部族、方邦的演进之路。而从“部族时代”进入“封建时代”,作者认为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是大大小小‘方邦’分合离聚历史运动综合生成的一个局面,其间很难有什么明确的标志。假若有,那就是大的‘方邦’成为核心‘邦国’”,即作者所称“联邦”式的“中央王国”的出现。[1]44而这种最初的核心邦国,即殷商,作者名之为“封邦联盟”。其虽然已存在“封建”,即对其臣服诸属国的承认,但并不像西周,还在别的邦国地域内“掺沙子”式地插进自己亲手分封的“邦国”(即“封建亲戚”)[1]53。以此,作者将其与西周的“封邦建国”做了区别。
如果说商已有“封建”,并成规模,那么西周则形神俱备,已成典型。王家范界定的“封建时代”,即是指“以西周为典范的一个时代”,“它经过春秋战国的逐渐崩坏,转入秦帝国大一统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时代’即宣告结束。”[1]38至此,中国历史演进经历了由“方邦”而“联邦”到最后更大地域性“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要揭示传统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规律,就要以土地制度为基点,系统考察土地制度、国家权力、社会控制的变迁过程。”[10]梳理王家范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划分与界定,如学者所论,体现了“精到与贴切”[11]。如在“部族时代”的论述中,作者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方法,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土地关系、权力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初阶段的演进轨迹,较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本质样态”。
二、中国古代的土地权属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土地为谁所有的问题,学界曾经一度落实到土地的所有制形态上,并且主要着眼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所有权)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古代土地问题的复杂性,使这一问题长期争持不下。有鉴于此,王家范从对通史界普遍接受的自商鞅废井田、“民得买卖”,中国土地私有制出现,到秦汉之后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的质疑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土地“所有”问题做了一次长程的辨析。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由于经营从早期的氏族聚落开始一直以小家庭为主,因此,作者将分析的进路主要放在对收益权和处置权,特别是收益权的论述上。因为“农业的产出是按多少种形态分割的,不同身份的人在这种分配中的收益比例,都是判断产权性质不可忽略的事实依据”,对分配结构的分析,是判断产权的关键。[1]96循着这一思路,作者展开相关论述。
部族时代,由于土地归共同体集体享有,因此作者名之为“集体共有制”。至于不采用“公有制”,是因为“产权也是有边界的,共同体的疆界就是它的边界。”土地的享有对于血族群体之外的部落是难以一秉大公的。这一阶段收益权由三级(村落聚落、氏族、部落)分享,不存在任何称得上“私”的产权。随着部族演进到“部族国家”以至“共主联邦国家”时期,产权形态亦随之复杂化。“原有共同体的‘集体产权’被纵向提升为最高共同体‘所有’,成为‘部族国家产权’或‘联邦国家产权’,而收益权则增加了向最高共同体纳‘贡’的分割份额,并逐级向下分摊,经营则仍维持个体家庭耕作的模式。”[1]101在这一过程中,产权的“共有”性逐级被稀释,而王作为最高共同体的象征,集体产权的“法人代表”,随着军事征服疆域的扩大,其代表的产权由于奠基于扩展的权力而体现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谓,并渐次演变为一种“历史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产权体现的收益分配,则通过贡、助、彻三种形式来实现,“其份额大体保持在收益十分之一的比例上。”[1]106但由于管理的层级化,各级“代理人”在完全脱离耕作经营的同时,却享有收益权分割份额的特权,时日既久,便存在着“代理人”异变为国有产权实际处置者的可能。与此同时,“法外”私田在春秋战国时期因诸侯垦殖隐秘不报以及“军功授田”的推行而大量出现,尤其后者,由于当权者机会主义的考量,促使土地买卖的限制被突破。
入至大一统帝国时代,产权随时势的演进而更趋复杂。作者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是“黔首自实田”的问题,二是自耕农实为“国家佃农”,三是“土地兼并”问题。作者认为,秦时的“黔首自实田”实为之前“授田制”的进一步扩大,受田人的资格要求也从侧面证明了农业耕地的产权国有性质;一般而言的自耕农,由于正税之外的各种摊派与役使,实际上沦为“国家佃农”;至于土地兼并,虽然自秦汉至唐中叶,“国有”产权的实际控制力在步步后退,但国家反兼并的努力一以贯之。从唐“两税法”开始,“‘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收益权’上做足文章。”[1]131王家范指出:在两千年的大一统体制之内,“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通过赋税、徭役或正常或非正常的行政法令随时都可以‘化私为公’。”于是,中国古代的产权便体现为一种独具的历史特征:“‘公’与‘私’的两种要素犹如阴阳两极,负阴而抱阳地包容于这种特殊的‘国有’产权观念之中,在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产权模糊和动态变化的特殊权利结构。”在此结构之下,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而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重要造因或即埋伏其中。[1]537
三、明清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传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界说,主要依据吴承明的看法,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因此,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就需讨论生产关系,判定其是不是雇佣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反思以及这种研究范式的退场,学者对明清经济的研究出现转向,如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理论,一改过去过分注重生产关系、忽略生产力研究的状况,而成为当下史学界关注的新方向。[2]王家范在本书的分析中,也撇开江南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而是从专制体制下,江南的繁荣局面何以形成,是否为真的繁荣的角度,间接地回答了上述议题。
首先,从国家赋税征收来看,“一条鞭法”推行,赋税货币化,固然有把农民进一步推向市场的作用,但赋税项目并未单一简化,税额并未减少,政府的各种摊派依然所在多有,农民的负担还是有增无已。其间还不包括在地亩的清丈上即已存在权势之家与书吏暗通款曲欺压百姓的弊窦。其次,从农民的收入来看,耕种所得,交纳地租之外仅够支付口粮、衣着、农本之需,剩余部分,则全靠棉织所得。以上还不包括水旱灾荒的影响以及政府各种叠加的摊派。一般农民之外,明清江南庶民地主的境遇也因政府不时的差役负担而常有“以田为累”的感慨。再次,从丝绵的流向来看,“政府公款购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头”[1]604,因为明代军队特别是北部边防军事装备对棉的需求量极大。至于一般民众,丝绵主要用以换钱交税、补贴生计,而非自己消费。综上可见,江南由于为国家财赋重地,农民负担沉重,为了弥补收支缺口,农民不得已织棉、缫丝。所以,生产是为了变缴赋税的谋生,而非商品化的谋利,也因此“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成本经营水平线上”[1]554。在此基础上显现的市场繁荣,实际上是“一种以国家财政作为市场购买力重要来源”[1]604所导致的“假性繁荣”。
农业农民之外,与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传统商人阶层,其经营与成功之道又如何呢?在作者看来,近代早期的中国商人,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投资于生产领域,所谓的豪富,并不是真正的“资本阶级”,“他们大都是靠官商勾结,靠政策的‘特许优惠’,异常活跃于流通领域,稍有头脑者即使将部分资金转移于购买田产,也只是为自己留后路,坐收租金,不思经营。”由于与权力共生纠缠,因此“政局大变或权力背景一倒,他们的财富也往往灰飞烟灭。”[1]606可见,近代早期的中国商人,其经营思路不外是立足土地,输来运往,少有积蓄,又回归土地,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依然不脱以土地为中心的传统农本思维。追溯其渊源,与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专制体制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不无关系。和欧洲相比,古代中国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能够和王权相抗衡的工商阶层,工商业的发展始终突破不了专制王权的藩篱,“工商依附于政府”,官商结合倒是中国商业发展的大传统。[1]555
以上是笔者对《中国历史通论》初步的阅读与感想,虽然该书的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不无商榷的余地,但由于本书议题丰富,学术信息量大,且取精用宏,意境高远,为作者积四十余年之功所成,溶入了作者丰沛的生命体验,因此需读者后学反复翻阅揣摩,方能体味作者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