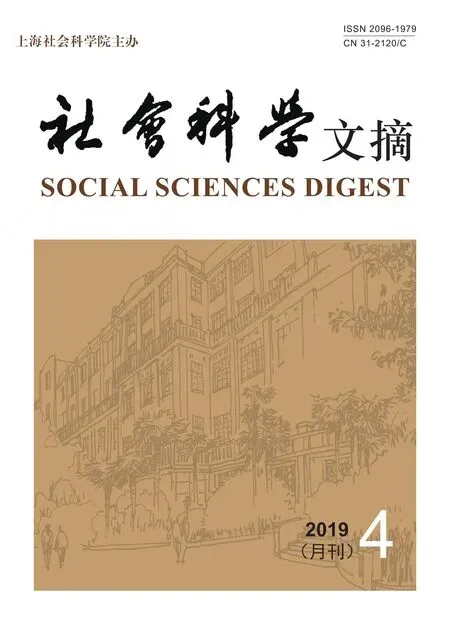对王维“诗中有画”的再讨论
自拙文《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发表以来,学界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发表多篇商榷性的或延伸性的研究论文,我一一拜读,收获不一。今重拾旧题,补足前论,以期作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诗中有画”的“画”指什么?
《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立足于绘画的造型性,以此衡量王维诗歌的艺术特征,从而质疑“诗中有画”的命题是否适用于概括王维诗歌的主要成就,并进而思考“诗中有画”作为批评术语,其意义是不是被夸大了?关于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争论的双方都没有事先界定物质画与想象画,也混同了‘有画’与‘可画’的含义”。这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看似具有学理上的反思色彩,实际上却未斟酌“有画”和“想象画”的概念是否能成立,或是否有意义。在我看来,“有画”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无法界定其内涵,历史上许多诗人,包括杜甫的作品都被说成有画,但没有人关注那些作品的绘画性;而“想象画”只能勉强说是一种心理表象,恐怕不是讨论诗歌文本适用的概念。
浏览这些续出的论文,可见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对“诗中有画”之“画”的理解。按常识说,这里的“画”应该指绘画的特征和意趣,即绘画性或者说造型性。但商榷者都不这么看,他们提出诗中有画的“画”乃是指中国画特有的意境,而认为我对“画”的理解太拘泥,未理解中国画的美学本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画特有的意境又是什么呢?不就是象征意蕴么,或者说不就是诗意么?这么一来,“诗中有画”在他们的解释中就变成了“诗中有诗”,这样的循环命题显然是无助于讨论深入的。
我也反思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苏东坡的命题其实提供了两个讨论的角度:价值估量和话语分析。《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的讨论出于价值估量,观点已表达得很清楚。这里我想再尝试作一番话语分析。这一研究已有学者进行尝试,基本观点是东坡所谓“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判断,而是对王维个人诗、画特征相互渗透现象的直感。这种话语分析的方法不是要考究东坡说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而是要究明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要对王维诗和画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认识,立足点已转变为对苏东坡艺术思想和见解的研究,与对王维艺术特征的认识不是一码事了。
由于宋代文学艺术总体上为“破体”——不同艺术门类、不同体裁的艺术特征相互交融、渗透的风气——所笼罩,诗画艺术的交融尤其是画家自觉地追求抒情性也是当时的流行思潮。这就让人很自然地向诗画互相借重对方所长的方向去理解诗画关系,将“画中有诗”解释为画有诗意,“诗中有画”解释为诗有画趣。这绝不是我的穿凿理解,事实上宋人对于王维诗,的确说过:“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宣和画谱》)但这只能说是后人的感觉,王维的创作理念究竟如何,终不能起九原而叩之。既然我们无从断定苏东坡的说法是否符合王维本意,就只好据其所说作一番话语分析了。而话语分析的前提,是要求回到东坡命题的语境,关注他发言的艺术史和美学背景。研究者指出,诗歌和绘画创作在唐代都进入一个繁盛时期,两类艺术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也日渐突出。到北宋诗画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以苏东坡为代表,艺术家们在理论、实践两方面都有一些探索。随着文人画、写意画主体地位的确立,诗歌和绘画在表现作者人格精神的最终指向上趋于同一,由此产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这一论断我总体上是认同的,但具体思路觉得还有展开的余地。
“诗中有画”的“画”作为王维画意
当我们将考察的中心由王维诗歌转移到苏东坡的艺术观念上时,问题马上就与艺术史上足以同文化史上的唐宋转型相媲美的观念变革联系起来。日本学者浅见洋二考究殷璠《河岳英灵集》所谓“着壁成绘”与六朝以来“雕绘”“雕画”“图缋”“画缋”等词的渊源,认为那是指一种人工色彩强烈的艺术美,并推想王维诗在当时就给人这种印象。他的研究着眼于中国文人如何读诗,在他看来,“所谓诗的绘画性,或所谓诗与绘画的接近、融合,最后仍与怎样读诗的问题有关”。此言深得我心。
上文提到,宋人读王维诗,“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说明他们从王维诗歌的画意中看到的是作者的高情逸致。这一方面体现了宋人尚意的美学旨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王维诗之画意的感受不是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绘画性,而是着眼于王维诗体现了他本人绘画的某些审美特征。这样,我们的讨论就重新回到学界早就涉足的思路上来——考察王维绘画的艺术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在诗中的表现,说明它们给王维诗带来了什么特色,然后评价其历史意义。
从美术史的语境看,东坡对王维诗的论断,相信与他对王维画的认识有关。我们知道,苏东坡是非常推崇王维画的,他在王维的壁画中看出王维诗既清又不失其厚的美学特征。这似乎这也是古代艺术家惯常的思路,反过来也可以说知画者乃知其诗。黄公望论钱选画,说“知诗者乃知其画”,即肯定钱选的诗歌表达了其绘画的境界,能懂得他的诗便能懂得他的画。为此清代画论家笪重光曾将诗画相通的原理概括为:“故点画清真,画法原通于书法;风神超逸,绘心复合于文心。”而诗人乔亿更具体论述了王维诗具有与其画同样的美学风貌:“以画论诗,李、杜歌行,荆、关、董、巨之山水也;唐初四子歌行,思训父子之金碧山水也;摩诘之诗,即摩诘之画,意致萧散中自饶名贵。”至于苏东坡,陶文鹏先生已指出,他对诗画的艺术界限是有清醒认识的。虽然学界考察东坡对绘画特性的认识,对他论画重传神已形成一致看法,但我们仍可以肯定,东坡对绘画的造型特征有着清楚的意识,他对诗歌“写物之功”的理解并不向绘画的造型性靠拢。
东坡明显将诗的写物之功限定在能够捕捉事物的形象特征及与特定环境的关系,而非概括性的一般说明。那么,他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理解是指这种写物之功吗?更进一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就是对王维诗、画具有共同的美学特征即乔亿所谓“摩诘之诗,即摩诘之画”的认识吗?
在考究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应该肯定,苏东坡对绘画的认识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刘石认为东坡已“开始突破了仅仅以画家身份定义文人画的皮相之论,成为绘画史上较早系统提出文人画理论的学者”。东坡有关文人画的理论有三点值得重视:(1)在绘画原则上强调神理象外,不重形器;(2)在绘画功能上强调达心适意;(3)在绘画风格和意境上强调意气所到,清丽奇富,变态无穷。刘石看法是,东坡评价王维的两个命题隐含着对王维画风的认知,即王维的画具有他诗的那种意境。我很赞同这种见解,虽然我们尚不能坐实这一点,但通过南宗画的传统间接地体认王维绘画的艺术特征,也能获得到一些验证。
王维画的写意倾向
作为画家的王维,在美术史上有多方面的贡献,但他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南宗画的鼻祖,二是开士人画风。
“士人画”之名始见于苏东坡《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为此前人或认为士人画的概念出自东坡(如邓椿《画继》卷三)。这是不对的。谢赫评刘绍祖已有“伤于师工,乏其士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引)的说法。可见这种观念由来甚早,只不过“士人画”的概念现在始见于东坡文字而已。到明代以后,以“士气”称许文人画的精神已为老生常谈。所谓的士体、士气,与师工、匠作、画师、工笔对举,都指有别于画师、工匠之作的士大夫画或者称文人画特质。前人追溯这种特质的由来,王维之前更无古人。王维之所以被奉为南宗画的初祖,正因为他的水墨山水开创了文人画的新风。
历史地看,南宗画的艺术精神以写意为主,不重写实,强调文人画的士大夫气。在乾隆间画家王学浩,嘉、道间画家李修易心目中,士大夫画无非是以写意为核心,意在笔先,纵情笔墨,不事刻苦,不重写实,唯以意趣自足和气味古雅为尚。然则我们就是直接在写意与士气之间划上等号也不为过吧?
写意一方面意味着不拘泥于对象的真实,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不作写实性的描绘及忽略细节。南宗画尚写意而不刻画,在用笔上就变线条而为渲染,不用骨法而以气韵胜。在风格倾向上,南宗用笔疏简,出韵幽淡。论者对南宗画技法特征和艺术风貌的概括、描述,都旨在强调,洋溢着文人气息的南宗画,能以潇洒的写意性克服工笔刻画的繁缛琐细,独造一种气韵冲淡、神情幽远的意境,其画面之意境流动着天机,透露着逸趣,随处可见作者的人格和襟抱。这种不是强化而是抑制造型性,同时突出作者主体性的画法,的确有着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诗意,不妨称之为“画中有诗”,实质上就是中国画的抒情性亦即写意倾向。画家的创作冲动,首先起于感受到物色景象的诗意,而且是特定的诗意境界,然后以画笔赋形,于是成就古人所谓的“无声诗”。这便是“画中有诗”的原理,如果我们将它视为中国画的特质,说王维诗中有画的“画”即指这种特质,那就不啻是在演绎一个“诗中有诗”的循环逻辑;而如果将苏东坡说王维“画中有诗”理解为可从王维的画中感受到他诗歌的意境,即那种清空澹远、隽永灵动的诗趣,则不能不说是过人的深刻感悟。同理,若将东坡的“诗中有画”解释为王维诗有着绘画的造型性,那就不仅在学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也大大遮蔽了王维诗歌夐绝的艺术造诣。因此,只有将“诗中有画”解释为王维诗中含有他自己绘画的意趣,才可以将王维诗歌的艺术表现与其画风对应起来考察。
王维诗的写意特征
王维画因负当世盛名,论者往往先入为主地设定其诗与画同出一源,而从取景、构图、用笔、色彩、光影等绘画的各种要素入手,寻找它们在诗中的种种表现,以见王维诗歌总是不经意地露出画家本色。按这种思路来评论王维诗歌的论文已发表很多。这种批评方式虽然不失为认识王维诗歌的一个途径,但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流于主观化的危险。如果我们同意说苏东坡的“诗中有画”是指王维诗中可见其南宗画风的某些特征,那么首先就应该从他描绘景物的写意特征来印证这一点,因为南宗画风首先是以写意而非刻画见长。而我们一旦从写意特征来看王维诗对外部世界的描写,就会从艺术表现到风格层次都得到一些异于往昔的新判断。
我们先要转变一下习惯的反映论思维方式。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表现取决于观察,而是观察取决于表现。绘画所展现的内容并不是观察的结果,而恰恰是选择的结果,以往被视为素材的形象其实是写意的符号。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最大程度地强化了这种写意特征,这是举世公认的。王维诗歌对景物的处理也明显可以看出写意化的倾向,这在许多侧重于造型性,紧扣构图、色彩、光线等视觉要素来分析王维作品的论文中都被忽略了。
在《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一文中,我已分析、说明王维诗习惯将空间存在转化为时间过程的动态表现模式。尽量避免静态描写的效果,用诗学的语言说就是去赋笔化。去赋笔化意味着脱弃单纯的白描、形容、比喻等呈示性要素,而采取以景叙事、离形取神、淡化线条轮廓、忽略细节等方式来造成整体上的写意特征。以下试分述之。
先应该确认的一点是,王维那些被论者目为山水田园诗的作品,大体是沿袭谢灵运游览纪行诗的写法,以叙事为主调,风景描写其实着力不多。
由于写景承担着叙事的功能,王维笔下的景物大多是粗略点染,不事刻画。中国画的写意特征是,无论风景或人物都仅抓住主要特征,而不作细节刻画,这使形象的表现机能带有强烈的程式化亦即符号化倾向。具有写意倾向的王维诗歌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王维诗中的景句,一定是浑融疏略的写法占主导地位。王维写景的特征,取疏而不取密、取神而不取形、取浑沦而不取刻画是其大旨。这其实也是整个盛唐诗风景描写的主导倾向,不只王维如此,同时代的大家、名家莫不如此。由此可以间接地理解,盛唐诗歌风景描写的基本倾向就是浑闳不切,不拘泥于细节刻画。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断然否定王维诗中存在细腻的景物描写。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王维放弃写意化的表现而致力于细腻的刻画,就意味着他同时也离开了写实而进入意象化的表现方式。这时他往往用非常突出的意象来构成场景,使景物成为渲染氛围的媒介。这种意象化的表达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方式的先声。我的看法,情景交融的意象化抒情模式是在大历诗中定型的,王维诗中这种意象化的苗头,涉及唐诗写作范式演进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专文讨论,这里姑不展开。
以景叙事、离形取神、淡化线条轮廓、忽略细节,这些特征的交集,就造成王维诗出韵幽淡的意趣,整体给人艺术表现淡化的感觉。尽管有许多为人称道的写景名句,却少有以刻画见长的例子。王维诗中风景所留给人的印象,就像他的水墨画一样,无非是一个“淡”字,它是艺术家从胸襟之淡到笔墨之淡的全程体现。
结论
如果上文对王维绘画特征的概括大致不错,那么就可以肯定,苏东坡能从王维诗中看出这些特征,是很有眼光的。问题是这些特征是否为诗歌中前所未有,纯属画家王维移借了绘画的艺术精神呢?
回顾诗歌表现的历史,从南朝到初唐这个阶段是形似的追求走向极致的过程。虽然它对于唐诗艺术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资源积累,但在后人眼中,“其时脍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等诗,本色无奇,亦何足艳称也?”(叶燮《原诗》外编上)确实,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来说,这类出以赋笔的名句绝不是诗歌最上乘的境界。王维诗歌的写景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超越了以雕琢求工的妙品,而臻真境湊泊的神品、平淡真率的逸品境界。这与他绘画的写意精神正相一致,具有反对和超越造型、平面等一般意义上的绘画性的倾向。这种写意化倾向融入诗境,强化了超越绘画性的动态特征,不仅实现了诗性对“形似”的超越,同时也使诗歌中的风景由自在之景向意中之景过渡。中国古典诗歌最核心的审美特质——情景交融的意象化表现——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正式开启了它日益占据诗歌美学主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