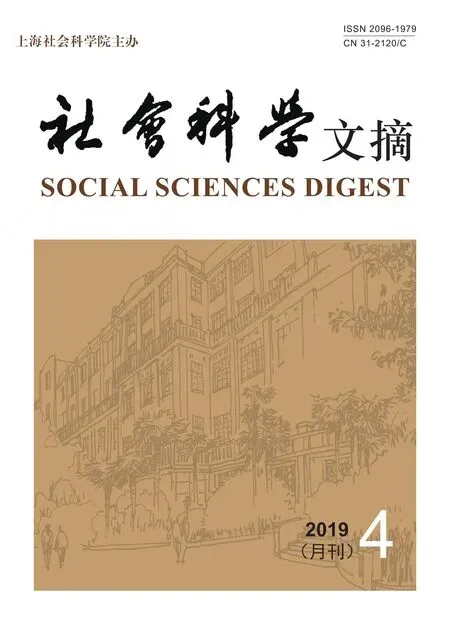老年、艺术与政治: 《当你老了》与爱的逃离
《当你老了》写于1891年10月,叶芝时年26岁,刚于两月前向摩德·冈求婚被拒。此诗确实与冈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如果将整个阅读的框架完全根基于自传式的青年人在恋情受挫时的激烈情绪反应,则贬低了文本的形式在表达内容和探索思想时的力量,忽视了叶芝关于灵与肉的思考的复杂性,忽略了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探索,也遮蔽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爱尔兰民族文化与政治运动这一背景。
叶芝诗歌从早期至晚期持续关注着老年这个主题。叶芝研究者乔治·伯恩斯坦称之为叶芝整个创作生涯的执念。在叶芝的诗歌中,老年概念往往脱离仅与年龄相关的社会学式思考,而成为关于生命、历史、文化、创作和社会的整体性思维的一个切入口;即便在诗中老年与青春构成对立关系,也是在威廉·布莱克式的纯真与经验的对立框架下的建构,即其建构目的最终为批评现实观念中二元对立的状态,要求超越对立关系、建构新的统一体。
叶芝与爱尔兰
在与爱尔兰民族命运和身份认同相关的活动中,叶芝与冈于1889年1月相识。两人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积极投入繁忙的公共生活。叶芝的活动主要在文化领域,他创建文学社团,还热忱参与神智学与神秘主义社团的活动。他使用英语语言并结合爱尔兰文化历史传统的写作方式是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重要脉络。1889年,叶芝开始写作以16世纪爱尔兰饥荒与英国的掠夺与压迫为背景的诗剧《凯瑟琳女伯爵》,并在该剧引言中称,是冈提供了写作的灵感。冈的活动侧重点主要在社会政治领域。结识叶芝时,她关注贫苦爱尔兰农民的生活,并募集款项为失地爱尔兰农民提供栖身之所。1890年,冈已克服了19世纪对于女性参加政治活动的种种限制,公开讲演,为一位格拉斯通派的候选人助选。
1891年10月6日,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帕奈尔病逝。冈从英国本岛回爱尔兰时所乘坐的恰好是运送帕奈尔遗体的邮船。船在10月11日清晨抵达都柏林,同一天举行的葬礼据称有20万人参加,冈也在其中,而叶芝则表示不喜欢参加这类大型政治集会,未去参加。
“爱的逃离”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在借鉴法国文艺复兴诗人洪萨《致艾兰的十四行诗》之一《当你老了》的基础上,叶芝于1891年10月21日写下《当你老了》。洪萨是七星诗社的重要诗人,而七星诗社的关注方向之一是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强调通过法语而不是拉丁文写作来丰富本土语言、振兴法国文学,因此被卡斯特称之为“语言爱国主义”。叶芝在《凯瑟琳女伯爵》和《玫瑰》组诗中正是在尝试用英文写作与爱尔兰传说和民间语言相关的诗歌,希望这种写作方式能达到爱尔兰民间传说曾有过的高度。
叶芝曾在《外衣》中描述自己的早期诗歌“披覆锦绣”,德曼因此批评他的早期作品堆砌辞藻,使用的意象缺乏比喻或象征的深度。但在叶芝的早期诗歌中,对声音效果和简练口语风格的探索已非常突出。《当你老了》全诗基本避免了使用拉丁词根的词语,多用源出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单音节词。同一组诗中的《老翁悲辞》甚至附有诗人自注,沿承了华兹华斯的诗论主张,称“这首小诗无非是把一位威克洛郡老农民的原话直接译入诗行”。《当你老了》的语者开篇即向诗中的聆听者提出了一个设想——她年老之时的状态:
当你老了,苍白鬓发,睡意昏沉,/在炉火旁打盹时,就拿下这本诗册,/慢慢诵读,梦忆那柔和的眼神/曾是你双眼所有,梦忆它们暗影深沉。
诗的第一行在节奏上具有完美的抑扬格,极言迟暮之年的衰落,单调起伏的节奏暗示着自然规律的无情和时间的紧迫,老年终将无可阻挡地来到,同时,“睡意”喻指着被称为永恒睡眠的死亡。
如将这首诗与洪萨的十四行诗原作进行对比,原作中被设想为老妇人形象的女子也坐在炉火旁,虽年事已高,却仍秉烛纺线,吟唱起洪萨赞颂自己年轻时美丽的诗篇,并为之讶异——这个劳动并思考着的人物形象保持了身心的活跃。相对地,叶芝诗中的老年时期,似被刻意塑造成了白发衰容,不仅沉闷迟缓而且无所事事,是临近死亡的衰颓阶段。伯恩斯坦因此批评了《当你老了》中的老年意象,认为其产生原因是诗人早期诗歌风格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并且主张叶芝对老年的看法在其晚期作品中臻至成熟。
诚然,叶芝涉及老年的诗篇颇多,其中尤为著名的例子是晚期作品。如《驶向拜占庭》(1926),诗中老人的灵魂可以有清扬的歌声:
老了的人只是件破烂东西,/棍子上挂着的褴褛衣衫,除非/灵魂拍手歌唱,肉身的每个伤痕/都让它歌声更清扬
又或是去世前一年的诗作《一亩草地》:
允我一名老人的狂怒。/我必须重塑自己/直到成为泰门和李尔/或是那位布莱克/他捶打着墙壁/直到真理服从他的召唤。
这心智是米开朗琪罗知晓/能穿破云层的/或是被狂怒启示/能将死者在尸布中摇撼;/非此均被世人遗忘/老年人拥有的鹰隼的心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亩草地》首先考虑了出自古希腊和莎剧的虚构或半虚构人物形象——泰门和李尔,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实中的诗人布莱克,强烈的情绪与文学艺术结合,成为探索真理的创造性道路。与这些歌唱老年人灵魂与心智的热切激烈的诗句不同,《当你老了》却极言凡人肉身的衰老,灵魂之爱在老年也成了过往,这样巨大的反差需要进一步的诠释。
应当指出,与伯恩斯坦的观点相左的是,即便在叶芝早期诗篇中,也有对老年的积极理解以及复杂的描述角度。在《奥辛的漫游》(1889)中,叶芝写道“一位老人搅得火焰升腾”。《猎狐者歌谣》(1889)直接描写了普通人在老年时期的生命力:“这位老人的眼中是火焰。”显然,即便对青年时代的叶芝来说,老年也可以有充沛的能量和丰富的可能性,并不单纯意味着衰竭和失去,老人的形象也能与火焰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组成统一体。
在《当你老了》被收入不同诗集出版的过程中,叶芝也作了一些修订,但无论行文还是字面意义,该诗的1892年版本与1925年版本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与同时写作的《爱的忧伤》相比,后者显然才是被诗人认为风格和思想不够成熟的少作,修订版变化极大。如把《当你老了》置于叶芝与冈之间社会与政治取向的差异中来分析,那么诗中负面的老年形象似乎并非诗歌风格或诗人成熟度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叶芝对冈的激进政治活动的批评,而且他后期的诗也愈加明确而强烈地表达了这个批评的立场。
叶芝虽喜爱布莱克和雪莱的诗,但并未吸取这两位诗人的激进面向;他虽被萨义德称为一个“无可置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离岸统治折磨的人民的经历、抱负和有复愈能力的愿景”,并参与了现实政治,但他对于冈的激进政治活动和采取一切手段达成独立的姿态始终持保留态度,甚至认为这些活动妨碍了冈发挥天赋。在写给女儿的诗《为女儿的祈祷》中,叶芝把基于抽象理念的激进政治与憎恨和固执等同,认为“智识上的憎恨是最糟糕的”。
同样,在写于1927年的一首悼亡诗中,叶芝将爱尔兰独立运动军事领导人马克维奇伯爵夫人描述为“在无知者中密谋”,而她的妹妹,热情投入曼彻斯特的平权政治和劳工运动的艾娃则“枯萎成苍老并像骷髅一般消瘦”。如果对比《智慧随时间到来》中类似的句法和截然相反的措辞“枯萎而进入真理”,晚年的叶芝依然通过描述女性老年时的衰老和枯竭来批评被他视为过于激进的政治参与。
《当你老了》这首早期作品体现了自传与创作之间的张力,重视诗歌文本作为文学创造物的性质,强调诗人与读者的身份以及阅读的过程,可被视为借助戏剧独白式的语者诗人的陈述以探索诗歌中英语语言的声音和语调以及传统母题的努力。全诗行文看似简单,细读之下却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第一节第二行“在炉火旁打盹”,加强了开头两行建立的衰朽而单调的老年意象:内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唯有依赖外在的温暖度日;头颅不再是活跃思想的所在,而是机械动作的被动执行者,突兀地一遍遍上下运动,仿佛重复着第一行中规律的抑扬格节奏。
第二行的“慢慢诵读”让诗句的节奏放缓,这虽是对聆听者的要求(或是对老年时钝讷理解力的批评性描述),但也可被同时理解为语者在某种程度上潜意识地对自身的反省:在对聆听者的诉说中,不宜操之过急。此外,这更可以被理解为对读者的教育,诗的文本自身要求读者采用一种更加从容的阅读方式。“拿下这本诗册”则进一步提示我们,叶芝不仅创建了文字,还希望造就读者,要求读者思考阅读的方法和意义。这首诗并非仅作为文字组合而孤零地以业已结晶、边界分明的固体形式存在,而是在历时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形成的诗集中的一篇,而且也应当在这样的框架中被当作构成物在文本形成的历史中被阅读和诠释。“这本诗册”随着叶芝诗歌以不同形式编选出版,将会获得时间性和变化性。
和洪萨的十四行诗中规整的将来时不同,复杂的时间观念和时光交错是恰当理解叶芝《当你老了》的前提。雅各布森和鲁迪在讨论《爱的忧伤》时,注意到“爱”这个词在《爱的忧伤》诗行中并未出现,而在《当你老了》中却以动词和名词形式一共出现了六次。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六次中所有的四次动词形式均是以过去时形式出现的,流传最广的一些中文译本就是在这里作了更动,令其部分或全部成为现在时,造成了误读。原诗中,“爱过”(loved)在第二诗节中被重复四次:
多少人曾爱过你欢畅优雅的时刻,/爱过你的美,以假意或真心,/但有一人爱过你朝圣者的灵魂,/爱过你变化着的脸上的悲哀。
“爱过”是从将来出发的过去时,语者认为到了老年的时刻,这些具象之美的爱慕者终将散去,无论真假的爱也都会消失。颇有深意的是,“爱”的过去时被延续到后两行,与前两次爱的动词用法时态实则相同。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并存,导致了真诚情感与带有破坏性的反讽之间的纠缠。恰是在分享着时间共同性的诗句中,语者开始强调自身的特殊性:那么,被语者引以为傲的、独特的对内在灵魂及其苦痛的爱其实并未能永恒,也并不那么特殊,它也将和对外在之美和欢乐的思慕一样成为过去。聆听者的面貌被描述成始终在成为过程中的“变化着”,而不是完成状态的“变化了的”,让这种通过时间对比而构成的反讽显得更为突出。
同样具有反讽性质的是,诗中所描述的对爱情的追求事实上是通过自恋来表现的。此前保持着平直文风的语者-诗人在此放肆地流露出了自诩独一无二的语气,自恋的口吻倒是与洪萨诗中的语者-诗人相通,后者在面对求爱被拒的命运时更是自怜自艾。语者愈是自矜,爱的逝去就愈成为突出的问题。关于诗中爱的逝去这个主题,已有多位学者试图诠释。这些分析并未充分考虑到此诗的一个内在矛盾:语者声称他所爱的是灵魂而非肉身,却沿用了传统的诗歌形式,用身体状态来定义老年、对比青春。
诗中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以及诗体和话语之间的对立似乎都是通过爱的逃离而被超越的。首先,叶芝总是试图超越二元对立,这个倾向不仅来自布莱克,也来自神秘主义。哈珀指出,叶芝从未宣告过退出“金色黎明”,这是因为它的一些教条印证了诗人对现象界和真实界的理解:“在低下之处的东西和在崇高之处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对于灵魂的爱虽然成了过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通过逃离到达了另一个层面,并且“爱”本身在行为过程中成为不同高度的联系:
在闪亮的炉栅旁俯身,/略带悲伤地低语,爱是怎样逃离了/并在头顶的山上踱过步/又将他的脸隐藏在了群星之中。
“爱”的逃离最终意味着上升,通过与“群星”发生联系、形成共同体,才最终完成。
其次,当爱被拟人化、拥有了实在的身体之后,它才可能逃离。前文中语者所自矜的,是符合柏拉图哲学或是基督教教义的灵与肉的区分以及相应的选择——对灵魂的爱。而在诗的结尾处,大写的对于灵魂的爱却拥有了实在的身体,对灵与肉的二元区分至此被彻底抛弃。不妨再对比一下洪萨十四行诗的第三个诗节:诗人的爱不被接受,将埋身黄土成为“无骨的幽灵”,这是一个与叶芝诗相反的、完全失去肉身的下行状态。在诗的最后两行,叶芝没有追随文艺复兴法国诗人的下坠感和忧郁感,而是开始强调上升。与但丁的贝雅特丽丝或是歌德的永恒女性不同,灵魂之爱通过获得肉身而“逃离”,与造就这首诗的前半部分的爱的对象决裂,同时也与自恋决裂,到达了更高处。将脸隐藏在群星中,是否意味着生成了比自我更崇高、更强大的东西,这似乎并不确定,因而留下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结尾。
最后,虽然爱逃离了,但尘世并未被抛弃。读者可以设想拟人化的爱所处的奇妙位置:在同一个语句中,脚停留在人间,但是位于高出普通尘世的山巅,头到达了星辰的高度,最终连接了尘世与天空,使二者成为一体。这里需要设想的不是巨人化的躯体,而是绘画中采用的被压缩的视角,类似布莱克的画《阿尔比翁》的构图。或许叶芝本人也意识到了这首诗中的内在困难。可以设想,早期的叶芝所设想的拟人化的“爱”超脱了人间,完全进入了天空这个更高的层面。1895年3月,叶芝在《诗集》的序言中说,他以《玫瑰》为组诗标题,是因为“作者相信,他在这组诗中发现了唯一可以亲眼见到‘美与和平的永恒玫瑰’的途径”,但这样理想化的超验的玫瑰只能存在于高出人间的层面。1899年再版《诗集》时,叶芝放弃了这种激昂的语汇,希望自己将能目睹的是小写的“美与智慧”。到了1925年,叶芝60岁,他用略显挫折但仍态度坚决的措辞表示,自己“第一次意识到《玫瑰》所象征的东西与雪莱和斯宾塞的心智之美并不相同”,他所想象的玫瑰“与人类一起受磨难,而不是从远处看到的追求的目标”。此时的玫瑰,已经回到了人间,不再是视觉的对象,正如爱一般立足在尘世。
叶芝的《当你老了》并非单纯地改写洪萨,诗的末尾还裁去了洪萨十四行诗中最末两句贺拉斯式的直白邀约或敦促——在尘世中及时行乐。当然,叶芝和冈的彼此尊重或许使得类似的邀请显得轻佻,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这首诗的重点并非青年人求之不得的爱情,而在于思考可能导致衰老昏沉的原因,探索诗中内在矛盾所质疑的灵魂应有的状态,强调写作与阅读中的创造给社会与个人带来的可能性,以及质疑导致孤独与衰弱的过度狂热的爱尔兰分离政治。正如《爱的忧伤》并不提“爱”字,《当你老了》屡次言及爱情,却将历史、文化、政治作为主题。如果将此诗单纯视为一首复制传统诗歌母题中人类身体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永恒爱情之间的矛盾的作品,或是一首强调基于灵魂之爱的崇高与完满的情诗,那么被忽视的不仅有文本中思想的复杂性,还有产生此文本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