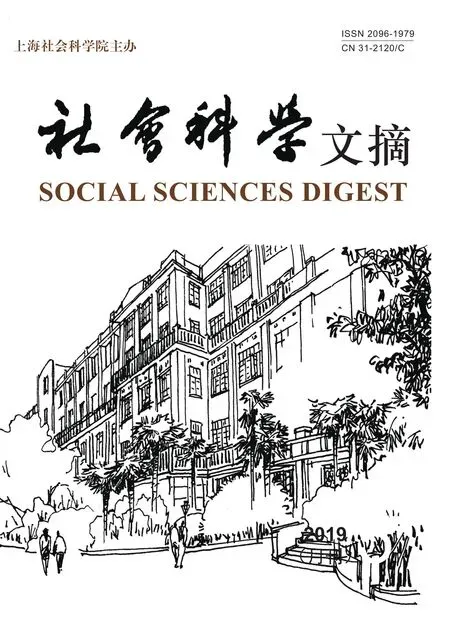启蒙还是浪漫?
——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在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扬一代风潮,提倡白话、批判传统、主张西化、宣传自由与民主,足称文化英雄。但他虽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谤亦多由其盛名而来。今胡适辞世已逾半世纪,放眼裁量,由宏观追溯往事,作理性的检讨,从而客观评其功过,不因其功而忽略其过。胡适学崇杜威,虽未尽窥乃师堂奥,但始终信奉自由主义。不过,他在思想上仍持有激烈的面向,尤可见之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激波扬澜。
“五四”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以胡适成名时期而论,其时所弥漫于西方社会者,已属浪漫主义而非理性的启蒙精神,而中国社会自西方所接收者,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余绪而非理性启蒙精神的真传。“启蒙”讲究理性与个人,而“浪漫”讲究意志、权力、群众以及国族主义。
浪漫思潮于20世纪昌盛,认为理解知识之源,需要直觉、灵感、想象与同情。“浪漫氛围”的影响波及面甚广,文艺、哲学与政治无不波及,在思想层面上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动,可称之为一场文化革命。浪漫风潮在现代西方影响深远,虽有人洞悉其弊,提倡回归古典,但并不能撼动当时激情的浪漫运动,浪漫风潮仍难以遏止。从西方思想背景可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迎接的西潮,就是西方的浪漫风潮,所以不仅思想与文学需要革命,连文学形式也需要革命。“五四”是一场不断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强烈批判并不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激情。“五四”爱国运动的底蕴是在外力刺激下引发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不能磨灭的浪漫色彩。胡适参与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不可能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感性的浪漫激情。
科学与民主当然需要理性,但“五四”所宣扬的科学,是以科学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来抨击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欲以科学的世界观来取代传统中国的生命哲学,视科学为万能,成为非理性的“科学主义”,已失去科学的真精神;信奉“科学主义”的人,将科学过度应用到无法由科学方法验证的事物,将科学当偶像来崇拜,就是反科学的浪漫态度。郭颖颐教授认为,“科学主义”从“五四”发轫,经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对崇拜科学的社会风气影响虽大,但并无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所以“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乃科学主义而已。至于“民主”,也像科学一样被崇拜,同样被视为救治中国政治病的万灵丹,人们将之作为抨击传统专制的利器,在一个缺乏民主理念与实践的国度,不经过理性思考与批判,也未考虑袭用西方制度的条件与可行性,只凭仰慕的热情,作一厢情愿的拥抱,成为非理性的“民粹主义”,仍然是浪漫情怀。然则我们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之本质,本来就多浪漫而乏启蒙精神。胡适所倡导的重要议题,莫不具有浪漫主义的情调。
高唱“文学革命”
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其中最关紧要的是“不避俗字俗语”,也就是提倡白话文。他无疑是提倡白话最力的先驱,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拟用国语(白话)造文学。但语与文并非一事,不能径自将文作语,亦不能将语作文,中外文皆如此。所以“八不主义”既无新意,又不乏可商榷者,却轰动一时,浪漫讯息又在其中矣。胡适界定“白话文”为“明白畅晓的”文字,岂非要包括浅显易懂的古文?但又应如何处理不明白畅晓的白话文?钱钟书曾指出:“以难易判优劣者,惰夫懦夫因陋苟安之见耳。”胡适坚持以“死”“活”来界定文言与白话,其实西方人所谓“dead language”指的是“已废文字”(language no longer in use),然而文言在当时仍然是“通行的现行文字”(language still in use),绝非“已废文字”。胡适自定文字生死之余,却又以一己的主观判断在《白话文学史》里收揽了一些自称“已死”的古文。其实,“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的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文言与白话都是汉人的语与文,白话是“口语”而文言是“雅言”,口语成为可读的白话文,仍需要雅言作为根底与资源。白话可使文学普及,但无须废止菁英的古典文学,两者原可双轨并行而不悖。口语与行文之不可能完全合一,中外皆然。但胡适欲以白话取代文言,而民国九年教育部又通令全国各校改用白话教学,自此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文言逐渐成为读书人难以索解的“古代汉语”。此一转折之影响深远,吾人称之为革命,并不为过。具体说,就是白话革了文言的命,胡适的助澜之功断不可没,但也是新时代的形势促使他成为识时务的英雄。
今日回顾,白话文的普及固是大势所趋,但无必要废除文言,新文体没有必须取代旧文体。白话俗语诚然可能写成精致的美文,但白话文腠理的精粗好坏还是与执笔者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如何使拖沓繁复的白话写成简洁明畅的文字,仍有赖于文言的善用。证诸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手,无不从古文源泉中获得滋养。然而因古文遭到废弃与漠视,能够借文言之菁华将白话文写得精简雅洁者日少,能执笔作文言文者,更是日见凋零。偏废古文不仅枯竭了白话之源,且舍弃了汉文化的宝笩,因数千年古文所载,乃整个传统文化精神之所寄。今人读古文犹如有字天书,又因西式语法的入侵,充满生硬的句式,成为冗长又难懂的白话文。胡适当年视古文为死文字,实在有欠深思。
主张“充分西化”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因“全盘”有语病受到批评,乃改称“充分世界化”,但如他自己所说,完全是名词之争。他显然将“世界化”等同“西化”,所以说“充分西化”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他在《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得更加明白:“如果还希望这个族在世界上占有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番议论,已经非常接近全盘西化了。不过这种一厢情愿的西化,依梅光迪之见,会带来“中国式的自杀”。胡适见到进步的西方现代文明,反观中国的落后,他是真诚想要弃旧迎新的。在他心目中,文化是一元的,中国文化是旧文化,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新旧不能并立;他认为,即使是中西文化折衷论也是“变相的保守论”,不足为法。然而如何才能充分西化呢?胡适以行动给出了具体的答案:他与陈独秀携手提出,必须请西方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到中国来。
赛先生指的是“科学”,是观察自然界之后,对客观现象力求合理解释的专门知识。近代西方科学多能突破窠臼,经实验而得出结果,自16世纪以后,科学逐渐发扬光大。科学是专门知识的累积,必须按部就班、实事求是,靠科学家在研究室、实验室里孜孜不倦,持续发展,不可能靠喊口号、搞运动而有所作为。即使把赛先生请进来,那些口号宣传家又安能越俎代庖搞出科学来?然而胡适平生锲而不舍“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忱颂赞”,直到逝世前一年的1961年都没有改变。胡适不仅将现代文明定性为西方的科技文明而大加颂赞,而且视“没有精神价值”的东方文明为理想主义的现代文明之障碍。他是有心想要清除落后的东方文明,以便充分接纳进步的西方文明。他对西方文化无保留的赞美以及对东方文明极度的鄙视,可以证明他的思想本质仍然是“全盘西化论”。
胡适的用心固然在于为国家的进步与繁荣着想,但科技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西方早已分途,科学在英美指的是自然科学,然而胡适在1922年说:“今日人类最大的责任与需要莫过于用科学方法解决人生问题。”他不仅谈科学的人生观,而且要以科学方法治文史之学。科学范围甚广,可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两者方法也不一,而胡适将之浓缩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口号虽响亮,但不很“科学”,因无论假设或求证都要小心谨慎。大胆的假设乃“空泛的假设”(barren hypothesis),非科学家所应取,因假设既然空泛,又何须小心求证?故科学家必先求有望“丰收的假设”(fruitful hypothesis),始冀有成。胡适误将现代化等同西化,也因他未留意二战后盛行的社会科学及研究新兴国家西化的成果,故昧于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重要性。他未能考虑到:传统未必是现代化的阻力,例如日本的传统就对其现代化进程有所助力。
科学之外,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诉求就是民主与自由。胡适毕生倡导民主,但他信奉的民主是美国的“威尔逊式民主”。胡适对威氏的仰瞻之高,确实终生不泯。他倾倒于美国民主的选举制度,即由公民自由选出领导人。他曾与李大钊进行“主义与问题”的辩论,批评马克思主义源自19世纪欧洲工业社会,不适合施用于20世纪的中国,但是,产自欧美民主社会的“实验主义”又如何必然能适合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呢?
胡适对民主与自由的信念虽然终身不移,但失在不知如何付诸实施:他既没有在书斋里深度考虑中国的现状,完成对中国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也没有师法杜威,全力从教育培养民主的下一代,而是最后选择与当政者建立关系,进入蒋介石的圈子。他无非想从体制内改变威权体制,但结果与虎谋皮不成,反遭奚落。胡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在雷震案的压力下,既不能反抗威权,又爱惜羽毛,不能彻底与当局摊牌,最后只有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来自解。
全面抨击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伐对象。原因不外乎外力侵略、国势凌夷,人们在激情的号召下,感情的宣泄远多于理念的追求,愤激之士更为救亡而归罪于传统。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受到保守势力的尊奉,如袁世凯以尊孔为其洪宪帝制张目,所以感到有必要进行反击。激进派认为:中国若不从“封建”威权体制中解放出来,将无以立足于现代世界,更不能追求富强。然而强烈的文化批判并非基于理性,而是依傍于激情,结果必然摧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怀忧丧志,失去信心,年轻一代更呈现精神迷茫与心灵空虚。主张充分西化的胡适在抨击传统的阵地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他文化一元论的心目中,先进的西方文化理当取代落后的中国文化。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抨击传统必然使孔子成为众矢之的。儒家思想被视为专制集权压迫的渊薮,孝道成为了家庭对个人自由的捆绑束带。胡适指责孝使得父母子女相互依赖,以为是亡国的根源。然而自汉武帝独尊孔子,不仅历代王朝多尊孔,而且儒家对制度与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其间流弊自不可免,但未可全面否定。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于五四运动后访问中国,注意到新文化运动抨击儒教所重视的孝道,因孝重家,不利于“公众精神”,孝既尊亲,涉及尊君,具有强化威权体制之效,但罗氏认为:孝再可议,其害远不如西方的“爱国主义”。两者虽各自为特定人群效忠,但孝不至于像爱国主义会导向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罗素还肯定儒家经典主要是教人“彬彬有礼”,即使时而无效,也是“一部礼仪书”,教人如何自制、谦和、有礼。其实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并不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孔夫子的理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才是他心目中人君的典范,才能实现治平之道。然而历代帝王名为尊孔,实用法术,故南宋朱熹谓“八百年来圣人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间”。历代所行的专制,主要是基于讲求严刑峻法的法家,当然,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重视,得到帝王的尊重,因而多少起到了“软化”冷酷专制政体的作用。儒家道德规范与伦常关系也起到了稳定社会构造的作用,维持社会的礼法很可能因打孔而毁灭。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登高一呼,成为攻击儒家文化的领导人。这是浪漫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有他个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儒家的经典经过几千年的涵化,犹如基督教之于欧美人,已成为中国人所尊奉的行为准则。儒家经典要在致用,所谓“儒教”,乃儒者的教化,并非宗教,除治国平天下所需外,使日常行为有所依归,使社会和谐稳定。尊孔或反孔关系到人心之邪正与国家之治乱。胡适虽曾写《说儒》,并对若干儒家人物表示尊敬,但既无补之前的激烈反孔言论,亦无意重新肯定儒家价值,至于他晚年对传统与西化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更无片言辞证。他于逝世前发表英文文章,仍严厉谴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认为东方人一方面必须要承认古老的东方文明几乎没有多少精神价值,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而且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他仍以小脚与迷信来贬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引发中西文化论战。他一贯的西化立场始终未变。
结语
胡适的盛名因新文化运动而起,他自己也以领军新文化运动而感自豪。胡适的思想一方面是要全心全意西化,另一方面是要全心全意否定传统价值。他乘势而行,促进了白话文的蓬勃发展。然而强调只有白话才是“活文学”,力陈“文言”不再能够作为创作之用。他高度自信的论断值得商榷。他身后十余年后,钱钟书出版《管锥编》,证明古文不仅未死而且极具创造力,甚至可以无碍表达西方的哲学思维。不过“五四”之后出生的学者即使有钱氏之才,已难以运斤斫白,流畅使用文言作为书写的工具,文史功力浅者甚至有阅读上的困难。胡适宣布当时仍然通行的文言为“死文字”,使其渐遭废止,百年之后的今日,确有灭绝之虞。于今视之,胡适当年以文言为“死文字”,力主废除,即无有心之罪,至少亦有无心之过。吾华思想文化自先秦至清末民初,以文言为载体,一旦文言成为“死文字”而遭灭绝,则胡适全面攻击传统之目的将彻底达成。几千年的传统精华既失,中国的选择唯有充分西化,其结果只能受制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丧失学术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崛起,但在学术上仍无法与西方匹敌,已有学者警觉为何中国崛起而文化仍然滞后?为何仍然在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原因不外忽视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故出现自我文化认同的危机。传统文化的价值失落、文化认同出现危机、学术话语权丧失……今日种种,当年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公,是否难辞其咎呢?中国原有数千年的文化经验,而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将其践踏,此一历史的折损要用多久才能恢复?西方所掌握的学术话语权,其理论并非凭空而来,就是根据西方历史经验而来。我们若轻忽传统经验,而珍重不切合自己国情的舶来理论,又如何能建构自己的理论?如今胡适谢世已57年,我们不宜一味表扬胡适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功,亦应论其过,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