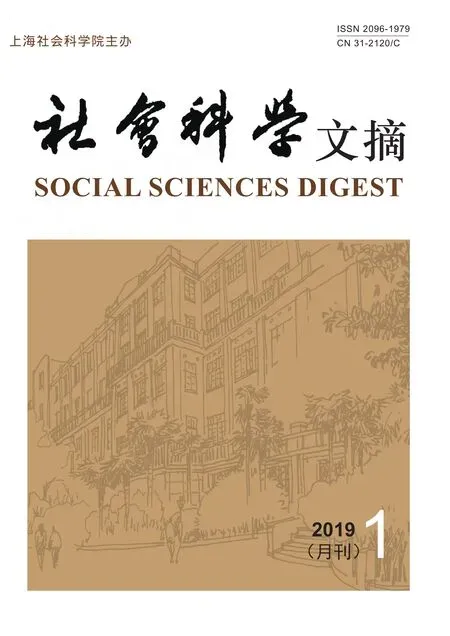“多元竞争的现代性”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小说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话题持续得到关注,“现代性”和“现代化”成为不断自我更新的理论话语焦点;但对于如何阐释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则有不同的路向。我们可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小说为例,对相应的研究方法作出新的思考。其时处于三个政治/文化区域内作家的小说创作,可以提供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多元竞争的现代性”历史局面下,多种形态和内涵的“新文化”相互角逐的图景的宏观和微观面貌;而相应的批评因此也可以成为富有启示性意义的新的研究方法。
更具体地说,自晚清的梁启超始,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理论)中,一种“新文化”首先体现在“新民”和“新人”的迥异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与行为的面貌中。在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就提出了“新青年”“新女性”的概念。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作风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现代的文化的化身。因此,借助“新青年”“新女性”或“新人”这些“五四新文化”的核心概念,以及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20世纪40年代(1937—1949)小说中的发展和变异,我们可以发现“多元竞争的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不同的主体性和个人主义症候:在现代中国的动荡时代,对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寻求经常是通过对“新青年”和“新女性”的身份危机(即个人主义的危机)的克服来进行把握的。换言之,对新身份的建构基于对新主体性的寻求上;“主体性”的创造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设想不同的“新文化”的内在需要和实质。而正像“新文化”有不同的版本和规划,不同的主体性也被塑造并当作现代中国人的主体性本身。因此它们在文本中显现的状态,就成为我们观察社会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如何交织互动的一个“中介”。在此之中,观察“新青年”,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新女性”的形象在作品中发展和变异下的文本的叙述态度、策略与文体风格,就成为让我们体会这两种现代性如何在“新文化”中互动的又一个合适的“中介”。
“新青年”“新女性”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变异
如果说现代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都在追求中国的“现代(化)”,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如何使中国和中国人从古代或近代走向“现代”,这两个问题也可以换为另外一个说法: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他/她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现代中国社会迅速转变的20世纪前30年(1919—1949)里,我们见到了两个巨大的文化变迁运动和从“新民”到“新青年”或“新人”的初步转换。
在“五四”以后,中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社团大量出现,早期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产生深刻变化。如果说在“新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打倒孔家店”具有社会革命性质,文化建树少;在第二个十年里,随着北伐统一全国,国民政府试图进行全面的文化建设,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使得它无法进行深入的社会革命,无力破除宗法制的顽固堡垒,再加上国内外的种种矛盾,都使得它无法实现“新文化”所要求的各项改革;那么,在第三个十年,“新文化”建设所要求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由于现代中国独特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得以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解决。在此之中,“新启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现,试图将市民阶层所要求的启蒙价值观以复杂的方式加以继承和扬弃。
注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新政治不能够在旧的政治模式中产生出来,要建立在全新价值观和新社会地基上,要有一代不同的人来从事新活动,才有可能产生新政治,这也就是新人的问题。”如何区别新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具体内容,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的不同?李慎之认为,艾思奇所说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任务,“实际上是说‘五四’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与“新文化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儒家学说在现代生活中的权威不同,“新启蒙文化”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和当下思想和伦理道德变动的原因。在价值观上,与新文化启蒙学者倡导个人主义理念来批判纲常名教等不同,新启蒙运动倡导者以社会主义思想来反对封建理念和资产阶级自由观。1940年1月毛泽东出版《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把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引到一个新的方向,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来强调文化的阶级性。
从“新女性”的迷茫到“新新女性”的难产
在现代中国文学里,我们看到妇女比男性其实更好地扮演了这样一个体现各种各样“新文化”主张的人格显现的角色。“妇女问题”成为“众多社会和政治问题被提出并辩驳的斗争场所,在其中新的政治理念成形并被确定”,因而,对社会中的“妇女问题”及对它的不同应对策略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成为文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互相交织、缠斗的又一个中介。
我们不妨先以沦陷区内“南玲北梅”即张爱玲和梅娘的作品为典型个案加以分析。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抵制日本人宣扬的“贤妻良母”的父权思想宣传,而继续倡导五四“新女性”解放的理想。在此之中,梅娘在很短时间内脱颖而出。而她的创作也代表了她们的成就及局限。在她的小说里,都市市民阶层的“新女性”则面临着双重的困境:除了日本人所倡导的、所获响应不多的“贤妻良母”的理念外,还有对于现代的“自由意志”个人(或“自由新女性”)的盲目崇信。那种个人主义的对妇女权利的声张,在殖民地半封传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下根本就无法实现。这也反映了包括“新女性”理想在内的新文化方案在那个时代与社会所遭遇的总体困境。然而,当梅娘超越这一阶层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将对社会不公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女性主义话语与对政治经济的分析相结合,以致扩大自己的社会关怀视野至地位更为底下的普罗大众之时,她的写作就成为一个带有更大批评锋芒的批判工具,也更有效地实现它的潜能与其女性解放的目标。
而张爱玲与梅娘相反,对五四“新女性”的理想持有某种反讽怀疑的态度。在她的“闺阁小说”里,充满了被婚恋问题所折磨的“旧淑女”复杂的身份焦虑。她们被婚恋所困扰的处境,折射了这些社会体制在一个(半)殖民地处境和半传统社会里所处的窘境,以及在这种情形下“新女性”方案的不可能性。这一文化-政治上的焦虑带来了一种小说文体风格,它是传统趣味与西式技巧的混合;让作家吸收她内在体验的挫折和震惊感。她的故事整体上显现个人主义这一中产市民阶级的主要价值观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而这是因为当时(半)殖民、半传统的状况限制了各种角色“人性”的表达,而这一人性有其历史性的内容和阶级性的本质。在“殖民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现实中,无论是梅娘还是张爱玲,她们小说中的女性都不过是历史的“人质”。
20世纪40年代对这种“新(旧)女性”面临的困境作出不同方向的突围的,是生活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内的女作家们。我们可以以萧红和丁玲为其代表。作为流亡的“东北作家群”典型一员的萧红,其笔下似乎从未出现“新女性”的风貌。相反,她的小说里的角色多是农村妇女。她们显得愚昧,过着肮脏粗鄙的生活。她们不幸地被各种男人(丈夫、地主、嫖娼者……)虐待,却也同时显得顽强而善良。正因为她们被传统夫权粗暴对待,被阶级结构剥削和压迫,过着黑暗悲惨的生活,因此似乎格外需要“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思想的启蒙。此外,作者自身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国统区里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受困的五四式“新女性”的象征性症候。
与萧红在乱世四处躲避、试图独善其身不同,丁玲从国统区投奔延安。她在20世纪40年代日益彻底地摒弃了原来她所属的阶层的知识分子惯习,而这也同时是她思想抱负和身份重塑的转变过程。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不但显示了她意在克服自身异化感觉的急剧变动的主体性,也对应于文学作为变动的社会-文化体制的不同概念和功能。她从一个“女性气质”浓厚的妇女,转变为左翼社会批评家;并进而发展为大众和“听将令”的文化工作者;她的身份在这一时期最终在党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批评家之间徘徊。在丁玲这些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她写作的文学也改变了其性质:从一个市民阶级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并通过向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最后通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丁玲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新女性”身份转变虽然似乎解决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和“存在主义”烦恼,却仍然留下很多需要填补的缝隙(比如我们看不到“新新女性”坚实的政治意识来自何方),它们可同时被视为“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困境。
从“新青年”的颓唐到“新新青年”的彷徨
讨论在不同现代性历史趋向下的不同社会,如何对作家笔下的形形色色的“新青年”的发展和变异施加影响,同样是检讨社会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互动的一个中介。
“新青年”在沦陷区作家梅娘的小说里,显现了一种另类面貌。尤其在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夜合花开》中,我们看到围绕在女主人公黛黛周围的一群男人,他们都可以被看作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曾经)的“新青年”。这些描绘从根本上颠覆了在新文化启蒙中,被理想化了的新青年形象。在这个被日本侵略者殖民的社会里,这些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青年”不得不在个人的粗鄙愿望中戴着虚伪的面具挣扎,而无法实现崇高理想。
由现实中的“新青年”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人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分裂异化的处境中生存,于是大多梦想一种世界主义的自由和大同。无论是无名氏的被称为“江河小说”的《无名书》,还是徐訏的“现代志怪传奇”,都意图建构一个超越时代的集体主义主导话语的个人主义叙事。然而,文本中意图表达的世界主义情怀却被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状况所限,造成许多叙事的裂缝和漏洞。易言之,在国统区民众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经验下,一些怀抱新文化理想的男性作家对于实现进步的政治方案的思想革命(和社会运动)失去了信心,因而沉浸于通过文化来改变人民和统治者的心态的幻想中。虽然他们故事里的男主角表面上都拥有坚定的主体性和扎实的社会(政治)身份,但经常表现为失败的“精神征服”过程的伪成长小说(或反成长小说)只是暴露了它脆弱的、伪饰的本质。
“新青年”无法实现其世界大同的梦幻,于是更新一代的青年随时代风潮而起。这在(泛)左翼知识分子和党的文化工作者创作的作品中可以见到。路翎小说的整体性主题是关于“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文化改革的设想与实践的挫败,这导致了一种新主体性的难产。如果说五四作家提倡的主体性一般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导向的,那么路翎笔下的人物的主体性则一般被认为是超个体的集体性的意识。但它其实和共产党所倡导的主体性根本不同,只不过是陷于艰难动荡岁月里、处于边缘化而无法发挥其五四时期的领导力量的知识分子愤懑、抑郁、憎恨与焦虑的投射。在他们拒绝对身体欲望进行扬弃,并拒绝以一种新的集体性的纪律与(新的)革命道德,特别是共产党所提倡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选择中,路翎展现了一种对自我利益浪漫化的五四式“新青年”主体性的依恋与坚持。
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心理上的矛盾和挣扎,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被在解放区的作家所克服,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新民主主义(现代性)文化”的时空中。但在细读之后,我们会发现仍然有很多有待进一步解决的矛盾和张力存在。赵树理的故事被认为是提升一种新文化的“民族形式”的绝佳载体。但他笔下的男性此时并没有展现出迥异于往昔“新青年”的新时代先锋的模样,而还是在女性角色中出现了作为时代先声的变异。她们已经“翻身”起来反对传统父权的观念和习俗、落后的权威,并已经参与进步性的政治活动中。但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丈夫和婆婆的虐待没有全部得到纠正,政治意识似乎仍是初步的原始的,也还没有多少自我意识,或“主体性”。革命意识的缺乏既显示在被压迫大众身上,也显现在党员干部身上。对于那些有西式(或五四白话)教育背景的都市读者来说,这些故事虽然充满了地方性的风土人情而显得质朴而有趣,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文化政治内涵。
丁玲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如此。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时期形形色色的革命干部。他们是革命的发动者,但似乎大多缺乏足够适当的政治意识。他们似乎都难以被称为英雄模范。最进步的干部也仍然是最平常的,并且远不像我们预想的那么精干。因此,他们的“主体性”也并不鲜明。这一问题既与作家此时对何为阶级意识和主体性的认识仍是实证性的,与党的基于能动的过程性而显现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革命理论颇有距离有关,也与革命此时所处的阶段相关联系。而尚处于萌芽胚胎状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致力于剖析外在世界,更意图通过建构“运动中的历史过程的工作模式”来细描和图示通往新世界的进路。
结语
由以上讨论可见,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历史性内容”显示出,无论是“殖民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是“新民主主义现代性”,在当时都无法给陷入困境的现代中国“新文化”“新女性”与“新青年”的命运提供完善的解决之道;而作家作品中的形式上的种种矛盾、罅隙与裂缝,也以文学性的症候的方式,呈现了社会现代性的不足。总而言之,在以上分析所基于的历史阐释学方法的视野中,我们并不将“新青年”“新女性”看作是不变的本质性的概念,而是将其在文本中显现的表征及其发展变异的过程,与“新文化运动”与“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宏大宗旨进行互相参证,从而结合作品中的历史与社会的“潜文本”进行探讨;由此,我们方可以理解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结晶与折射的小说作品的形式/内容的辩证,及其“文学性”所在。我们进行这种阐释并不是为了证明预设的“多元现代性”的存在;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破除那种认为历史上存在着“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多元现代性(共存)”的迷思,在社会的历史变动中认识到“不同现代性进路”的竞争的场景,并对其具体演变进程展开探讨。这种历史/政治阐释学在理解文本结构和文学性、文学性和历史性,以及文化和政治的有机互动关联时有效的原因,就在于以这样一种“历史化”的精神,进行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下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