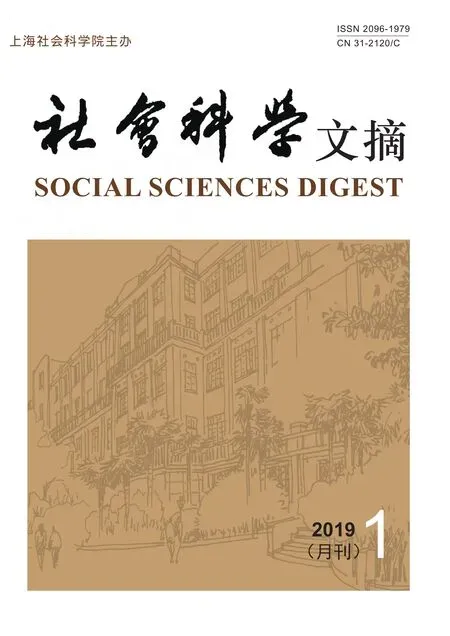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
——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概念的认识,应放宽历史的视野进行慎思。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和“乡村发展”的认识紧密相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与“农业”、“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相提并论,鲜有人把乡村视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加以理解和认识,遑论将此认识上升为一个共识性政策并加以实施。如果不能着力于社会建设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极有可能沦为一场地方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行为,从而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一
近代以来,我国自踏上现代化道路,乡村即出现凋敝衰败之势,由此引发了乡村往何处去、中国经济走何种道路的争论。这一争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盛行于30年代,并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的争论,大致形成四种主要意见:一派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这以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为代表;一派主张发展工业,认为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这以吴景超、张培刚等人为代表;第三种意见是先农后工,主张首先使农业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第四种是调和论点,主张农工并重,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一争论暂时中断。20世纪40年代初,又有人写文章重弹以农为本的老调,于是一场论战又起。翁文灏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二者相辅相成的新观点。这些争论,处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时代,其焦点在于中国到底是选择工业化道路还是农业化道路。
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要么批评西方工业化的弊端而主张农业化,要么针砭我国农业之痼疾而提倡工业化。譬如,章士钊提出“业治与农”,主张“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孙倬章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国计民生之病源,咸在于农业太盛,工业不振之故”。显然,他主张发展工业。又譬如,董时进主张“中国不宜工业化”,“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董时进的农业国仿佛“桃花源”之国。杨铨认为“不特彼所渴望之农业化,不能完全实现,即其所恐惧之工业化,亦将永无完全实现之可能”。恽代英不但针锋相对批驳董时进的农业国思想,还进一步论述了当时中国工业化的急迫性,认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再譬如,龚张斧分列工业六弊、农业六利,而支持“以农立国”。吴景超则认为,除了工业化,中国没有歧路,并提出工业化才是唯一的活路,“虽然这条活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此外,还有人主张农工调和。例如,陈宰均认为“吾国农业,自当彻底改革”。然而,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的学者毕竟少数。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二十余年,直至人民政权的建立才一时终结。这场论战的最终结果,工业化论调渐居主流。
从这些争论来看,当时人们对于“乡村”的认识,大多局限于农业或农业发展这一产业或经济的维度,要么将乡村的衰败简单地归因于农业本身的弱势或者农业发展的问题,要么将农业与工业相对立,把农业发展的问题归咎于工业化的阻挠、侵扰或掠夺。无论是主张农业化乃至农业立国的,还是主张工业化或者工业立国的,绝大部分人把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相等同;尤其是前者,更简单地认为发展农业便能复兴乡村乃至拯救中国。
在这场论战之中,只有极少数学者从乡村的社会方面探寻乡村凋敝的原因。其中,尤以乡建派梁漱溟为代表。他自己宣称并不反对工业化,但认为,“我们的目的可以是振兴中国的工业,却要紧的,眼前用力须在农业”,“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对于乡村,他强调“更须知道的,我们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这一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便是“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者说是文化失调”。故此,他提出:“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此]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
二
如果说之前还主要停留在论战层面,那么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便开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成为这一现代化的基调。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但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盘剥,而且还经受着长期的战争摧残,国民经济既已凋败。留给新生人民政权的,只是一个国民经济破产、城市工业破败的“烂摊子”。在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之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确立了工业化发展道路,依靠自力更生重建国民经济体系。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工业只能从农村汲取资源。据牛若峰所言,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税收,从农村汲取资金7000多亿元(扣除国家支农资金),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超过当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而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和温铁军引用,“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尽管不同学者的计算方法不尽相同,具体数据也有所出入,但结论几乎是一致的,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来自于农业,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诚如张军所言,“这一时期乡村价值和乡村建设被定义为:农业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积累,乡村为城镇发展提供服务,并逐步形成了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工农城乡关系和工农城乡不平等的利益交换格局”。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是,这一特定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却形成了路径依赖,被锁定在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之中。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国家最终在2006年废止了农业税的征收,但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至今仍然存在。除此以外,牛若峰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国家汲取农村资金的新形式。譬如,国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利用垄断一级土地市场,产生土地价格“剪刀差”(市场价格-征地补偿费)。许多地方官商勾结,非法占用农民的承包地。其实,还有其它形式的工农“剪刀差”存在,譬如,全国2.7亿农民工,他们的收入水平实际上也与城市工人之间存在一个类似的“剪刀差”,并未享受到同等的工资福利待遇。总之,国家从农村汲取资金,取之过度,持续时间过长,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严重不均衡发展,只会导致乡村进一步衰败。
锁定这一工业化道路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便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该体制由城乡分立的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等耦合而成。其中,在农村所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尤具代表性。贺雪峰就曾认为,“人民公社20多年时间,通过政社合一、党政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结构,为国家提供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并最终将中国由一个基本上的农业国(建国之初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约80%),建成了一个工业国(人民公社解体时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约20%)。应该说,在无法从国外获取资源的前提下,人民公社制度为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立下汗马功劳”。通过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构造,国家从农村高强度地汲取资源,因为不是直接以农户为计征单位,农民往往难以直接地感同身受。有学者指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负担要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重得多,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负担与上年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最高达35.2%(1970年),最低也有20%(1962年),一般在25%左右。只是在那时,这些极为严重的农民负担是通过农村基层集体组织间接征收的,被人民公社制度所掩盖。
随着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普遍推行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最终破产,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逐渐产生了直接的利益关联。一开始,农民尚沉浸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欣喜之中,而且,农民的实际收入相较过去确有极大的提高,农民对负担问题尚未来得及感同身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业发展进入徘徊期,农业增产不增收,这一问题才日渐突出。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负担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农民负担再次凸显出来,农民因此怨声载道,并开始动摇对农村基层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农民抗税抗粮、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于是,从2000年开始国家才在农村地区进行税费改革。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市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资金、资源、技术、知识的配置持续地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尽管肇始于普遍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逐步拓展和深化,但是维持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户籍、治理等诸制度安排却并未得到彻底变革。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必然导致城乡差别不但不能缩小,反而日趋扩大。
三
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力进行工业化建设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达到现代化中期水平以后,就必须适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政策进行调整,以避免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政策不但没有适时进行调整,反而有加强之势。
从2000年开始,中央开始在安徽等地进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再次强调,“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认识及其政策调整经过了不断深入和推进的发展过程。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且在这个战略中,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仅为今后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重新定义了城乡关系——从“统筹”转向“融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进一步升华。
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以前乡村发展、城乡关系政策的超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对“三农”工作进行了全新论述,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地辨别亦不难发现,即便是长期研究“三农”的学者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也有较大分野。其中,大多数人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最终是服务于城市化发展需要的。城市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强大动力,提出振兴乡村绝不是不要城市化,而是认为乡村的某些功能可以弥补城市化的不足。持这种立场的人,或可称之为城市化趋向的乡村振兴派。只有少数人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跟城市化相对的一种发展战略,其着力点则在于“乡村”本身。这一战略鲜明地体现着一种乡村主位的发展理念,它站在乡村大地上思考中国乡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而不是片面地主张将乡村融入并最终消弭于城镇化之中。乡村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被城市所取代,亦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和城市都是人类值得珍视的重要生活方式,各自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两者应该并存,共生共荣。持这种立场的人,或可称之为乡村主位的乡村振兴派。
之前,不少人热衷于城市化,对城市主义抱有图腾式崇拜,认为“三农”问题要靠城市化来解决,只要让农民都进了城,“三农”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然而,现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对前一个时期片面强调城市化的适度纠偏和政策调适,重新回归到乡村主位的战略立场。
四
纵观近一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乡村不断衰败凋敝。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掀起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绝大多数人将中国的乡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要么主张农业化,要么主张工业化,要么主张工农并举。1949年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初期乃至中期阶段,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导致工农、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失衡,乡村沦为工业和城市的附庸。总之,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基调是工业化,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乡村,不仅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固化为一种社会体制。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对近百年现代化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后,所提出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国家发展之策,它对前一个时期将现代化简化为工业化、并片面强调城市化战略的适度纠偏和政策调适。城乡互融、农工互促,理应成为未来中国现代化的主基调。
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走何样道路的争论,尚有不少知名学者站在乡村的立场主张“农业化”,1949年以后,能够站在乡村立场提出自己主张的学者尚且少见,能够鲜明地从积极意义上提出“农业化”乃至“乡村化”主张的学者几乎没有。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研究“三农”的学者开始站在乡村立场上思考中国发展问题,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从消极意义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一状况,到了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正面或积极的意义论述乡村(包括农业)的价值。
不过,从现有的论述来看,大多数人还主要是从产业、经济或者技术层面来论证乡村的价值的,极少人从社会的视域来审视乡村的积极价值——亦即乡村作为人类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且可欲的生活方式,它不但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而且需要得到不断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把乡村振兴战略放置在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其深远意义,确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