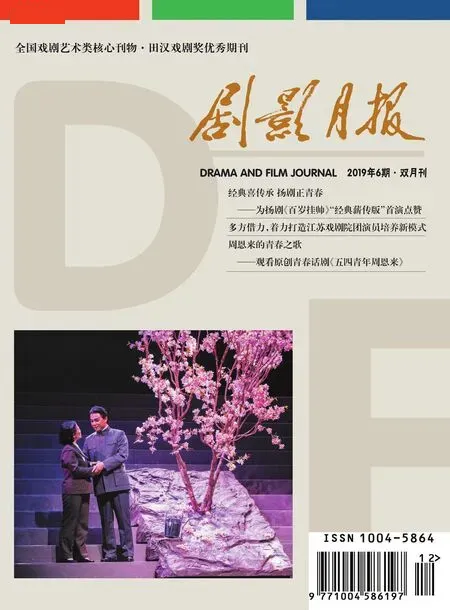年轻的扬州评话
■陈中
曲艺里面有一项叫说书、讲故事,北方称评书,南方称评话,我曾问过多位前辈老师,大家都称这行祖师爷是明末清初柳敬亭。
柳敬亭于1587年出生,算来扬州评话到现在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是个很老的行当了,我认为扬州评话历史长但很年轻,扬州评话在柳敬亭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说书大家龚午亭,他把扬州评话在扬州又掀起了个高潮,他在书场演出是场场爆满,当时扬州人为了叫他书说了句:“要听龚午亭,吃饭莫要停”。意思是,早吃过饭,可以到书场占位置,显示出扬州评话年轻活力的魅力。
年轻才有活力、年轻才有动力、年轻才有市场,世界永远年轻,扬州评书同样如此,一开始扬州评话书目并不是很多,只有《三国》《水浒》等几篇,到了清中叶期间,扬州评话艺人为了扬州评话成长,自创了用扬州方言说的书目,如浦琳的《清风闸》,邹必显的《飞跎传》《八窍珠》。一开始,扬州评话艺人只有几十人,随着漕运改道、盐政改革,扬州评话艺人向苏北里下河扩散,由于演出地域扩大,市场打开了,艺人由原先几十人扩大到几百人,其中仅说《三国》《水浒》的就有上百人,也有多位听众因听同一书目多了,形成了先生在台上说,他在台下提,最后也干脆发展成了一名评话艺人。苏北运河淤塞,江南铁路通车、扬州评话向江南发展、沪浦线、一直发展到上海、南京、东台、南通、淮安、镇江、盐城等地,书目同时也增加了很多,如《三侠剑》《彭公案》《施公案》《乾隆皇帝下江南》《绿牡丹》《明清大八义》《三义图》《岳飞传》《西汉》《隋唐》,显示了扬州评话年轻的活力。
扬州评话又一次年轻时在民国期间,光《水浒》《三国》就分出多个宗派,如《水浒》就有王家、马家等,《三国》有康家、吴家、费家、徐家,各家表现手法不同,内容大致相同,各家市场不同而又互不干扰,如《清风闸》的传人仲松岩在扬州镇江一带,余家的《清风闸》在东台、盐城、泰州下河一带,更有名家王少堂在上海通过广播电台将扬州评话《武松》播向全国,王少堂是说书中的第一个通电,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曲艺上还有一个扬州评话,显示出扬州评话年轻的市场。民国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有很多书场,最有代表性的是苏州的弹词与扬州评话,据传说《三国》的康幼华的听众很多是坐“乌龟壳”小轿车过去听书的,而每次听完书还要求先生继续加演加钱打赏,而一代宗师王少堂在上海每天都是日晚两场,场场爆满,听后观众几乎都连连赞赏,连连称奇,因为一代宗师王少堂把《武松》书目上的人物都刻画到入木三分,就仿佛英雄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身边,再一次显示出扬州评话的活力。
抗日战争开始,由于战乱、经济萧条、百业凋零,听众已无心听书,书场纷纷歇业,使扬州评话人才凋零,原先有几百人的艺人只剩下几十人,也有很多优秀书目失传,其中《飞跎传》《东汉》《扬州话》《飞龙传》《血滴子》永久地失去了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评话得到了共产党共和国政府的帮助和扶植,一九六O年成立了扬州曲艺团,把散落在民间的优秀评话人才召集在一起,招收学员,传授业,使扬州评话后继有人,并在原有的书目上增加创新了《烈火金刚》《红岩》《林海雪原》《小二黑结婚》,表演手法吸取了电影话剧的先进之处加以改进。改革开放后扬州评话再一次展现了他年轻的魅力,出现了很多名家,继王少堂、王筱堂、康幼华、康重华后,扬州评话人才方面出现了李信堂、惠兆龙、周敬堂、陈爱堂、马伟、姜庆玲、谭敏、于海、殷健、张红蕾等,书目创新有《万鸭过江》《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红楼惊梦》《京都奇案》《红墙七六》《枪声再次响起》《广陵禁烟记》《斗胆直陈》《冰释凤凰山》《捕鼠记》《挺进苏北》等大量中长篇优秀书目,表演场地由各县市只有一家书场转向各社区,便民服务、为党宣传,让更多的群众接受扬州评话,了解扬州评话;让扬州评话深入民间,这样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扬州评话爱好者,其中较有名的有祝乐、吴爱军、郭程等;让很多人都以会说几句扬州评话为荣,并在一五年到香港、法国、意大利进行交流演出,使扬州评话年轻的魅力在境外也展现,让世界了解年轻的扬州评话。
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国地大物博,风俗有异,乡音有别,南人喜米,北人爱面。改革开放后,交通便利,物流方便,为了了解异乡风俗民情,首先从文化方面入手,这几年扬州评话在党和政府关心下,在市政府领导下,走亲访友了全国很多地方,如广州、沧州、兰州、西宁、宁夏、天津、上海、济宁、张掖、皇榆林等地进行文化交流,并受到一致好评,使很多地方人了解到扬州评话。
扬州评话激情四射,充满了活力、动力、魅力,祝愿扬州评话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