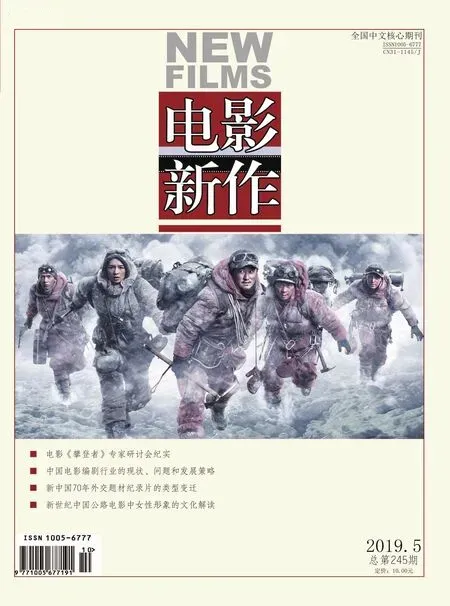《浮世画家》中的镜像与国民性
王一妍 施雯君
《浮世画家》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代表作,2019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日本上映。与小说相比,电影不仅为观众呈现了具体化的二战前后的日本国民日常生活、日本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也立体展现了小说中没有给出具体描写的小野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的绘画作品。父亲为阻止青年时期的小野成为一名画家,不惜烧毁小野的绘画作品,却成功点燃了小野立志成为一名画家的野心;战后,小野为了迎合时代新生活,亲手将二战中绘制的宣扬军国主义的画作付之一炬。两次烈火焚毁画作升腾起的烟与火,成为电影的片头,为全片定下阴郁感伤的基调。电影导演深谙石黑一雄一贯隐忍的笔风,以焚烧绘画映射二战给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带来的血腥和灾难。电影《浮世画家》中值得分析和研究的电影镜头语言异常丰富。本文选取了颇具内涵而又较为隐晦的四组镜头语言(影片中四次小野的镜中之像)进行深入研究,试图管中窥豹,剖析这部影片所蕴涵的深刻和隽永的内涵。电影《浮世画家》与小说一样,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且电影更能深入地挖掘画面背后的思想,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更直接、更深刻、更具体,引人沉思。
一、镜像·导演的匠心独显
画面的运动构成电影,电影画面的组接,既有导演意图的体现,也有其下意识的自然流露。分析不经意出现的画面,有时更能接近导演真实的内心世界,因为偶尔出现的画面,往往是不被理性所控制的、丰富多彩的、有巨大能量的心理世界的产品。它表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的生活现象,包含人的生存和意识行为的综合现象,也最能表达人类生存的文化。
影片《浮世画家》中有四处出现了小野的镜像。
第一次出现在川上夫人的酒馆中,当时小野回忆自己当年写一封信推荐学生的弟弟入职而倍感自得。他认为,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写一封推荐信就能安排一个人成功就业。可见,当时他确实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连自己都感觉不到的社会高位。川上夫人则提醒他,把所有的画家朋友都带回来,战争结束之后,将军必须把四散的家丁召集回来。在这段谈论社会地位的镜头里,导演透过金鱼缸的折射,给得意的小野拍了一个面部特写,是夸大、扭曲、变形的。
第二次拍摄小野的镜像,是小野为避免大龄的小女儿再次被退亲,事先去拜访二战中与他有过密切合作的老朋友松田知州时。小野希望松田在第三方问询时,以最正面的话语来描述自己在二战中的行为。两个老朋友坐在松田家的门槛上聊天,诉说往事。这时,导演再次给出小野映射在窗户玻璃上的头像特写,并特意将镜像与真实的头像同框:镜像中的小野轮廓清晰,却表情模糊。这是在谈论关于名声的时候,导演给小野一个两幅面孔的特写。
上述两组特写都是典型的他视镜像,分析影片中的镜头话语,可以理解导演或作家的意图:地位和名声都是外在的,通过他视镜像方能得以突显。
影片中还出现了两处自视镜头。一处是战后,学生来到小野的住所,希望老师可以给占领军当局写一封说明信,大意为:他虽然曾师从小野作画,但并不认同小野的画风,且与小野在军国主义立场上有过争执。以此力证自己不是军国主义分子,才可以得到占领当局的认可,获得战后他非常珍惜的一份工作。但是,小野断然拒绝了学生的这份请求。之后,小野站到窗前,此时窗外下着大雨,窗玻璃上映出了小野的脸。小野长时间凝视自己的脸,在窗外大雨如注的映衬下,小野的镜像一片模糊。双面人的形象在此刻再一次得到了凸显。小野要求自己的学生不管世间如何评判,一定要直面过去,不要试图掩盖。可是他自己却为了女儿不被退婚,不得已去拜访老友松田极力掩饰其过往的军国主义行径。镜头语言给观众的提示不言而喻:小野是典型的双面人,内心始终充满矛盾与挣扎。
影片行将结束之时,小野几次被人当面指责,特别是女婿和黑田的学生当面责骂他厚颜无耻、卑鄙至极,让小野极度不堪。他为了小女儿的婚姻大事,在相亲的宴会上还不得不违心地做了一次检讨。这时,他再次直面自己的镜像。连续几次遭遇面斥和自我检讨后,小野的内心也经历着炼狱般的考验,也试图找到真实的自我。
仔细分析四组他视和自视的镜头,可以发现,正如石黑一雄的双重叙事策略一样,影片的两种镜头视角也同样极其细腻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孤独、压抑、自欺与不安。当涉及地位和名声这些外在因素的谈话时,导演给小野的都是他视的镜像,其意图明显:地位和名声是外在的,是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突显的。别人眼中的小野是夸大、扭曲和变形的。或者说,即使小野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在别人眼中,因其曾为军国主义服务过,其追随军国的人生价值观就被无限放大和扭曲。战后的自我检讨和反省却是内在的,必须通过小野端详自己的镜像来审视和反思。而此时的小野是迷失的、矛盾的和迟疑的,不愿正视历史的、真实的自我。他的借口是:身处苦难的时代,听从内心的召唤,听从自己所谓的良心,无意做一个“浮世画家”,牺牲自我去追求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以艺术助长国家的好战之风,企图赶超英美国家,小野形象的背后是日本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疯狂。
二、镜像·殖民化的生活世界
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
在现代社会,体制的理性化主要是在市场和国家范围内。市场是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金钱制约着人类的行动或者生活世界。而国家则是通过行政机构所产生的权力来控制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制约人行为的主要手段是金钱和权力,二者都追求高效的运作。因此,都以工具理性或者目的理性作为运转的法则和目标。现代社会中,人们逐渐习惯于将所处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当作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结合影片中四组镜像前后的文本分析,可以论证二战前后日本国民如何走向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道路。
在川上夫人的酒吧,川上夫人恭维小野“要再请您的朋友们到这里来喝酒,这样才能重现那个让人怀念的时代(即小野权势滔天的时代)”;学生信太郎类比小野为“古代统率全军的将军”,要召集在战时“四散而逃的家臣”。小野此时回想起自己曾写过一封推荐信就轻松为信太郎的弟弟良雄找到一份工作,更是感叹“在如此匆忙的人生旅途中,突然发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如此之远”,但还是不觉得自己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川上夫人酒吧里的这段交谈是关于小野社会地位的,最后以扭曲的脸结束这一组镜头。透过金鱼缸小野的脸庞放大,扭曲,而虚假的谦虚更突出了小野自我反省的不诚恳和矛盾。
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沟通行动的合理性标准除了要满足语言表达形式本身的可理解性之外,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有效性要求:对客观世界事态做出的陈述是真实的;沟通行动建立的人际关系是正确的;言词表达与说话者的意图是一致的。如果行动者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有效性要求,就能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协调相互关系,从而为社会合作提供合理的基础。
分析这一组镜头,川上夫人和学生信太郎对小野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极力吹捧,使小野本人颇为自豪,加上酒精的作用,更使他对他人的夸大之词表现出极大的满足和自得。对照上述三条标准,三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正确的,言语的表达与说话者的意图一致,但是对客观世界事态的陈述却有出入:川上夫人希望能够恢复酒吧生意,邀请小野如战争时期一样带学生和朋友过来消费。学生信太郎是一个失业的画家,则希望老师的威名和声望能够帮助他战后的就业。小野在战后面对老师的批判和学生的抗议,依然留恋过去因鼓吹军国主义而获得的社会地位,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一呼百应,呼风唤雨的满足感。因为三人各怀心思,这样的沟通行为无法产生正面效应,反而使小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虚荣心。战后在日本民众不断忏悔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时,他却依然享受着鼓吹军国主义而带来的尊崇,至少在此时,小野并没有一点点的忏悔之心。因此,镜头中,他的脸经过金鱼缸的折射而变形,成为夸大而浮华不实的形状。关于原本正常的生活世界,三个人围绕着权力和地位进行了一场华而不实的对话,没有涉及战争的罪行,也没有涉及忏悔,三个人各怀心思,完成了一轮权力和金钱的对话。
当场景切换到小野为了小女儿的婚事拜访旧友松田先生,期间出现四次镜像。小野首先询问是否“有人因为纪子的事情来接近松田先生”,而后推测“或许会有人来这里拜访”。(第一次镜像出现,本人与身旁的门框镜像同框)。在得到松田的保证会用“用最好的话来描述”,透过小野身旁的门框再次出现小野的镜像。小野表示感激,认为“就是说一些过去的事”。此时出现第三次镜像。松田再次保证会“很好地描述”小野的事,小野最后才心安理得地返程。
对照有效沟通的三个原则分析这个场景,小野试图让松田为他在战争中鼓吹军国主义的行为进行掩饰。松田一开始也没有把小野的来访当作一次简单的老友重会,他以为小野是为借钱而来,因为小野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战争中死去。日本国有很多男子在二战战场上牺牲,女子出嫁成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此次给纪子提亲的斋藤是当地显赫的名门,在经历了上一次退亲之后,小野多多少少心有余悸,不敢因他在战争中的罪行而再次让女儿失望。小野在二战中从一个浮世画家转向激进的军国主义画家,恰是松田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所以,此次小野对松田的谈话沟通是小心翼翼的,但又是志在必得的。
小野的两面人形象再次得以充分展现。一方面,他维持着原有的体面和尊严,面对他人当面指责他“卑鄙至极”,是“最应该去以死谢罪的人”,却依然逍遥自得,享受酒吧女老板和学生的奉承,沉湎于能够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辉煌。另一方面,他却又担心军国主义行径败露,给大龄小女儿的婚姻增添障碍,所以希望松田能为他掩饰罪行。小野与松田是多年的老朋友,本可以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效果,但小野所述事件是虚假的,因事实本身的虚伪性,两人之间的沟通注定无法成功。聊到最后,松田突然说:“你最好去找一下黑田吧。”
黑田曾是小野最心爱的学生,极富才华,但在小野的鼓吹下,黑田创作军国主义的绘画作品,又因战后小野的举报,黑田被占领军当局抓获,其画作全部被焚毁,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两人不久前在雨中的街道偶遇,黑田没有和小野打招呼,只是给了小野一个终生难忘的幽怨的眼神。这些事情松田不可能完全不知情,而他建议小野去找黑田帮忙,无疑预示小野与他人沟通行为的再次失败。在这次交谈的场景中,导演多次把小野真实形象和虚幻镜像设为同框,是一种隐喻:作为双面人,小野表面的自负不能代替其内心的无力。
而小野与学生信太郎在住宅里的交谈更是表达了小野作为教师身份的失败和其社会身份的可悲。得知学生信太郎申请进入新建的高中都有了不错的回音,小野先是表示恭喜。但由于其过去隶属于军国主义画家小野的麾下,信太郎的工作迟迟悬而未决。信太郎恳请小野向高中的委员会写封信证明,自己对小野支持日本战争的创作有过反对。此时小野走到窗前,凝视着窗上玻璃的自我模糊的镜像,脸色凝重,先前的喜悦完全消失殆尽,口气变得不善,告诫信太郎,“你为什么不敢直视过去?无论世间如何评价,你都没有必要伪装自己啊。”
至此,影片接近高潮。信太郎于十多年前曾让小野写一封信,推荐弟弟如愿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今,信太郎应聘新岗位,希望小野也写一封信助其顺利就业,可小野态度迥然不同。就算信太郎拿出已经写好收件人和地址的信封,小野依然不为所动。这一次的沟通再次宣告失败。原因何在?十多年前,小野势头当红,作为军国主义的画家,得到日本当局的认可,位高权重,为年轻人写一封推荐信,是举手之劳。此次,信太郎的要求却是他无法应承的。信太郎要求小野承认他是自己在军国主义绘画作品中的引路人和监工,强迫自己走上的这条路。如果小野写了这封信,就变相坐实了小野作为一位军国主义画家提倡侵略战争的事实,这是小野不敢也不愿做的事情。小野不仅不写这样的信,而且还振振有词地教训信太郎。其实不敢直视过去,极力伪装自己的人正是小野本人。所以,小野对信太郎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是心虚的,他看自己在窗户玻璃上的映出的镜像是模糊不清的,面目全非的。导演的潜台词通过小野的镜像得到了传达:小野是选择性记忆和短暂性失忆,而他对潜意识里储存着的深刻的记忆,却可以根据需要做出取舍。主人公小野没有死在昨天,而是真实地活在当下,背负深刻的历史记忆,却毫无保留地活出永恒。
最后一个场景是小野与大女婿池田在小野战死的儿子的灵堂外的交谈,是小野真正的内心剖白,显示了小野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名声违背良心的事实,更表明了其自我反省的虚假与矛盾。
大女婿池田不断强调:“真正的罪人却逍遥自在地活着!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才是卑劣至极的态度。”小野不仅置若罔闻,更狡辩道:“我秉承自己的信念生活至今,仅此而已。或许有人声讨我,说我背叛师父,伤害徒弟。但这些都大错特错,为了达成一些事情,我不得不这么做。有些风景,不这么做就无法欣赏。我确信,我不惜牺牲某些东西而一直追求的东西,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此时小野凝视着自己模糊的镜像,室外一片黑暗,镜像轮廓可见,细节模糊。
这又是一次失败的沟通行动。小野家中为作为侵略军战死客乡的儿子举办追悼会。作为大女婿,池田理应宽慰小野,但是他却以无比愤怒的口气讨伐小野,骂其是“罪人”“卑劣至极”。小野没有因丧子之痛受到沉重的打击,却为池田的声讨倍感沉痛。两个情感态度不一致的人很难完成一个有效的沟通行动。通过小野自相矛盾的行为,导演为观众揭示:主人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命运之路,而后坚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他的逃避,他的叛逆,他的坚守,都是他精神成长的真实世界。小野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在这个意义上说,小野的形象又是清晰可见的。他不惜用以各种自欺的激情方式演绎自己的人生传奇,其实是将挫折的人生神话化,强化了他生存分裂的状态,更突显了小野反省人生的矛盾性。
综上,电影《浮世画家》刻意回避了二战的血腥画面,通过四组生活世界的场面,不动声色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战争叙事,并对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地描画,入木三分。
三、镜像·国民性的深刻体现
电影,无论是娱乐性的还是反映生存分裂状态的,都是人类世界真实的反映。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而我们就是通过不断选择而一步步走向自己,完成自己的本质。所以,到最后,小野无论是自我毁灭抑或自我救赎,都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影片《浮世画家》最后以小野焚烧自己所有军国主义画作收尾,表明了他对现实社会趋势的把握与认同。
地位、名声是小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他的别墅并不是以拍卖价高者获得,而是靠信誉和名望拍卖而来——房东要选择地位和名声与别墅相匹配的人,浮世画家的小野则是他们的合适的“意中人”。沿着这条主线再来剖析四个镜像,日本国民性的画像逐渐清晰。第一个夸大的镜像正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营造大东亚共荣圈的背景下,日本国民不断走上战场,走上侵略的道路。当时,整个国民性是夸大的、浮华的,他们大多都看不清自己的真面目。这是日本国民性的第一幅画像;而进入战后清算时期,像小野这样的市民,其心态是矛盾的。他们不希望日本国一夜之间成为战败国,成为战场的牺牲品,成为美国占领军统治下的臣民。但面对现实,他们唯有选择顺众,却尽力掩饰,不管这样的掩饰是否奏效。这是日本国民性的第二幅画像;一旦要求小野们这些战争时期的知名人士和军国主义分子进入忏悔的程序,尤其是通过文书等书面表达的形式,他们是万分不愿的。这是日本国性的第三幅画像;小野体味过勇于冒险,超越平庸是什么滋味。他说:“我们至少凭着信念做事,而且不遗余力。那种真正的满足也是令人欣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他选择决不忏悔,即使面临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痛苦,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教训年轻人,为自己开脱。这是日本国民性的第四幅画像。
战后,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做到正确认识与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彻底杜绝极端右翼残渣余孽势力在社会上兴风作浪,从政治上影响政府与人民的正确导向?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和理论上都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影片《浮世画家》通过小野的四幅画像(两幅他视,两幅自视)展示日本战争分子自视的态度:日本的所谓精英们认为,“自虐”的历史就是否定其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性与荣誉,摧毁其“光辉历史”,将使日本永远成为东亚地区的二流国家。所以,谈到战争罪行时,他们往往采取选择性记忆或不靠谱叙述,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扭捏作态。揭露如此的日本国民性,反映出作家石黑一雄的深刻性。
日本虽被公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但却有着多维度的历史观,究其国民性的复杂性,便可透析一些缘由。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该国民性特征概括为“美德的进退两难”。她谈到:“日本人慷慨或吝啬,乐意或迟疑,保守或自由,温柔或残忍。”正是因为行为的两面性,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善恶二元论”的模糊价值判断。对此,日本学者橘玲在《括号里的日本人》中指出:“在日本,至今正义观还是随机应变式的,政治家根据时间、情形改变观点的情况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日本政治家谈不了正义,因为他们只有情绪化的道德。”显然,模糊的“正义观”容易使民众容易迷失“道德判断力”。
险恶的岛国地理因素造成的“反复无常”行为模式也体现在日本人际关系的诸多方面。由于不善于以普遍、固有原则作为行为依据以及价值观的相对性,日本人的行动中往往习惯于对事物进行个别、具体的思考,并采取现实的对应。对此,日本学者滨曰惠俊做过很好的说明:“日本人在生活中重复显示的行为模式,也可称为‘状况中心型’,日本人所考虑的行为第一基准,是自己身处的状况。”故日本的国民行为特征一方面显示出灵活性和柔韧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极为谨慎小心、反复无常的“暧昧”不清的行为。
“国民性”绝非“古已有之”且恒久不变之特性,而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产物,不可对其做僵化不易的理解。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乃至国际关系因素等都对其有不可小觑的制约和形塑功能,甚至常常是这些因素综合、倒逼出来的产物。这种思维不仅对于理解日本国民性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反躬求诸己,也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电影除了具有艺术和娱乐功能之外,还包含着社会和文化的积极意义,即电影是世界观的梦想和艺术价值观的标志。所以说,电影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激活个人和群体的潜意识。我们可以采取任何一种人生态度,无论是物质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但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必须选择一种信念,尽管“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每个人对电影的理解与电影基本宗旨偏离的程度,可以反映出人们自我认识的距离,或者说,可借此发现自己的情结与自我意识的偏差。因此,据自我情结投射于电影的程度,主体可发现一个自我问题的对照标准。
石黑一雄一贯标榜自己是国际作家,他不会单独描写一个民族,而他本人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并不很长,他却能够远距离地看到日本和日本国民性。这是一个作家真正的伟大之处,也是作品《浮世画家》的不朽之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