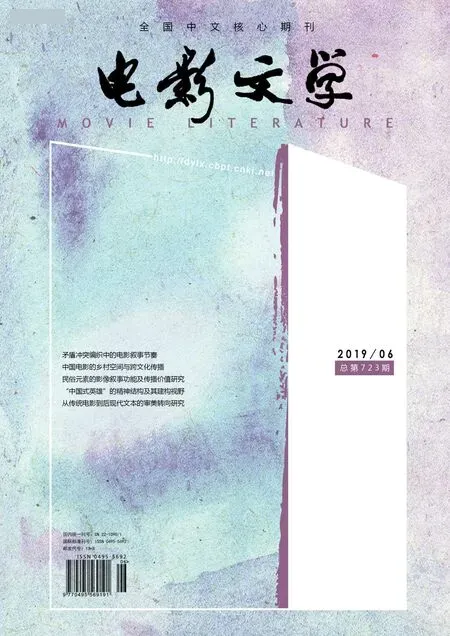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战狼》系列“英雄”与“国家”的成长叙事刍议
沈维琼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近年来,国产主流电影体现出了强烈的类型自觉,以《集结号》《湄公河行动》为代表的国产大片,努力将类型片模式和社会主流价值相结合,以通俗且传奇的言说方式、易于接受的类型手段、超级英雄的形象塑造,配合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大国崛起的民族自信、天下大同的人文情怀等精神内核,令这些影片能在票房和口碑上获得双赢。在多部佳作的映衬下,《战狼》系列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不仅在类型自觉上可圈可点,在票房上也获得极高的成绩,《战狼2》甚至“燃爆”2017年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上映4个小时过亿,25小时过3亿,46小时过5亿”[1],最终以近57亿的票房稳居亚洲影片票房第一位,并成功跻身全球票房Top 100。
两部《战狼》的大获成功,当然要归功于视听语言的流畅与精益求精,技术、表演、取景等方面的匠心是可见的,尤其《战狼2》开篇6分钟的长镜头被很多影迷和评论者津津乐道,在艺术呈现上也完全能够载入中国动作电影史册。但真正值得思考和探究的是这个电影系列在类型叙事、精神价值和文化归依上的潜在言说,尤其是关于“英雄”与“国家”的成长叙事,以类型模块和潜隐话语碰触到了艺术与时代的脉搏。
一、“敌人统一化”策略
《战狼》系列成功运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叙事经验,吸取了动作片、战争片、军事片乃至公路片的类型元素和戏剧冲突。其类型特征被归结为一种以“现代动作片为主打类型,兼容战争(军事)电影,好莱坞超级英雄亚类型电影,折射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等的强强结合,强情绪强节奏的‘类型加强’型电影”。[2]多重类型的杂糅和喜剧效果的融合,在贡献视觉奇观的同时也让艺术接受成为一件轻松和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这种多元类型复合的模式在处理相关叙事场面和段落时具有较高的复制性,实际上,类型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消遣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某种可复制性,甚至批量化生产的电影系列产品”。[3]
这种可复制、可辨识的叙事模式、轨迹和元素是类型电影叙事成功的一种保障。抛开具体如动作片、战争片等类型要求,《战狼》系列具有一些共性的鲜明叙事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核心矛盾的处理上——两部《战狼》均落实了“敌人统一化”的策略:《战狼》中大毒枭敏登誓要为被武警狙击的胞弟武吉报仇,并且认定仇人就是射出子弹的狙击战士冷锋,随着冷锋所在部队与雇佣军的不期而遇,二人狭路相逢并一决生死;《战狼2》中远走他乡的冷锋本是为替因执行任务或已牺牲的女友龙小云报仇,但在乱世意外成为保护华侨的一把利器。由于被冷锋救护的黑人小女孩是雇佣兵领袖“老爹”的争夺对象,所以二人纠缠不休,直到终极对抗时,冷锋才发现此人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仇家。
两部电影均以家仇与国恨叠加的方式,让男性英雄完成国家使命的同时也解决了个人恩怨。这种“敌人统一化”的叙事策略,将个人情感和国家使命高度统一,成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主体模式,后在主旋律电影中亦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代表作如《白毛女》《智取威虎山》《闪闪的红星》等,均将“家族恨”与“阶级仇”巧妙地融为一体,家国一体的仇恨及复仇成为新中国电影主流价值观诉说的一种显性策略,这种策略随着不断的延续已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直至新世纪的国产主流电影都强弱不一地保留和呈现着。
从叙事和接受效果可见,“敌人一体化”策略在调动共性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上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忠”“孝”核心价值观让“国仇家恨”构成“复仇”主题的双向统一性。当然,在这一共性的设置上,《战狼》系列在具体“复仇”线索上的安排是有差异的:《战狼》中反派人物敏登是主动出击的复仇者,主人公冷锋只是在被动承受。这样设计的目的,当然首先要强调敌人的狭隘与无原则、无底线,但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冷锋所代表的“军人”身份和价值。军人的纯洁决定冷锋必须身家干净,他身上不应该沾染仇恨的因子,甚至不应该有与境外毒枭私人间的关联,如果产生了关联那必须是对方蓄意为之。虽然冷锋背负了父亲的心灵创伤,但父亲的创痛是“忠”与“义”取舍上的不可兼得,而“为国尽忠”的选择不仅没有错,反而应该嘉奖。两代人的负罪只是在证明英雄的正义和侠骨柔情,也强调军人的自律之美。
另外,冷锋的被动性设计具有鲜明的历史隐喻意味。在空间场域的设置上,《战狼》将云南边境线作为战斗高潮的展开地,毒枭与外国势力雇佣兵的双重身份结合,让这场战争不仅具有缉毒的社会责任,也具有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治使命。“毒品”对国人而言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负累的,而“缉毒战”自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就成为中国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核心战役。毒品对国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摧毁身心的物质存在,也是西方列强欺凌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柱。冷锋与战友的浴血奋战和九死一生的胜利,其民族自救和洗刷历史耻辱的意味是十分强烈的。
《战狼2》延续了第一部的故事脉络,但这一次却将冷锋处理为主动的复仇者,尽管复仇的最开始所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明确,但由于以“老爹”为首的雇佣兵处处威胁非洲平民和中国侨民的生命安全,让冷锋一次次地和“老爹”交手,并在最终决斗中通过螺旋花纹的子弹,发现老爹正是苦苦寻找的杀害女友的凶手。寻找凶手是冷锋踏入非洲土地的原因,但战乱四起之时,私仇被搁置,直到最终决战之时,“老爹”射出的子弹和冷锋悬挂胸前的子弹一致,此时国仇、家恨的两条叙事线才相交,“老爹”也明白“现在是私人账”更是挑明了这一点,而冷锋“血债血偿”的回答和致命重击不仅是为死难平民和同胞复仇,亦是为女友复仇——家与国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休戚与共。
“塑造同一个敌人”不仅让具体的事件陈述和英雄塑造得以从容展开,而且“家”“国”同构后的共情也更易引起共鸣,配合二元对立的人物和矛盾构成,观众的民族情感和历史情怀被点燃。这种策略是主流类型电影叙事最易操作也最见成效的,当然为了这一叙事惯例的实施,有可能会影响到故事的逻辑性,如《战狼》毒枭与雇佣兵身份和任务的过度巧合、《战狼2》中“老爹”忽高忽低的智商及对冷锋莫名其妙的赶尽杀绝。应该说,这一带有样板戏意味的叙事策略尽管讨巧,但必须付出一些代价,所以逻辑硬伤的出现几乎不能避免,所幸“战狼”系列以英雄的完整图谱和大国自信的精神内核对叙事进行了弥补抑或掩盖。
二、英雄的成长和完整英雄图谱的构建
两部《战狼》讲述各自的核心故事,但均一致弘扬中国军人不畏艰难、保家卫国的精神,强化了强大的爱国情怀和自尊自信的中国人身份。在对“英雄”的塑造上,《战狼》系列是不遗余力的,其中既有英雄之殇,也有英雄之难,在见证英雄成长的同时以一带多,最终勾画出完整的英雄群像,经由英雄们共同守护的核心价值在层层强化后成为坚强的誓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体现出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
在《战狼》中,冷锋是有着个人伤痛记忆的特战队员——亦是武警出身的父亲为曾经执行任务被迫杀死负伤战友而备感痛苦,深刻的负罪感不仅令冷锋父亲终生未能走出道德的审判,而且被儿子几乎是“父债子偿”地主动承担。这种基于人伦情感的审判成为冷锋的职业倒刺,他试图用痞性十足、玩世不恭的方式去掩盖心灵创伤,直到创伤情境的重现:所在特战队队长被敌人狙击手射中失去行动能力,战士的营救只是制造了又一个死亡,队长声嘶力竭地“解决”自己的请求让冷锋明白了父亲当年的迫不得已。所以这一次他必须得去改变结果,完成救赎,包括为父亲正名和拯救自己。大队长的成功得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冷锋作为英雄首先需要实现的自救,只有完成了自救的任务,才能顺利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之后才能去完成救人和救国的使命。最终冷锋不仅完胜敌人,而且截获了记录国人基因图谱的血液样本,让国人又一次躲过了可能带来民族危机的敌国的灭种阴谋,“救国”和“救国人”的任务初战告捷。
《战狼2》顺理成章接过了英雄塑造的第二棒,将“救人”扩大为不仅“救国人”,而且“救所有可救之人”。冷锋踏上非洲本是为了个人复仇,但踏入乱世后,复仇的任务由于目标不明而被搁置,于是“解救”主题成为人物主要的行动力——冷锋在枪林弹雨中不断地进行着解救,这个解救从解救“干儿子”土豆到解救与自己有嫌隙的奸商,再到救助素不相识的人们,从拯救同胞到解救华资工厂的所有员工,冷锋完成了英雄主义的升华和最终确实——强大的国家是他的坚强后盾,他的任何胜利都代表着国家/民族的扬眉吐气,真正的英雄是必须舍弃个人恩怨,也必须始终为正义、为民族、为国家而战。
爱国主义是《战狼》系列电影的主基调,两部影片均将英雄人物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和中国国旗及中国护照的能量强调作为核心。作为新时代国民形象的代表,冷锋不惜生命冲锋陷阵、救民于水火,就是“为国为民”的现代“大侠”。不仅如此,第一部中的“大侠”冷锋到了第二部已经成长为人类的、国际性的“人之子”冷锋。两部《战狼》由此完成了从国家性的爱国主义叙事进入到国际性的人道主义叙事。
在进行英雄“成长叙事”的同时,两部《战狼》又完成了“民族悲情英雄”和“民族自豪新英雄”的巧妙转换。
虽然不同于以《霍元甲》《黄飞鸿》为代表的传统功夫电影塑造国家积贫积弱时代背景下的悲情英雄,但《战狼》中冷锋的“民族悲情”以隐喻的方式被呈现。尽管冷锋是新时代新世纪的英雄,但他依然承载着历史的重量,这个重量不仅来自父辈,更来自民族的被欺辱史。作为特战兵,冷锋在开场就与武吉率领的国际贩毒组织交战,这种不太符合作战逻辑的剧情设计当然是在强化“毒品”作为国家/民族耻辱柱的意义,于是冷锋的“缉毒初战”与“缉毒决战”都包含着为父辈复仇的言说欲求,而改造民族被奴役的历史记忆对任何一个时代英雄来说都有承受历史、诉说民族悲情的必然意味。
《战狼2》中,面对受难的同胞和非洲难民,冷锋在尽其所能地进行救助和保护,贫民区分发食物、街头枪战中保护平民……在华资工厂,工厂具体负责人林志雄强行将工人分为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后,面对数倍于中方员工的非洲工人的求告无门,身处楼上的冷锋以上帝的视角悲悯地观看,最终发誓将带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就是为他们而生的”,这种豪情和自信既来自英雄的本能和使命,更来自英雄身后的在世界新格局下日益强大的祖国。
除冷锋外,“前辈”何建国、“后辈”卓亦凡以及中国大使馆樊大使、医学专家陈博士和身为现役军人的海军舰长,一个新时代英雄的群像被完整建立。不难看出,这一英雄图谱具有前后承继、彼此协同的关系,老中青的完整配置同时又囊括了政府、军队与民间,把新时代新英雄以生命和人民名义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做了强化。
在爱国情感上,“为国为民”是英雄行动的基本动能,因此“敌人”必然是非国人的,即曾经侵害或正在损害中国的外国敌对势力。《战狼》系列把终极敌人设置为来自欧洲的雇佣军,他们纯粹的白人样貌和身体特征完全符合国人对欧洲人的想象,而雇佣军的残忍野蛮与自清末开始奴役中国的欧洲列强构成了强烈的关联性。于是,冷锋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后胜利在国家/民族层面,就具有鲜明的叙事诉求,即伴随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国已经具备了和欧美国家博弈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以冷锋为代表的中国男性英雄的智勇双全和冷锋的“那他妈是过去”的经典台词让“东亚病夫”这一浓缩着民族之殇的称谓成为“被终结的历史”——新的时代已经被创造,那就是中国的崛起。
“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它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4]在《战狼》系列中,冷锋从第一部“痞子英雄”到第二部“超级英雄”的成长,英雄特质的升华期间编织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代码,代表了国家力量和民族自信的自觉承载,也代表“大国崛起”的时代命题下中国的国际形象诉求。
三、大国形象的文明特质
《战狼》系列的走红,根本原因在于影片对国家形象的持续性建构上,这种源于国家实力和国际威信的自信,通过两部影片所呈现的国族符号、所传达的群体心态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建构起了一个强大、成熟的大国形象,并由此打破了“东方只能被西方定义,不能进行自我定义”[5]的神话,表征了中国在国际上开始拥有自我言说的权利。
在构建大国形象的过程中,电影在视觉形象上积极使用了图解化的方式,如强大的军事能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尤其《战狼2》中,航空母舰被不同的景别、多样的视角全方位地给予了展现,中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不容置疑。
在视觉形象累积的基础上,影片又通过英雄的行动进行深度言说。《战狼》系列以阳刚的男性气质和国际背景下的人道救助讲述着中国的“崛起”,但电影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大国”实力的展览上,而是通过英雄叙事,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明特质进行了展现——冷锋作为男性的、理性的超级英雄,他的救助对象是不分国别和身份等级的,白人、黑人,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均在他的解救中,“全人类守护者”的意义非常鲜明——中国的崛起根本不是通过创造和复制资本主义罪恶而生成的经济、资本强权,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和世界性格局上,在与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休戚与共、携手并肩过程中,主动站出以维护生命的平等权利、抵制霸权强权,并最终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使命。
如果说《战狼》还是基于救国情怀的爱国主义,到了《战狼2》,国家与民族的设置被放置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叙写完成的是对新世纪中国国际新形象的确认。电影中,乱象丛生的“非洲”、贪婪凶狠的“西方”世界、守护生命的“中国”被分置,其上附加的是恶与善、过去与未来的伦理和价值判断。其中,以陈博士为首的中国医疗队对非洲瘟疫展开的积极有效的救治和疫苗研发,其救援不仅是技术帮助,更是生命救护。电影中中国烈士的墓碑层层叠叠,记录着中国派至非洲展开医疗、建筑等人道援助而牺牲的英雄生命。中国的国际人道主义行为和精神通过墓志铭的形式被传达,这时的爱国情和民族志已经上升为救助贫弱国家的大国自信和自豪——中国早已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在实现自救后获得大国尊严,而这一尊严又通过维护和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奉献来加强。
在当下现实中,非洲的确是灾难深重:以索马里为代表的东非国家深受海盗之苦,西非的埃博拉病毒肆意蔓延,南苏丹内部不间断的热战,等等。但这些苦难并未全部集中于某个特定国家或区域。然而在电影中,这些苦难被聚集在一起,加上撤侨所指涉的中国2011年叙利亚、2015年也门的两次大规模撤侨行动,“非洲”成为“种族苦难”的展演地,“等待拯救”就成为“非洲”想象的基本特征。
《战狼2》中,携带埃博拉病毒自愈抗体的非洲小女孩帕莎无疑是一个既象征历史又隐喻现在和未来的符号。当现实空间中,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裔有色人种中肆虐的时候,关于基因病毒战的假设被提出,即这极有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非洲有色人种的一次基于基因图谱的生化武器试验。对经历过SARS瘟疫的国人来说,SARS病毒在华人中的流行、白种人与黑种人均有先天不敏感等怪相令国人部分地认可这一假设,第一部《战狼》也以敏登抢夺记录国人基因图谱的血液样本企图进行细菌战的阴谋实施为主要敌方行动,无疑又在暗示关于基因病毒战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一带有病毒自愈抗体的非洲小女孩帕莎就是对美国势力具有先天抵抗力的新一代非洲人民的象征。这一代非洲民族已经从曾经的被殖民和臣服、追随美国的历史惯性和泥潭中觉醒,因为这条老路意味着种族的灭亡,只有自身产生对美国势力的抵抗才能带来可能的种族延续。小女孩帕莎固然尚在童年,但她的女性身份意味着假以时日,她的繁殖能力和价值就会产生并迅速放大,非洲也由此获得种族的延续。而这一切需要首先获得自救的中国伸出援手才能维系和发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是睦邻友好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而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上会有它们的搭载。由此中国在国际形象上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救助和庇佑”这么简单了,这种强大的国家观和自信的民族观,成为《战狼》系列病毒和人种设置的深层话语。
四、性别叙事的深意
从性别角度而言,民族国家是男性政治的产物,在艺术世界里,男性、理性、阳刚与女性、感性、阴柔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故事矛盾展开、影像系统风格化的一个向度,性别权利话语及其价值判断在电影世界中具有强烈的渗透力。
在《战狼》中,唯一的女性是特战中队的女队长龙小云,虽然她美貌诱人,但这也仅仅是面对冷锋的时候,影片更多时候强调的是她高超的军事技能和先进的战斗能力。在演习中,她准确判断,迅速在敌方主控系统中植入病毒,让其电子战能力近于瘫痪。因此龙小云最主要的叙事动能在于体现现代中国军人及其军队的强大,在这一面上,她是无性别的。在另一个向度,龙小云为数很少的几次体现女性特质的情节都是面对冷锋或被冷锋的言行催化的时候——只有男性以更强大的样貌出现,女性才自觉恢复女性特质,这实际上实现的是对男性英雄的烘托,女性特征在此时并不承担更重要的叙事功能。
到《战狼2》,女性身上被设置了国家、民族的信息,女性开始参与国家叙事,即塑造国家形象和强调文化认同。除帕莎所指涉的非洲种族延续的意义外,女医生蕾切尔的设置强调的也是女性身份与美国国籍的结合,其符码意义亦是被美国主流政权和文化抛弃的边缘、弱势人物。华资医院被“老爹”控制惨遭屠戮的时候,蕾切尔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顶替陈博士,突出了其作为个体的优秀品质。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美国女性第一时间被祖国抛弃——蕾切尔对冷锋的救援开始时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她笃定美国大使馆会救助每一个美国公民,直到被告知美国的救援舰已经驶离,她已经被遗弃。蕾切尔的遭遇一方面揶揄了所谓的“强国”在“等待救援”这一关键时刻的缺席,更表征了美国“恃强凌弱”的人权特征——它保护的是资本而不是人,不论这个人有多么优秀。这种狭隘的人权价值观正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雇佣兵领袖“老爹”作为白种男性,他的非理性残暴特征暗示着第一世界的霸权话语,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不断扩充就是以屠杀和清缴为基本动素。“老爹”给冷锋制造的困难尽管在叙事合理性上有待商榷,但这是基于对“西方”霸权和战争随意性的一种指涉。“老爹”对所见之人不留活口的清理,甚至对雇主奥杜教军的射杀,都在着力强调霸权国家或势力对国际规约及游戏规则的蔑视和践踏,对权利、资源的随意处置、肆意占有等反人类特征。
在人性悲悯的层面,如果说《战狼》还有民族雪耻的鲜明印记,那么《战狼2》就是男性英雄拯救包括强大国家的被抛弃者、弱小国家未来希望的承载者,彼此形成的联合抗暴队列又构成了无差别的命运共同体,以中国为根本力量形成了抛却一切差别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国族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审美化想象。由此,《战狼》系列实现了从“小我”的民族大义到全人类人道主义的过渡,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激情。
“拉康意义上的‘他者’永远是自我的‘他者’,他国形象即是一国自身欲望的投射对象。电影中,自我与他者互为镜像: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强权与受难,残暴与友好,不义与正义,二元对立的形象符号具有明显的价值指向。”[6]《战狼》系列通过多重隐喻,以爱国主义和国家叙事将中国塑造为强权西方的对立面——以和平共处和人道主义为终极宗旨,不畏强权、守护生命、伸张正义、传递友好,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大国威仪。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性命题下,在世界格局新变中凸显着中国的独特和力量——中国才是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希望,中国是且必须是未来的希望,如果中国没有未来,那么世界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