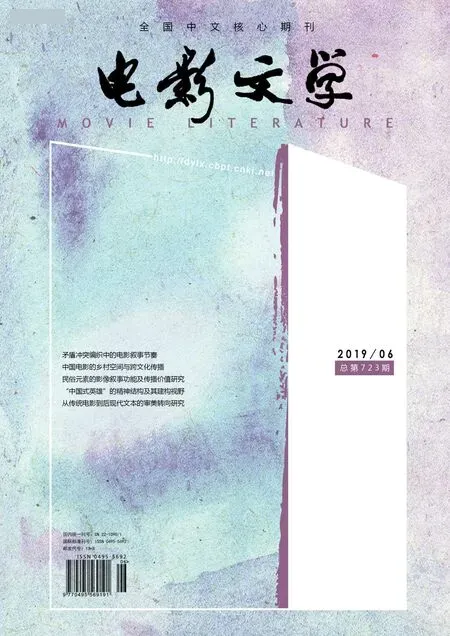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江湖儿女》的空间变异与性别辩证法
韩旭东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江湖儿女》的象征性叙事元素的运用体现了导演创作谱系内的自我互文意识,旧作中的物象/意象、场景、人物出现在新文本中的视觉/记忆“重复”,是创作者对此前作品的致敬以及对逝去时代的招魂。不同于贾樟柯此前创作谱系中对中国社会底层偏执化的影像记录,新故事中男女之间辩证化的两性关系、女性在社会/江湖空间中的身份与地位、女性角色身上彰显出的忠、侠、义等精神是新作所谱写出的主旋律。
二元对立指的是主体在获得理性优势的前提下,以审视、优越的目光将他者放在被支配的位置,“主体永远处于优越的地位,客体只能作为主体的对立面而卑微地存在”[1],主客体之间是绝对的差异关系。道家哲学中的阴、阳二者则各占一极,事物随时间的变化而发展,它的运动和发展是向对立面的转化,没有绝对的主客、高下之分。《周易》中阴始终处于阳一极之下是应然,阳凌驾于阴之上为“承”,而阴处于阳之上时则多为“乘”,体现出该书扶阳抑阴的思想。根据六十四卦中所涉及卦内二爻运动变化的状态不同,阴有压制阳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斌斌与巧巧分别代表阴阳格局中的两极,他们之间的两性关系体现了中国哲学“变”与“通”的思维模式。本文从阴/阳、男/女、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转化入手,考察文本中的女性在建构性别主体意识时,与男性本体性别气质的消解所构成的对位变化现象;在以性别政治的变迁为立论前提时,观照两性所处的江湖/社会空间性质的变异以及时代/历史、空间/江湖、性别元素之间的互为关联性。
一、作为侧影的女性
第一个叙事组合段中的巧巧是作为斌斌的侧影、附庸而存在的。就镜头技法而言,她多次出现在双人中景、近景内,而鲜少有单独给巧巧的特写人物镜头。未建构性别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性时的巧巧不具备独自占据单个画面的资格,她是一个“不完整”的影子。该段落中的江湖空间是典型的男性阳刚世界,画面的色调鲜艳、饱满,镜头间剪辑的速度较快,它的内在核心是文本中多次复现的以关公铜像为代表的忠、义、信。民间的关公崇拜源自《三国演义》和宋代开始的关公戏,关羽自桃园结义后忠于弱势的刘备和蜀汉,拒绝曹魏所给予的官职待遇。民间侠客因崇敬故事中关羽的忠义气节,而将其尊奉为江湖规则的裁定者以及共同体的内在规约符号。
斌斌的江湖大哥地位、忠义信精神体现在处理裁决还钱事件、为二勇哥办丧事、放走对自己行凶的年轻人等事件上。首先,老孙与老贾的还钱纠纷并未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而是被斌斌请出了关公铜像,对着江湖规矩的象征来裁决债务纠纷。纠纷的解决说明前现代、未完全被现代化的90年代江湖空间自有一套内部规则,遵守关羽信仰才能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存活。其次,斌斌为二勇哥解决兜售别墅时遇到的闹鬼谣言、在二勇哥的丧事上请来他生前最爱的国标舞演员表演以及安慰他的年迈老母与妻子,都体现出江湖朋友之间的责任与道义。最后,斌斌得饶人处且饶人,放走了误用铁棍打断自己腿的年轻人,且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这体现了江湖中的晚辈一旦认错低头,前辈便会大度原谅其错误的宽容意识。斌斌虽身为大同黑社会的头目,但并没有打家劫舍、欺凌弱小,而是践行了共同体内部的忠、信、义、仁精神。隐含作者通过对斌斌忠义精神的肯定,抒发了对前现代江湖空间、90年代民间规则的怀悼意识。
但吊诡的是,身为江湖中父辈的二勇与斌斌等人,却被不守规则、大胆的子一代们颠覆了自身话语权威,并因此而丧命或受伤。这象征了随着现代性时间的进展,子一代已经不再遵守父辈所留下的规则,他们睚眦必报、下手阴毒,“这帮年轻人不知深浅”。前现代江湖空间中的斌斌在大同当地有着显耀的社会地位,解决朋友的困难时能够呼风唤雨;且从是否要作为巧巧的家属去新疆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身为阳一极的斌斌拒绝做阴/女性的附属,他是空间内至阳的权力中心点。但男性表面的阳刚形象如同影片中放映的血腥暴力港片与香港金曲类似,男性气质是一种被虚构出的意识形态。观看电影时的斌斌将自己想象/重合为片中的黑帮老大,这种假想的镜像/幻想被年轻人弑父/去势般的殴打/断腿所消解与嘲讽。此外,从煤窑厂因内部贪污而倒闭、老员工们被迫的搬迁、巧巧父亲对厂长的不满可以看出,故事中的江湖中人实际上也是由大同的社会底层民众所构成,庶民们在国家大政方针、流动的巨型资本面前就是一群微小、无话语权的他者/弱势群体。而第一段落中的巧巧是作为一个贤妻孝女的形象存在的,从开场所使用的第一个跟拍无正脸长镜头到坐在斌斌身旁抽烟可以看出,此时的她是江湖大哥的附属。断腿事件后的斌斌象征着阳一极的权威开启了辩证过程中的转化阶段,腿/菲勒斯被打断是他在影片中的第一次被阉割/去势。所以,此前一直是被长镜头背影、双人中景中附庸的巧巧,在被斌斌教会使用枪的那一刻,开始走向建构性别主体意识的起点,即阴阳即将开始转换、阴对阳的吞噬。
二、漂流的女性主体
从巧巧开枪保护斌斌的时刻起,女性开始拥有独自占据单人特写镜头的资格。开枪事件中的单人近景与中景镜头一直自车内跟拍巧巧到车外,长镜头水平匀速移动,巧巧干练的马尾辫、手开扳机对天空开枪等细节说明此时的女性已经开始建构性别主体意识。巧巧在得到男性的启蒙/开枪教学后,理性意识和积极自由权表征了她的主体性内核:主要体现在保护斌斌的责任意识、主动承担非法持枪的罪名、在狱中被监禁五年,此时巧巧为斌斌所承担的是恋人之间的情。但女性主体性生成的时刻,却是男性权威被消解,向阴一极转化的开端。斌斌因被女友保护失了面子、入狱后昔日风光不再等自卑心理,出狱后也并未曾探视过巧巧,离开大同,远走他乡。
第二组合段中的江湖空间不同于第一段中的浓墨重彩、血腥暴力、暗为主色调,男性为中心点、镜头快速剪切等,该部分还原了《三峡好人》中的以白、黄、灰等冷色系为基础滤镜色彩,单人近景镜头随人物在空间中移动的步伐慢速切换。巧巧在山西、湖北、新疆之间的移动,说明个体通过个人的积极自由选择权开始了不同空间之间的漂流。如果说前现代空间中铁板一块式的“捆绑”隐含了对空间中人的保护作用,那么新空间、空间之间的漂移/个体化现象则是以让度个体的人身安全与提高风险概率来换取女性更多的选择与行动自由。[2]巧巧所遭遇的风险包括人身、财物安全以及情感的创伤。她在长江客船上被假女基督徒偷走了钱包和身份证,以及搭乘摩的时遭到司机的性骚扰和言语猥亵都说明异乡人、女性是作为新江湖空间中的弱势而存在的;但新空间的风险也是“娜拉”们成长过程中建构性别主体意识的外在刺激力。巧巧行走江湖时对司机假意应承,随后却支走了他并骑走了摩托车,只留下司机一人在雨中哭喊;身上没有钱却用一朵玫瑰花装作新婚新娘的同学,在婚礼上骗吃骗喝;以装作被骗少女的“姐姐”,故意骗取婚外情大款们的钱财,来解决自己钱包被偷的燃眉之急;再遇女骗子时先帮她打走了围殴的众人,随后向其索要身份证;失恋后意图寻找到新的开始而跟随“教授”前往新疆,亮明囚徒身份而遭到警惕后果断地离开满嘴鬼话连篇的小卖部老板/“教授”等个人抉择都说明遭遇风险的“阴”之势力不断上涨,巧巧变成了行走于新空间内的江湖女侠。她亦正亦邪的选择与行为也体现了在底层社会之间漂流与历练来建构性别主体意识的行动需要来自民间的狡黠与智慧,民间/江湖并非是完全充满忠义精神的存在,它也会藏污纳垢,有着不为人所见的粗鄙与阴暗面。但总体而言,隐含作者肯定了她的独立、自强乃至“行骗”,同情她被斌斌所辜负,独自在社会上行走时的孤单与无助。
巧巧漂流/移动的前提是她对斌斌还有“情”,目的是为了找到他并询问虽提前出狱却一直消失的原因,以及为他们二人之间的“名”分讨一个说法。而斌斌在武汉却一直故意躲着她,无法面对自己男性气质/权力被消解、被阴一极所庇护/压制的现状。此外,阳一极处于弱势的原因是斌斌无法面对自己昔日的手下在当下的实力都超越了自己、自己只能躲在林氏兄弟的手下打工居无定所、开枪事件中自己是被女人所救、目前在异乡混的境况大不如从前等。宾馆会面中的一组双人中景、近景长镜头的推移使用,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表明了隐含作者同情斌斌当下的境遇以及对时间/旧时代不再“重来”的惋惜与伤怀。
三、阴性的她者世界
第三个叙事组合段中的巧巧已经觉醒/建构了性别主体意识,成为当下江湖空间中的核心与支配性人物,而男性/阳/斌斌却沦为被巧巧庇护的对象,他是“阴”的附庸。该段落中以白、灰、淡蓝等冷色为基本调的滤镜以及多次对焦斌斌脸部的单人近景镜头等都凸显了被去势后的男性之无助状态和落魄大哥晚景的凄凉;而对巧巧照顾斌斌时所使用的仰拍单人中景镜头、远景空镜头中巧巧的入画过程都意味着新空间中的女性是一个需要被人仰视的强大主体。
不同于旧江湖的忠、义、信精神和漂流过程中的风险、狡黠与智慧,当下的江湖空间是失去了规则与秩序的混乱所在。就人在空间格局中的位置而言,斌斌在棋牌室里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处所,他需要借用厨子的卧室吃饭,并被厨子呵斥;斌斌昔日的部下老贾敢当面挑战他的权威,意图以拍卖他所坐的轮椅来羞辱他的颜面;棋牌馆中的看客们通过代表现代化科技的手机,来“看”并在网上转发老贾羞辱斌斌的过程,表明技术媒介之“眼”已经异化了昔日江湖中尊卑长幼的秩序与规则。对“囚犯”的露天展示与围观性羞辱,所造成的心理伤痛要大于来自肉体的惩罚。[3]坐在轮椅上、拄着拐杖行走、头顶扎满针灸、左手穿衣行动不便等身体的残缺都说明了当下(2018年)性别意义上的“阳”已经变为权力格局中的“阴”,阴阳辩证过程的推动力以及变化的临界点是无法扭转的线性现代性时间。为了惩罚羞辱斌斌的老贾,巧巧把茶壶拍到了他的头上。棋牌馆中性别的“阴”是权力格局中的“阳”,斌斌也正是因为这最终的“羞辱”而主动离开巧巧,在微信语音中留下一句“走了”。隐含作者借单人近景、脸部特写等镜头同情斌斌的晚年境遇,昔日江湖大哥的衰老说明了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同时,隐含作者又用仰拍镜头、中景移动镜头跟拍巧巧在棋牌馆中的左右逢源,都肯定了建构性别主体意识的江湖女侠之强大与自信。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就文本中人物之间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而言,旧空间中的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二者的性别身份与权力关系是“正常”的阴阳状态;开枪事件以及寻夫过程中的巧巧开始由性别的“阴”转化为权力的“阳”,而落魄、被去势的斌斌则变为性别的“阳”、权力话语中的“阴”。最终,在最后一个组合段的权力叙事中,巧巧成为压倒“阳”而独立的“阴”,以贵柔守雌消解了斌斌的男性气质。男女之间在性别位置、权力话语之间存在明显的对位性变化,即一方通过吞噬、拆解另一方的存在而建构自我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三个叙事组合段中变化的是随时间逝去而老化的人之心态及身体机能:从忠义江湖到风险江湖,再到性别江湖的变化过程实质上象征着“空间的时间化”变异。只有当它与生存在空间里的人、现代性线性时间发生互动关系时,空间才会反过来对人产生构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