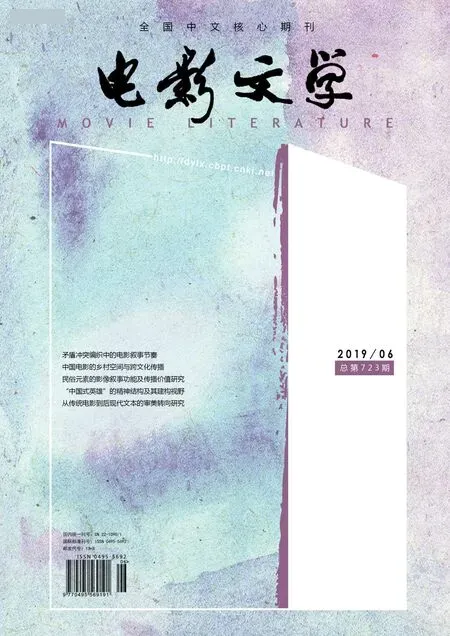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张艾嘉电影
李佳妮 (榆林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张艾嘉以女性的身份而能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电影界中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并能坚持只拍摄自己热衷的,与自身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的题材,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艾嘉在电影中,对广大的女性投以关怀的目光,使自己的电影闪耀着女性主义的光芒,这也正是张艾嘉电影在当代影坛的独树一帜之处。
一、张艾嘉与“她历史”
所谓“她历史”(herstory),即以女权主义立场阐释的,强调女性作用的历史,它有别于长期以来,基于男性话语,以男性文化为主流的历史言说,这一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兴起后的产物。
在女性主义运动之前,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西蒙·波伏娃曾经在其有着“女权主义宝典”之称的《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男权社会文化下的产物,人们普遍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即女性是男性的依附品或参照物,女性被赋予的身份,如女儿、妻子、情人和母亲,都是与男性有关系的符号式身份。离开了男性,女性的存在便难以被定义。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没有自我,只能接受男性的改造和压制。长期以来,女性也习惯、认可了这种规范,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其他女性。试图脱离这种规范钳制的女性,就往往被社会价值观所否定。
毫无疑问,电影是男性占有绝对话语权的行业之一,男性导演在电影圈中相对于女性导演而言更具优势,女性的创造力难以在片场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正是社会现实的镜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也是男性剥夺了女性表达权力后的产物。正如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针对“女性在电影文本之中是什么”这一问题所总结的,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有四个特征,即典型化,符号化,等同于“缺乏”,以及是被“社会建构”的。这四个特征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观点是相互照应的。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中,女性通常是被定位为男性的观看赏玩对象(如“蛇蝎美人”),或是男性依照自己的利益与审美标准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如“贤妻良母”),或是女性在“第二性”文化氛围中,不自觉地自我投射(如“女汉子”)等。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如胡玫、李玉、许鞍华等,参与到电影的摄制中,影像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女性视角,包括男性导演也开始关注起女性的生命历程与生存状态,“她历史”才正式出现在电影中。但女性在电影界的地位依然是微妙的。张艾嘉在20世纪70年代以演员的身份踏上影坛,并很快获得了金马影后的荣誉,但是她并未满足于做一个演员,而是早早师从于胡金铨,向着导演身份转型。由于屠中训在筹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1978)的过程中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张艾嘉便毛遂自荐,身兼编剧导演之职,将电影更名为《旧梦不须记》,完成了摄制,从此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作为导演亦称职且出彩的张艾嘉。
张艾嘉曾经表示,人们在对她进行介绍时,都会强调为“女导演”,而在介绍如徐克等时则不会称其为“男导演”。同样,在参加访谈节目时,主持人也往往会问张艾嘉如何看待男女导演之间的区别,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却不会出现在对男导演的询问中。而这样的现象在东方又比在西方更为严重。张艾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电影圈的生态对于女导演而言是不利的,但她选择了主动地去接受、改变而非被动地屈服,故而数十年来一直活跃于台前幕后,奔走于海峡两岸之间,先后成为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既在银幕之内,为女性镌刻、记录着生命的记忆;也在银幕之外,增强着女导演的影响力。
二、张艾嘉的女性主义立场
在数十年来的创作中,张艾嘉一直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在叙事中流露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气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女性困境的展现
张艾嘉电影往往以一种客观而细腻的视角,反映女性在生活中的种种困境。这种困境既有在经济生活上的,也有在精神生活上的,只是相对于同时期的同样刻画女性形象的导演如曾壮祥、李行等人,往往大力渲染女性被男性压迫、蹂躏、侮辱的惨状不同,张艾嘉的表达是克制的。例如在《最爱》(1986)中,芸芸与闺密明明的未婚夫俊彦相爱了,甚至还怀上了俊彦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芸芸不得不赶紧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甘医生,好让自己的孩子有个正常的身份。直到多年以后,芸芸把女儿的身世告诉明明时,明明才告诉芸芸那张让芸芸谨守一生的,误以为是俊彦亲书的“相见不如不见”的字条是明明写的,这样一来,芸芸一生对无爱婚姻的隐忍似乎都成为笑话。如果说《最爱》中展现的是道德以及虚伪的男性对女性的伤害,那么在《莎莎嘉嘉站起来》(1991)中,女性的困境则更难以逾越。嘉嘉先是遭遇了丈夫的出轨,丈夫对女性可谓毫无尊重,声称嘉嘉是一个永久停车场,而第三者则是公共停车位,男性的“车”有自由选择停放的权利。显然这一段婚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嘉嘉搬出来努力进步。而嘉嘉妹妹莎莎的感情也并不顺利,她先是爱上了一个有妻室的摄影师,在斩断情丝之后,莎莎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而社会又对于“女大男小”的恋爱关系极为不宽容,这段感情也只好宣告结束。
女性同性之间的爱情也是张艾嘉关注的女性困境之一,女性本就居于弱势,而同性恋的性取向则更增加了她们处境的不利。如在《20 30 40》(2004)中,20岁的小洁按理来说是三个女性角色之中因为年轻而优势最大的一位,然而她却在和另一名女生组合成类似“Twins”的双人组合过程中暗生情愫,这让她困扰不已,最终,小洁只能给对方一个吻,回归到异性恋为主流的世界中来,而没能进一步正视自己的性取向。与之类似的还有如《新同居时代》(1994)和《心动》(1999)等。
(二)对女性体验的表达
由于本人便是女性,张艾嘉往往能细腻地表现女性的内心体验,引发观众的共鸣。例如在《20 30 40》中,40岁的施亦梅经营花店,却在送花时发现订花者正是她婚姻的第三者,而对方正是要花来庆祝和她丈夫的周年纪念,这对于施亦梅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为此施亦梅才会在丈夫的故意刺激下马上提出了正中对方下怀的离婚;30岁的空姐想想徘徊在两个男人之间,因为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在房间中死去无人发现而急切地想结束单身。《最爱》中芸芸拒绝俊彦的项链,因为“我怕我拿了你一样东西,就想要更多”。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想法,都出自女性独特的思维和体验。
(三)对女性蜕变的赞颂
1987年之后,随着台湾的“解严”,整个台湾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在海外受过教育,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熏陶的女性的领导下,台湾的女性主义运动也空前高涨,这对于文学、电影等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不少台湾的乡土文学开始深入女性深邃的内心世界,而这些作品又被改编为电影,使得这一时期的电影“有不少是以刻画女性的坚毅角色而成功跃出银幕,而女性的成长更成为一个执着而自觉的命题”。张艾嘉的《少女小渔》(1995)尽管出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而非台湾乡土文学,小渔也是一个来自内地的角色,但电影却是后“解严”时代台湾女性自觉电影的代表。小渔原本为男友江伟而活,先是在美国非法打工,随后又准备和生活潦倒的老头马里奥假结婚以获取绿卡。然而在和马里奥的相处中,小渔意识到了尊重自己,为自己而活的重要性,同时也看清了江伟的为人,最终陪在马里奥的病榻之前,从此不再以江伟为自己生活的中心。与之类似的还有如《梦醒时分》(1992)中摆脱被包养身份的“港漂”马莉,《心动》中品尝过人生起落滋味的小柔妈妈等。
三、张艾嘉的女性出路探索
如前所述,张艾嘉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角度,为女性的自我解放提供了一个方向,但这并非终极答案。在张艾嘉看来,传统是需要被挑战,但是又难以被颠覆的。正如鲁迅等人曾经思考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给出一个“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悲观的答案,张艾嘉也并没有让其电影中的女性拥有一个肯定的,幸福的结局。张艾嘉电影的结尾,往往是留白式的,虽然女性主人公相比之前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开始觉醒,逐渐找回了自我,但是觉醒未必能指向一个好的结局。
在《20 30 40》中,施亦梅在感情破裂之后,能够果断离婚,这固然是她独立、坚强的一面,但是她一心想再次获得爱情,好证明自己依然是富有魅力的,于是她先是流连在酒吧之中,试图在这里猎取爱情,即使不能得到共度一生的人,有身体上的接触也能让她感受到男性对自己的肯定,以及作为对前夫的抱复;后来施亦梅则是改用打网球的方式想获得年轻男性的青睐,收获的却只有肌肉的酸痛和心灵的疲惫。最终,施亦梅只有一个与女儿同过圣诞节的愿望,而即使这个愿望也因为女儿要去滑雪而没得到满足,施亦梅还要故作无事地在电话中安慰女儿“妈妈有很多朋友”。电影的结尾,晨跑的施亦梅被一个帅气的男性看上,电影戛然而止。两人是否能成为合适的伴侣(甚至女性是否一定要有一个伴侣),电影显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又如在《少女小渔》中,小渔最终拿到了绿卡,可以在美国重新开展生活,但是美国也并非天堂。电影结尾江伟犹豫地找上马里奥家,敲了门后却最终还是走了,这被理解为他心志不坚的表现。小渔站在马里奥的床边,没有出去面对江伟,实际上是用沉默和回避的方式结束了这段感情。而在马里奥死后,小渔将何去何从,由于华裔的择偶选择有限,她是否又会遇上下一个霸道自私的“江伟”,是否终身没有情感依托,这些都是有待观众自行想象的。
女性的觉醒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张艾嘉的留白结局指出,仅仅觉醒还远远不够,实现在经济、人格上的独立仅仅是女性的自我提升,但是外部社会给予女性的不公正压力依然存在,如果电影中的女主人公都从此走上了一条人生坦途,那么无疑是在营造一种乐观的假象,在间接地为男权社会进行辩解。时至今日,女性依然没能取得与男性平等的位置,女性依然处于弱势,女性最终将有怎样的出路和归宿,女性在对传统说“不”后,还会遇到怎样的挫折甚至后悔,都还是未知数,这些正是张艾嘉用电影留给观众思考的问题,也是其电影的深度所在。
张艾嘉在电影中进行自我表达,以一种克制内敛而不乏温情慈悲的方式书写“她历史”,真实地再现女性心理,改变了男性在电影中的单一视角,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了女性的立场与精神世界,这对于男性话语权来说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挑战。同时,张艾嘉的电影,又为女性在意识觉醒之后的出路进行了探索,暗示了女性走向自由之路的漫长与艰辛,这样的设计包孕了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在庞大的华语影像世界中,张艾嘉的女性书写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