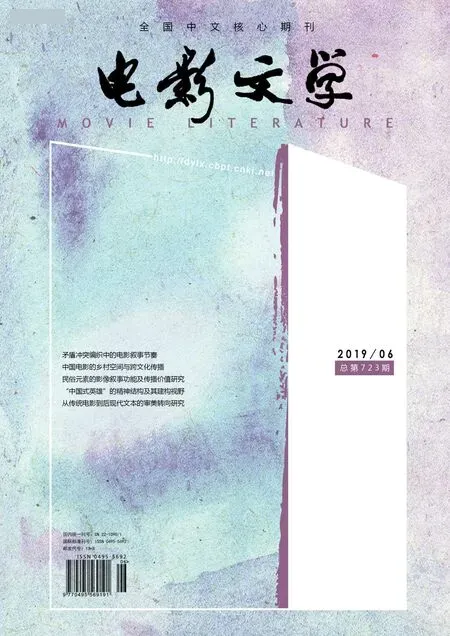从梅兰芳的电影生活看他的电影观
沈后庆 (广西艺术学院 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梅兰芳爱好广泛,除了擅长京、昆之外,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诸如字画、电影乃至舞蹈、体育等几乎无所不涉,无一不通,海纳百川的胸襟对他艺术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也是形成其自成一格“梅派”艺术的重要基石。考察梅兰芳近现代以来的从艺、商演生涯中,可以看出他在戏剧商演之余,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初20世纪头10年代抱着娱乐的态度观剧,到20年代的初次“触电”,再到30年代出访考察以及频繁与中外电影人士的互动,再到40年代摄制成真正意义上的有声影片,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拍摄关于本人的纪录片,梅兰芳在不断演戏、观剧和电影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并从感性到理性,形成了基于戏剧基础上的电影观念。具体而言:
一、电影的审美、教化功能高于娱乐功能
在一封答复美国记者阿维兰脱女士询问梅兰芳对中国旧剧和电影看法的信件中,梅兰芳给予了这样的回答:“中国各种旧戏,演唱已久,而仍能受社会之欢迎,此诚极奇妙之事,推原其故,当不外乎旧剧之演作唱白,乃至喜怒哀乐种种表情,均有一定之规则,而日成一种特殊之技术,观剧者能于此种特殊之技术,积有经验,以了解演唱之意思,斯能感受趣味,故观众对于旧戏,于特殊之技术,批判各伶人演唱之优劣,伶人亦于此特殊技术中,研究其变化,以充分发现剧之情绪,台上台下互相呼应,故戏剧虽旧而趣味常新,旧剧所以维持不败,此实最重要之原因也。”[1]“且旧戏有以善为目的者,如劝善惩恶,教忠教孝之类,有以美为目的者,如注重歌舞服饰之剧,及描写悲欢离合之剧等类,此与社会生活之关系,颇为切妥,亦其持久之原因。至鄙人所扮演角色,重在将各种妇女性质,恰如其分以表现,而对于妇女等角,所以幸负时誉者,则以古代装束本为最美也,鄙人素嗜电影,欧美各国有名之影片来华演映,几无不往观,就中尤欣赏者,为葛力夫氏所编之《赖婚》,其余电影如星,如飞尔班玛丽辟克福假波林康斯钿罗克诸伶之佳,亦极喜观之,鄙人亦曾演映电影,认为极有兴味之一事,他日甚愿投身电影界,以促进中国之电影事业也。”[2]
概括而言,梅兰芳对于中国旧剧何以富有魅力的理解,强调了三点:第一,中国戏曲具有程式化之美,对演员技术要求很高;第二,戏曲具有教化之功能;第三,强调了戏曲角色,尤其是旦角服装之美。简言之,就是戏法技术之高,教育功能之大,舞台装束之美。梅兰芳还以观看《赖婚》以及列举当时西方电影明星为例来证明自己对电影的喜爱。梅兰芳还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电影是一门“极有兴味”的艺术,表达了投身电影的意愿,但他并没有过多谈到电影艺术的特点,更没有讨论电影和戏剧的区别,原因在于一则当时他对于西方电影尚停留在观剧的兴趣层面之上,自身研究、实践不多;二则西方电影刚刚兴起,处于默片时代,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表导演甚至剧本的水平,尚未达到戏曲的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梅兰芳固然认为电影有娱乐的功能,但那种不讲究艺术性的电影不在梅兰芳的喜爱名单之列。1930年梅兰芳访美之时,正是有声片兴起的时代,电影艺术和风格都较之默片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商业至上的歌舞片梅兰芳不是特别喜欢,之后好莱坞出现了大量的文艺片和凶杀暴力恐怖片,比较之下,梅兰芳表达出对后者“这类电影的兴趣不大”,[3]32可见梅兰芳的电影观之一,认为电影的教化、审美功能高于娱乐功能。
二、电影艺术的独特性
梅兰芳在回复外界认为他将把《霸王别姬》一剧拍摄为有声电影的传闻时,就戏剧摄成电影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盖旧剧之作风,与影剧绝对不同,将来摄制是否,须将旧剧场次及其表演,稍加修订,亦为一大问题,在片上发音,与说白及歌唱方面,业告成功,然以制旧剧,凡所表演,一举一动,均须受音乐之节奏,则当如何使有更进一步之成功,方能益臻美善,故目下关于收音及戏剧,君须俟研究满意后,再开摄制。”[4]
随着拍摄经验的增多,梅兰芳对电影艺术独特性的认识逐步加强。1924年在拍摄了《木兰从军》和《黛玉葬花》后,他就认为戏曲舞台时空变换自由,苑囿于当时电影技术并不完善,时空变化大的戏剧就不适用于拍摄写实的电影,所以他说:“我觉得京戏里像《黛玉葬花》这一类故事题材,比较适合电影的要求,可以使演员不受约束,尽量发挥。”[3]21
20世纪30年代以来,梅兰芳对电影艺术的理解越发深刻。1935年访苏期间,当时梅兰芳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合作拍摄有声影片《虹霓关》中东方氏和王伯当对枪歌舞一场。爱森斯坦说:“这次拍电影,我打算忠实地介绍中国戏剧的特点。”对此,梅兰芳就表达出对拍摄此剧的看法:“像《虹霓关》这场‘对儿戏’,有些舞蹈动作必须把两个人都拍进去,否则就显得单调、孤立。所以我建议少用特写、近景,多用中景、全景,这样,也许比较能够发挥中国戏的特点。”[3]51这些建议的合理成分就被爱森斯坦予以了肯定。其实梅兰芳第一次拍摄的电影是昆曲《春香闹学》和京剧《天女散花》,也是基于认为这两出戏身段较多,适合拍摄电影这个原因。
1948年拍摄《生死恨》时,因为此剧不是舞台剧纪录片,而是电影艺术片,布景就需要认真设计,对此,梅兰芳就给导演费穆提了很多意见。梅兰芳说:“《生死恨》是宋朝的事,在用景方面,更要注意这一点。但我并不是说要按照时代来设计布景道具,当然还是应该根据戏剧的习惯来适应电影的要求。”[3]69在以后的拍摄中,导演费穆就对梅兰芳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考虑。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文化部准备给梅兰芳拍摄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梅兰芳认为要想拍好这次的影片,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剧目问题,有些戏虽然在舞台上很出色,但未必适合于拍电影,因此要选择合乎电影艺术要求的剧目。另外,有关布景、化妆、服装、表演程式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也都要仔细推敲。”[3]80在以后实际拍摄过程中,梅兰芳更是从剧本、特技、色彩、化妆等方面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比如他说:“我总觉得,电影艺术表现手段的有利条件就在于能运用镜头的远近和不同的角度来强调剧本中突出的思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他还举出特写镜头在《宇宙锋》中的运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梅兰芳还认为“有些戏在舞台上不好处理”,但是只要导演和摄影师熟悉戏曲舞台的特点和结构,“灵活运用镜头,使电影艺术与戏曲舞台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做到水乳交融,似断还连,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就能使二者的结合臻于完善的境地。”[3]105-106至于如何把戏曲写意、洗练的特点和电影写实的特点有机集合起来,就需要双方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
三、电影的局限性
梅兰芳满怀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也认识到电影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但不意味着他对电影发展的盲目迷信。1935年梅兰芳赴欧回国抵达香港时发表了谈话,对欧洲各国的戏剧给予了评价,认为通过对苏联二十几个剧场的参观考察,“只有一家演出宣传意义之戏剧耳”,意谓戏剧替无产阶级宣传的时代过去了,已走上了百花齐放的道路,并对当时舆论界过分夸大电影发展态势的声音给予批评。他说:“至于电影有占据舞台剧取而代之之问题,则余等以为戏剧有其固有之艺术,如颜色方面,立体方面,感觉方面等。电影虽然进步,似对‘取而代之’方面,有不可能之事实,何况电影可以剪接修改,而戏剧一经演出,即不可收回乎。”[5]这种观点梅兰芳在苏期间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交流时候就曾表达了出来。梅兰芳说:“电影虽然可以剪接修改,力求完善,但舞台剧每一次演出,演员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天才,给观众以新鲜的感觉。例如我在苏联演《打渔杀家》就与在美国不同,因为环境变了,观众变了,演员的感情亦随之而有所改变,所以电影对舞台剧‘取而代之’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3]54
无论是访美还是游欧,梅兰芳都和电影人有过密切接触,电影艺术也随着科技发展而强势崛起,但是梅兰芳基于对包括中国戏曲在内的戏剧本体的深刻理解,清醒地认识到电影较之戏剧有很多的局限性,尤其从戏剧艺术固有之美处与电影艺术进行观照,从而得出电影不可能取代戏剧的结论,这种观点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仍然是经得住考验的。
四、电影传播的重要性
梅兰芳认为电影艺术可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的舞台艺术。梅兰芳说:“在早期,我就觉得电影演员的面部表情对我有启发,想到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戏,这是一件憾事。”他还举出杨小楼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们老说我的戏演得如何如何的好,可惜我自己看不见。要是能够拍几部电影,让我自己也过过瘾,这多好呀!”[3]3
有署名“聊止”的《梅兰芳今后之事业》一文,对于梅兰芳赴美提出期待:“一、考察欧美剧场状况,及戏曲学校情形;二、赴电影中心之好莱坞,考察电影事业;三、表现中国旧剧之奥妙,以及音乐行头之美。”“归国后,梅应建设之事业,一、建筑大剧场;二、开设戏剧学校;三、组织电影公司。此于三项中,为着手改良中国戏剧与电影之准备。”[6]可以看出随着对电影认识的深入,梅兰芳有了投身电影界的愿望,外界也对此多有希望。
1930年梅兰芳在美考察了好莱坞,看到了美国电影的发达状况,更加激发了他投身电影界的热情,尤其对摄制有声电影很是期待。“他说,要演制有声电影的主因,不是希望销流在美国里的,他的志愿是演制声色双全的影片,贡献给居住在中国边疆和孤寂的村镇城邑里的居民,好让他们有机会领略本国古派名贵的戏剧呢。梅兰芳说,一个伶人,就是消磨了终身的时日,也不能够周游中国境内一万五十万方里以表演他的艺术的,这回却好利用西方新式的机械做成彩色而发声的影片,把中国世代传下来的名贵剧本——有些竟是原始于第三第四世纪的了——传遍遐迩呢。”[7]
如果说梅兰芳早期对电影的实践出于爱好和商业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对此项艺术认识的深入,他一方面认为戏剧较之电影有无可取代的地方,一方面也认识到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威力,尤其是电影的可复制性,为戏曲艺术的传播打破时空限制提供了可能。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梅兰芳归隐复出后,自觉受制于身体因素的限制,舞台艺术在演出、传承上都是个很大问题。在漫画家丰子恺对梅兰芳的访谈中,梅兰芳就表现出摄制影像的方式保存自己舞台表演艺术的迫切感。[8]在他预计拍摄的宏伟计划中,包括完整的《贵妃醉酒》一剧,《霸王别姬》一出,以及将《洛神》《思凡》《生死恨》《穆天王》等剧的紧要场次。[9]后来在选定《生死恨》作为中国第一部五彩电影的拍摄剧目,有记者问起“此片问世之动机”时,梅兰芳说:“我这次拍演电影有两种目的:第一点是许多我不能去的边远偏僻的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点,我几十年来所学的国剧艺术,借了电影,可以流布人间,作为我们下一代的艺人一点参考的材料。”这和他访美后的想法是一致的。导演费穆也说:“梅博士和他的时代的伙伴,——例如周信芳、盖叫天两位先生,——几乎一致地有了这样的警觉,他们认为当代的评剧家的任务,已不仅在登台献艺,供奉观众,也不仅在改革旧剧内容,硬放天足,主要的,有意义的工作,不如把够得上水准的演技记录了,在夕阳黄昏,稍纵即逝的时候,留给人一点‘规矩’,给人批评和给人观摩。”[10]
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梨园艺人充分认识到了电影艺术的复制性在传承后人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不遗余力,在有生之年摄制保存了大量的舞台作品,使得后人能够通过影像直观感受到中国戏曲的魅力以及他们代表的流派风格,在当下戏曲式微的语境中,这种忧患意识对我们更具有警醒和借鉴意义。
五、结 语
从1920年拍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一直到1959年拍摄《游园惊梦》为止,梅兰芳始终和电影相伴,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对电影的独特理解,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这点难能可贵。梅兰芳对电影艺术的实践,凸显了他对新媒体、新艺术发展的敏锐感觉,尤其应当指出的,梅兰芳认为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戏曲电影也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958年梅兰芳参与了苏联导演柯米萨尔热夫斯基全景电影《宝镜》的拍摄,他说:“我这次拍过全景电影之后,对用全景电影来表现戏曲艺术有些想法,觉得全景电影的镜头给演员的活动范围较为自由,在表演时不必顾虑到动作是否会出画面;虽然有两条缝线,但容易避开,不致成为演员精神上的负担。我想今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两条接缝的痕迹是有可能完全消灭的。”梅兰芳认为:“全景电影适宜于拍摄风景和大的群众场面,在各种电影形式中是别具一格的。”1960年梅兰芳第三次赴苏访问,看到了环幕电影,这让他“兴奋不已”[3]134。梅兰芳还说:“随着电影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何运用宽银幕电影、全景电影,以至环幕电影来记录和表现我国的古典戏曲艺术,都将逐一作为新的课题提到我们的面前,有待我们去热情探索和努力钻研。”[3]166当下电影艺术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也有力诠释了梅兰芳与时俱进的理念。
总之,梅兰芳喜爱电影艺术,一方面为了观赏,一方面为从银幕上吸取艺术素养来丰富自己的舞台艺术。从娱乐到实践,从感性到理性,梅兰芳的电影观念始终与戏剧相互观照,特别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梨园艺人,他固然认为戏剧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但包括唱片、电影等新兴艺术的可复制性和传播迅捷性都是舞台艺术无法相比的。梅兰芳对电影艺术的实践,有利于其艺术的传播,对他海上形象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梅兰芳等艺人灌制的唱片和摄制的戏曲影片成为珍贵的资料,而他们保留声音、影像,传承艺术的想法富有远见,更是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