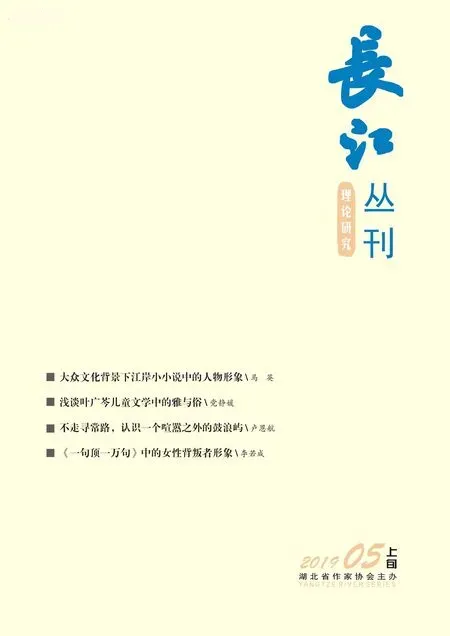大众文化背景下江岸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
/信阳农林学院
一、大众文化与小小说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中最早出现。“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对大众文化这一个概念的定义在学界始终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社会各方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也都是众说纷纭。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的过程中,不管是对新时期文学还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社会生活都影响巨大。作为一种从属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独立文体,读者对于新时期小小说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新时期的小小说也被称作是“平民艺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小小说》杂志主编杨晓敏先生认为:“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味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大众文化做为一种文化概念传入中国实际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新时期小小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登上创作舞台也是生逢其时。小小说做为小说问题的一种补充,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和旺盛生命力。它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中缤纷的世俗生活,用一种亲切的真实感,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欲望。小小说植根于大众文化,发展于时代语境,它依托着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之处,从多方面、多角度满足了新时期浮躁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文化需求。
二、江岸小小说创作背景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众文化作为世俗的、商业的、消费的文化,使得其笼罩下的文学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近年来许多登载着小小说的网站又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读者阅读更加便利,同时能够在网站上随时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是自己创作的作品。于是,我们可以说小小说的出现降低了人们参与文学创作的门槛,也增加了人们对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
基于中国小小说创作的大背景,江岸在进行小小说创造时决定将故事背景植根于生他养他的现实生活,这也导致了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总是给人活灵活现的生活气息。江岸在《我的小小说创作》一文中写道:“每次写黄泥湾,我都看见孩提时期的许多人,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我的童年时期,和当下的生活格格不入。我的父老乡亲和所有地方的人一样,善良,淳朴,勤劳,但也有很多人性的自私,山民的狭隘。但就是这样的山水养育了我,那个时期的生活给我打下了太深的烙印。我更喜欢忆旧,只有那个时代的乡村才属于我。我在那个时代切切实实地生活过,生活苦涩困窘得难以想象,但那时我们无拘无束,我是快乐的。现在的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村庄与时俱进了,我也不能再落后。我希望自己从古旧的废墟里走出来,呼吸一下新世纪的空气。未来的黄泥湾一定是旧貌换新颜的。”正是作品扎根于农村的真实生活,江岸笔下的农民和小人物形象更是显得更加的耀眼。
三、江岸小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农民这一群体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学形象,农民身上身上所体现的勤劳、善良、坚韧等优良品质,及所散发的乡土气息等都为人所称赞。同时,农民形象所具有守旧、小农意识等又为人所批判。无论现实世界中的农民群体,还是文学世界中的农民形象,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当代小小说发展与成熟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农民由传统走向现代所经历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
他们勤劳善良、简朴务实,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自己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比如《稻草人》中老人做稻草人,初衷是留着驱赶鸟雀的,让他把第一个稻草人画成张飞像,在雕琢心理的同时,细腻地赋予道具灵魂,让人物与道具合二为一,动感立体,既体现留守的孤单,又演绎英雄式的悲壮,给人以美感,也给人以震撼,文学的魅力,由此舒展。
有人说,语言和细节,就是小小说的空气和水。“溜溜的小风”、“哗哗哗划过”的鸟雀、“嗬嗬地吆喝”、“呵呵呵地笑”等重叠词的反复运用,含蓄而又张扬,处处荡漾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老人用焦炭给稻草人画了卧蚕眉、铜铃眼、蒜头鼻子,还把过年用剩的染花馍馍的颜料找出来,兑了水,画红彤彤的血盆大口,刚刷似的乱蓬蓬的绿胡子”;“拄着竹竿,慢慢走上田埂。田埂窄,泥巴稀软,杂草丛生,老人走得趔趔趄趄,好在竹竿比较结实……”等等不遗余力地细节描写,不仅控制着全篇的叙事节奏,还寓意双关地勾勒着人物形象,让结尾的升华有了立足之地。左手温馨,右手悲凉。这是稻草人的人生,更是扎制稻草人的老人的人生。作者不刻意批判,不特意谴责,却带着理解后的同情,真心怜悯,温情脉脉,将一个守望者的形象刻划出来。
四、江岸小小说中的小人物形象
小人物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它的外延比较广阔,小人物这一群体包含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人物类型,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聪敏、勇敢的本色,有时却又趋炎附势、欺善怕恶。尤其是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小人物才是生活的主角,在消解了英雄,消解了“大写的人”的时代,人小物才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存在。江岸的小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们或狡黠或精明,或愚钝或纯善,都是构成我们这个乡土世界的最主要的人群。
比如《天火》中,被天火砸到的老吕家是菊花婶的女儿未来的婆家,在黄泥湾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们认为被天火砸到是被老天爷惩罚,因此,老吕家的这场火让菊花婶心颤了。面对未来亲家的灾难,她先是送粮送衣,后来什么都送,还越送越贵重,仿佛格外地担忧女儿将来嫁过去缺衣少食。可是,这礼物送到一定时候,菊花婶就不送了,最后一次送礼时,菊花婶就告诉亲家母,今后有难处说一声,咱不是亲戚还是邻居嘛。亲家母一听,再仔细一算帐,就明白了,菊花婶送来的礼物,大概和定亲时老吕家给春兰买的东西价值相当。小说中的菊花婶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常典型的世俗小人物,她相信世俗的迷信说法,认为被天火烧的人家一定是有问题才会被老天惩罚,她不愿女儿嫁进一个有问题的人家,她精明而又不失原则,为了不占亲家便宜,她将当初收聘礼的等价金额息数买成礼物送给亲家,但却不说破,直到最后钱礼两清,才将退了亲事的话出口,而且也不轻易撕破脸皮,还好话好说,以后还是邻居。没有不计回报的善良,没有甘苦与共的境界,也没有高尚无私的情操,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世俗人,只想过平凡的生活,而这样的形象,其实正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写照。
又如《寻死》中八十多岁的牛德益老汉一反人们渴求长寿的愿望,一心求死。他觉得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都已经奔赴黄泉了,自己反而面色红润地活着,这太不应该,他不断地说自己活够了。尤其是当大儿子和二儿子先后离世后,老汉想自行了断的心就更加坚定了,因为黄泥湾有个说法:老人长寿,必妨小口。老人坚信是自己的不死妨碍了子孙们的健康,而他又怕死的太痛苦,所以想死得干脆一些,为此,他想了很多种死亡的途径。最后,他在一天深夜喝下了半瓶农药,却被半夜起来小解的三儿子发现,子孙们要送他去医院,他拼命地反抗,却看到了三儿子鼻孔里掉出的血珠。小说塑造了一个纯善而朴实的老人,他没有什么毫言壮语,也丝毫不以自己的年长而摆身份摆架子,反而,觉得自己的长寿是有害的,他想死,但又怕一次死不了,不能痛快的死,怕受罪,甚至为如何死而绞尽脑汁。同样,没有赞美高尚的人格,没有嘲笑怕痛的软弱,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纯良而朴素的老人形象。英雄消解的大众化时代,真正令读者为之感动的恰是这些普通人。
五、结语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大众文化背景下江岸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分别是守望与转变中的农民,徜徉在尘世的小人物,笔者在分析中发现,江岸非常擅于抓住时代的脉搏,塑造出贴近生活,而同时是经过艺术加工处理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江岸的作品中融入了很多他对乡村、对农民、对小人物、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也展现了很多闪光的东西。江岸对豫南这片古老地域风土人情的解读,具有独特而精准的辩识度,作为一种地域抒写,江岸的作品具有一种历史留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