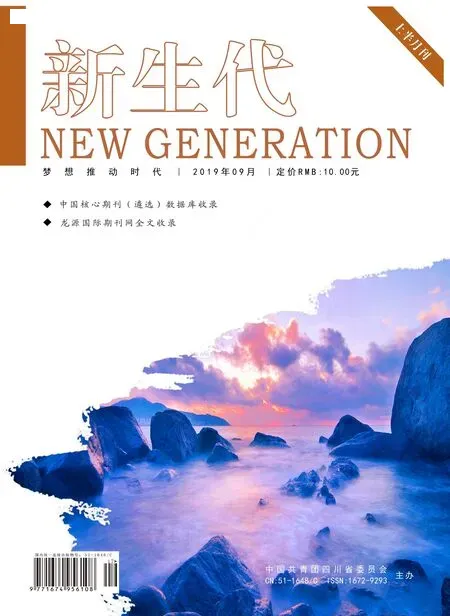新高考改革中选考对高校专业教育影响研究
——以2017届、2018届浙江省考生为例
陈渊 杭州师范大学 311100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逐步推进,至2019年全国相继有24个省市启动新高考。高校作为生源的输入处,对考生的选科、报考等都起到先导作用,应当在高考改革中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参与问卷的389位2017届、2018届浙江考生对本科学习现状的反馈及三位高校教师的访谈来看,部分高校应对选科的举措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实现高校自身建设的同时,倒逼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完善。
一、新高考改革科目选考对高校专业教育的新导向
(一)学科定位需明晰,学科建设需特色化
在改革中,取消传统的文理分科,实现科目选考,考生可自由组合选考科目,高校提前公布专业设置和相应的选考要求。参考浙江教育考试院数据,2017年在浙招生专业中,约三分之一专业无选考科目要求,故考生选考任何科目都可报近六成专业。
这一定程度上源于高考改革的初次试行,也体现高校对自身专业建设尚不自信,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较模糊,对学生日后的专业学习埋下了选考科目难以适应专业学习、基础知识分层显著的隐患。
(二)选考科目需确定,科目选择需精准化
高校学科定位不够明晰,造成选考科目的要求不够精细,而考生只需满足一项选科要求即可,这对高校招录适合本专业的学生、学生适应高校教育带来挑战。在需要理科基础的一些专业中表现地尤明显,以浙江物理选考为例,2017届考生中选考物理的比例仅41% ,从杭州师范大学(下称“杭师大”)物理系老师的访谈中得知 ,有一定数量的非物理选考考生进入与物理学科具有紧密联系的专业中。故高校应加强专业建设,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将选考要求精细化。
(三)培养方案需调整,人才培养需个性化
同一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理工医学类专业,因来自不同生源地、选考不同科目而表现出知识结构的明显差异,在学生群体中出现专业分层,这是高考改革后高校所面临的新问题。在复旦大学,“2017级本科生入学后的大学物理第一次期末统考,上海、浙江生源学生不及格率比过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达30%)。” 。因此,原本面向专业的培养方案在改革后已表现出不适应,应向适应学生的个体、小群体状况作出个性化转变。
二、新高考改革科目选考倒逼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一)加强优势学科建设
专业选考科目设限模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专业过多不够优的问题。“专业+学校”的志愿填报迫使高校发展优势专业、特色学科,以体现在招生中的优势,放弃不擅长专业,改变“千校一面”的发展原貌。一方面给传统意义的“名校”带来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普通高校通过发展优势学科以吸引人才带来可能性,促使高校建设一流学科。以杭师大为例,以小学教育为代表的师范类专业发展势头高,2019年的省内招生排名约在一万五 ,体现了师范类院校的治学之本。
(二)合并大类招生,推进大类培养模式
面对招生压力,许多高校对改革地考生采用“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模式,大一以大类学习打基础,到大二进行专业分流,使学生在有一定专业基础后进一步选择更细化的专业发展方向。
考生的选考科目大多在高一、高二上学期确定 ,通常尚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高校实行“大类培养”有助于学生进入大学后进行二次职业规划,也提高转专业的成功率。高校在转专业上也为适应改革作出调整,如杭师大大类专业中师范与非师范班可以通过专业分流直接分化,不需要转专业 大一时师范专业可零门槛转入与转出。
(三)实施分层教学,实现以生为本
由于选考科目选择、专业学习基础的差异等原因,新生进入高校后的专业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分层,众多高校为适应不同选考组合进入同一专业的状况而开设大类平台课等基础性课程。然而这类课程并不适用于两类人:其一是大部分来自尚未实行高考改革省市的考生 其二是来自改革省市,但选考科目与专业相匹配,或能够适应专业学习的同学。对于他们,一个学期的基础性课程无异于不必要的“补课”。而真正需要这类基础性课程的学生,是选考科目与专业不匹配及其他专业基础较差的学生。
因此,专业培养需精准化,可设置适当的准入标准,通过基础性测试将学生分层,如有需要则参加基础性课程,如不需要则可免修,实现以生为本,因人而异。
本质上,基础性课程的需求是高校选考科目要求不够精细化带来的阶段性问题,也是为应对改革现状而采取的临时性举措,随着高校对专业选科要求不断明确,学生对基础性课程的需求也将缩减。
在高考改革中,高校应主动扮演领跑者的角色,选考科目选择对考生进入高校后的专业学习、高校的专业建设都有重要的影响,而高校更应利用这一关联在促进自身专业建设的同时推动新高考的日益完善。
【2】 季青春:《新高考改革中高校主体功能发挥路径研究》,《江苏高教》,2019年第5期。
注释:
1.刘宝剑:《关于高中生选择高考科目的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2014级学生为例》,《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142-148。
2.访谈原话:“物理系自己有少量学生没有选物理,很多工科专业没有要求选考物理但是培养方案需要上大学物理。”
3.陆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2-26/101213962.html,2018-2-26。
4.参考《浙江2019年高考普通类一段平行投档分数线》
5.在学生问卷中比例占96.9%
6.访谈原话:“大一我们所有师范专业内部是零门槛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