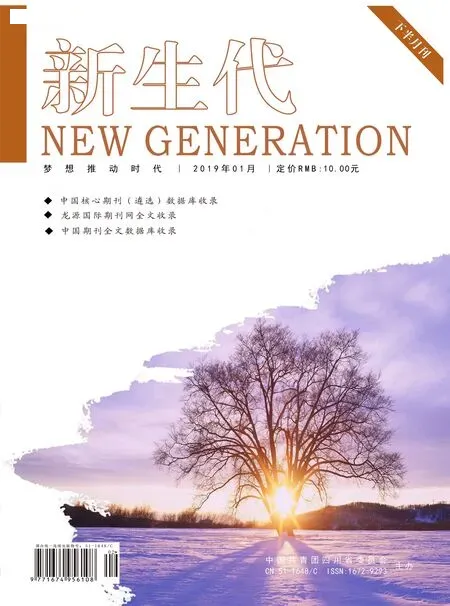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之浅析
陈宇珂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7
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现状
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下面简称《债务纠纷解释》)之前,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条有《婚姻法》第十九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简称《解释一》)第十八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简称《解释二》)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以上法条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解释二》第二十三、二十四条直接以时间为界定标准,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无论是以谁的名义都是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婚姻法》第十九条则规定,在同时满足举债人为夫妻一方、夫妻财产分别所有且债权人知道此约定的情况下,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此基础上《解释一》第十八条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在了夫妻一方这些条款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规定的很宽泛,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明显倾向于债权人一方。
《债务纠纷解释》从三个层次规范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第一个层次是共同意思表示。只要有共同借债的意思表示,所借之债都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层次即为共同生活之目的。举债为夫妻一方的单方意思表示时,只要个人名义的负债是用于婚姻存续期间的日常家庭生活开销,法院也应当认定此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第三层次首先从反面规定了不满足一、二层次条件的债务不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将此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
除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重新限定,《债务纠纷解释》还明确规定此前的司法解释与之相抵触的内容全部无效。这就意味着《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有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作废,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也应当分情况做出不同的区分。
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标准不明
《债务纠纷解释》出现了界定标准不明的问题。根据《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解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应的概念是家事代理权,与“需要共同生活需要”虽然在内涵上有重叠部分却不是同一个概念,后者与前者应该是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婚前个人债务如果用于共同生活则应当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时采用了“共同生活的概念”。而《债务纠纷解释》第二条在债务的界定上又使用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就与此前的规定在逻辑上不一致。第三条出现了两者混同使用的情况。按其字面应理解为“超越家事代理权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共同债务,除非用于共同生产生活”。笔者认为婚姻伦理性强调婚姻共同生活是夫妻关系的本质性特征,乃婚姻之自然属性,夫妻财产制是身份财产法,维护夫妻共同生活之稳定与和谐是构建夫妻财产制的重要价值理念,夫妻财产制度的修订都注重维护夫妻共同生活,强调夫妻协力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应当以是否用于共同生活作为界限,《债务纠纷解释》中若把第二条中的“家庭日常生活”替换为“共同生活”会更加合理,在立法技术上也更加统一。
其次《债务纠纷解释》在第二条的表述上有歧义。第二条原文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为”可以表示目的也可以表示事实,如果将其理解为表示目的,会扩大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将有悖于司法解释以债务用途来界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初衷。债权人是否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举债具有“合意”或“为”夫妻共同生活,与实际夫妻一方举债是否具有合意或为夫妻共同生活是有区别的,前者为是否发生表见代理法律后果的判断标准,后者是夫妻之间认定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两者不应混同。笔者认为,此处的“为”字可以更改为“用于”,这就限制了债务的实际用途,明细了界定标准。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
《债务纠纷解释》给债权人施加的证明责任过高。其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此规定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仍有失衡。此法条的内涵是超过家事代理权限的单方举债意思表示所形成的债务为个人债务,债权人除非证明个人债的标的物用途发生改变即用于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否则只能承担不利后果。表面上“谁主张,谁举证”看似公平,实则不然。因为夫妻双方相互串通更改借款用途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用于”表明债权人要证明标的物的实际用途,夫妻如果恶意串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更不要说证明双方有共同意思表示即“恶意串通”本身了。对此笔者认为可取中间地带,将其规定改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举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具有夫妻合意的,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除外”此“有理由”的法理基础就在于家事代理权。这样一来双方都负有举证义务,债权人履行初始证明责任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举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具有夫妻合意的”,夫妻中的非举债方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双方的义务相对平衡。
(三)界定标准、推定规则不加区分
界定标准是对一个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限定,而推定规则则是解决举证责任的问题,具体而言,推定受益方不需再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但仍需承担基础事实的证明负担。法条在阐述一个法律规则的时候应当区分推定规则与认定标准之间的差异,不应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与适用认定标准的程序相混同。《债务纠纷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此条款将将界定标准与推定规则杂糅在一起,造成的逻辑后果就是是否能证明用于共同生活直接决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与否。然而笔者认为不能证明并不能影响概念的内涵本身,只能决定诉讼程序中的不利后果又谁承担而已。笔者建议将界定标准与推定规则分开规定,将其表述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债务纠纷解释》大大改变了婚姻法第二十四条中夫妻非举债方承担义务过大的问题,它把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分成了三个层次,不再一律的以婚姻存续期间作为推定标准。但是也存在一些证明责任分配和立法技术上的问题,有后续改良的空间。在利用法律规定平衡夫妻非举债方和债权人的利益时,除了要谨慎衡量,使法律规则符合公平正义的诉求。在立法技术上应当更加清晰的界定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对不同的规制内容加以区分,做到逻辑自洽。我们虽然要追求司法效率,节约审判成本,而应当将二者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