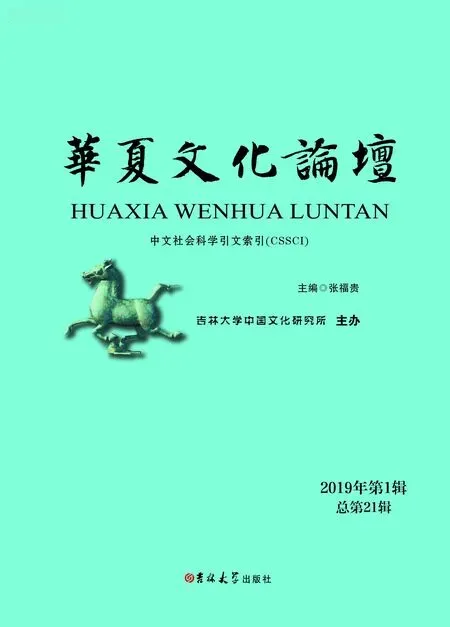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身”与“心”
——通过白居易《自戏三绝句》窥其心性
[日]中原健二 张宇飞 译
【内容提要】中唐诗人白居易曾创作了系列作品《自戏三绝句》,不言而喻,《自戏三绝句》是受到了陶渊明的诗歌《形影神》三首的影响而创作。《形影神》的主题是如何适应人生的有限性,“形”主张现世的享乐,“影”看重死后的名声,两者的对立则是“神”的扬弃。一方面,《自戏三绝句》中只有“身”与“心”登场,分别与“形”和“神”对应,而“影”并未登场。对于白居易而言,“身”与“心”似乎是一个整体,从白居易的作品中可以屡屡见到将“身”与“心”配套描写的诗句。中唐的士大夫自知人生的有限性,并将其视为难以避免的事物而接受,虽然常常倾心于脱俗的生活,却作为官僚肩负着社会责任、自知生存于俗世的职责。白居易晚年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时常吟咏“隐吏”的喜悦。但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达到了内心的平静,对他而言只是作为士大夫对生存方式进行再确认的一环而已。吟咏“身”与“心”的系列诗歌正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白居易是中唐士大夫中最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这一点可以说与之后的宋代的士大夫们相通。
前 言
“如何对待生命的有限性”这一命题在中国从古代开始就紧紧抓住人们的内心而难以释怀。由于人们从古代开始就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摸索,因此有考虑长生不老的仙药是直接的解决方案,也有从内在方面如老庄、佛教等这样的在思想、宗教的层面上提示的精神方面的解决方案。在文学作品里这个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例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形影神》等都各自在吟咏这一主题。
生命的有限性谁都无法逃脱,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那么作为士大夫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呢?虽然在“在俗”(做官)与“脱俗”(隐逸、归农)之间左右摇摆,但由于意识到自我的职责,带着所谓“放弃脱俗的觉悟”而选取“在俗”的生活方式,不正是中唐以后的士大夫们吗?
白居易于开成五年(840年)、六十九岁之际作为太子少傅在洛阳担任分司时创作了《自戏三绝句》,这篇作品让我们引起前面的思考。本稿想从“身”与“心”的表现用法出发来考虑并观察白居易的精神状态。
以下白居易的诗引用自中华书局出版的《白居易集》,其他的唐诗则来自《全唐诗》。另外,白居易诗歌的创作时间是根据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
一、《自戏三绝句》与《形影神》
《自戏三绝句》由《心问身》《身报心》《心重答身》等三首组成,这很容易看出是在意识到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诗之后创作的。事实上,从《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开始,白居易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已经是众所周知之事了。
那么在进入《自戏三绝句》的内容前,想先简单确认一下《形影神》这三首诗。
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的序是: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如此所述,采取用“神”来扬弃“形”与“影”的痛苦的体裁。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悽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感叹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重视现世的快乐而劝告“得酒莫苟辞”。对于忘却生命的有限性的悲哀,大概就是最一般的方法了吧。“影”这样回答: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崑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愁,方此讵不劣。
“影”暂且承认生命的有限性(“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用酒最终不能断绝悲哀,只有积累善行才能让人们永远记住自己(“立善有遗爱”),总之,就是说死后如果留下名声便可超越生命的有限性。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神”指出了两者的对应方法的无益之处,对“形”说“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对“影”说“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其实不应如此,并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是最好的方法,果然那是可能的吗?让“神”如此劝说,陶渊明连稍微一点儿的动摇都没有吗?
《自戏三绝句》也有一个短短的序:
闲卧独吟,无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戏,往复偶成三章。
诗题云“自戏”,序云“相戏”,但其所咏内容却不能看作如字面般的“一时的戏谑”。当然这带有轻快的腔调,白居易虽在闲职,但反省身为官僚的自己,其感其思是从诗中可以看出的。首先是《心问身》,“心”向“身”发问:
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
白居易于大和三年(829年),在五十八岁之时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之职任洛阳分司,之后除了任河南尹的两年多以外,在洛阳作为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分司,末句说的正是此事,“心”向“身”说“你得到快乐是多亏了我下了退向洛阳的决心”,对于此,“身”在《身报心》中如此回答:
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
你之所以安稳正是因为我把你放置在我这里。希望你不要说以恩人自居的话。之后,在《心重答身》里,“心”又说:
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
由于我是个懒鬼,你才能到现在为止获得长年的轻松快乐,还是多亏了我的帮助。如果你得不到快乐的话,我将会变得怎样呢?
“身”与“心”相互主张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毫不退让,采用相互争论、刺激的形式正是“自戏”的主意和目的,但说到内容还很难说是“戏谑”。白居易对自己过去的思念与感慨都集中包含在这里了。但是,《形影神》三首从正面对待生命的有限性传达作者迫切的感情,而相对于此,《自戏三绝句》至少从表面上没有那种迫切感,并且不是“形、影、身”而是“身、心”。“身”可以被认为是对应陶渊明的“形”,“心”可以被认为是对应陶渊明的“神”,但“影”并没有出现。
二、唐诗中的“形、影、神”与“身、心”
那么在唐诗中“形、影、神”是怎样被吟咏的呢?这三个字在一起的例子几乎没有出现过。出现词语“形影”或是“形”与“影”成对出现的例子却非常多,但几乎都是指灯火与灯火下的影或者镜中的影等,还有作为“不即不离”的例子使用的“形影”、以及指人或其面貌的“形影”等,无论哪一个从过去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到。但另一方面,“形神”却非常少见,只能找到三十个左右的例子。但无论哪种情况下,都不能找到直接继承陶渊明的《形影神》的作品。
与此相比,像白居易的《自戏三绝句》一样将“身”与“心”成对的唐人作品却非常多。虽然如此,下面所举的例子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佛寺、隐士或者老人的作品中的“身”与“心”。
(1)了然莹心身,洁念乐空寂。名香泛窗户,幽磬清晓夕。
(岑参《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
(2)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罗浮麻姑台,此去或未返。
(李白《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
(3)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
(王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
不过,从中唐开始,官僚或将要做官僚之人的 “身”与“心”被对比吟咏的例子变得零星可见。首先,举李端(大历五年进士)的《题从叔沆林园》为例。
(4)阮宅闲园暮,窗中见树阴。樵歌依远草,僧语过长林。鸟哢花间曲,人弹竹里琴。自嫌身未老,已有住山心。
这是在访问叔父李沆的林园之际所作,明明还没有到垂暮之年(当然做官是前提),但已经产生去隐居的错觉,吟咏叔父园林的完美。接着举鲍溶(元和四年进士)的例子,这首诗被认为并不是在仕途时,而是落第归乡之际发出的感慨。
(5)如何不量力,自取中路贫。前者不厌耕,一日不离亲。今来千里外,我心不在身。
(《将归旧山留别孟郊》)
最后举出元稹的例子。此诗是元和五年(810年),三十二岁的元稹从监察御史被贬到江陵士曹参军时赠给当地同僚的诗。元稹从仕途开始之际到被贬江陵的状况如下所述,作为官僚的“身”与“心”之对比更加明显。
(6)昔冠诸生首,初因三道征。公卿碧墀会,名姓白麻称。……心虽出云鹤,身尚触笼鹰。竦足良甘分,排衙苦未曾。(《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韵》)
事实上,多次使用此类“身”与“心”的还是白居易,其诗的数量出类拔萃。现在就举其中数首来看,首先引用元和四年(809年),白居易三十八岁时作为左拾遗在长安的作品《寄元九》。
(7)身为近密拘,心为名检缚。月夜与花时,少逢杯酒乐。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
这时,元稹作为监察御史在洛阳分司而不在长安,虽然开头的“身为近密拘,心为名检缚”感叹在宫中做官的束缚,但这首诗的主调还是悲叹好友元稹不在自己身边(大概正是因为那样,白居易才把这首诗放入了“感伤诗”吧)。但是,还是想确认早已可以看出的为官的白居易将“身”与“心”相对应。
(8)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
(《闲居》)
(9)世役不我牵,身心常自若。晚出看田亩,闲行旁村落。
(《观稼》)
上面两首都是辞官服丧期间退居下邽时的作品,下面所举的例子是左迁江州时的作品。
(10)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
(《咏意》)
与在受陶渊明《形影神》意识影响之下而作的《自戏三绝句》只吟咏“身”与“心”同样,这里举出的四个例子里也看不到陶渊明的“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白居易这里,被认为他的“身”是陶渊明的“身”与“影”合为一体,但是“影”所占的比例很大。换而言之,在陶渊明这里对待生命的有限性占了很大的部分,而在白居易这里,对陶渊明的“影”所言及的“应有的人生状态”注入了很强的意识。陶渊明的“影”感叹“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白居易不是接受而试图超越它吗?对于白居易而言,作为士大夫怎样完善属于自己的生命,正是其最大的课题。
三、心的控制
(一)从下邽时代到江州时代
对于白居易,“身”可以说是等同于作为官僚的自己的存在吧。这样看来,白居易“身”与“心”的表达从生命有限性的内部解决而远离,对于做官的“身”而言,被认为将更倾向于如何控制“心”成为必然。下面让我们来看与白居易“身”与“心”相关的表达。
首先,举出其为母服丧、隐退下邽的于元和六年到九年(811—814年)、即四十岁到四十三岁之间所作的闲适诗。
(1)遣怀
寓心身体中,寓性方寸内。此身是外物,何足苦忧爱。况有假饰者,华簪及高盖。此又疏于身,复在外物外。操之多惴慄,失之又悲悔。乃知名与器,得丧俱为害。颓然环堵客,萝蕙为巾带。自得此道来,身穷心甚泰。
虽然白居易身处贫困的服丧生活,却确实咏叹了自己从官场解放出来的境地。但是,讲了“此身是外物”,接着又讲了“华簪”“高盖”等都“复在外物外”,最后断言“自得此道来,身穷心甚泰”,果真按字面理解就可以吗?西村富美子曾经论及白居易在退居下邽时的闲适诗,如下所述:
总之,诗在表面上表达的虽是闲适,但此时诗人的心情被认为并不一定也是闲适。当时赋予诗人的无限的自由虽是人潜在的欲求,但那无论如何也是日常在体制的拘束下的时候,实际上实现在自己的生活上,虽然有精神的紧张感的解放,但对于以在官僚社会中生活为人生目的的人而言,如何对待便是问题吧。笔者认为,与期待未来的官僚世界的断绝感、不用考虑明天的悠闲生活、对于这种生活半永久性持续的厌恶感等,这些感情都复杂交织,作为这一时期的诗的背景而存在的。
白居易常常吟咏退居下邽时期的闲适,其中,“身”与“心”的字眼也屡屡被使用。比如《冬夜》吟咏村居的寂寞,其主要原因写在前两句“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确实很难解读出与离开官位的关联。但是,《首夏病间》以大病后总算被放开的心情和初夏神清气爽的气候为背景,吟咏了“忽喜身与心,泰然两无苦”,却有“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的官员露面的一瞬间。接着再举一例,诗的题目《闲居》完全与“闲适”相适应。这首诗已在(8)中引用了一部分,其后接着说:
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
到了这首诗,他对于官的拘泥就更加明确了。白居易在退居下邽时期虽屡屡吟咏闲适,但实际上如西村富美子所言,他的身与心都并未到达安定的境地。
为母服丧期满,白居易于元和九年(814年)冬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复归官场。可是,仅在第二年,因关于宰相武元衡暗杀事件上书被责难为越权行为,被贬江州司马。在此很短时间的激烈变化的遭遇,对于白居易的身与心应该有了很大的打击。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的冬天抵达了左迁地江州,第二年,他作了题为《约心》的闲适诗,时年四十五。
(2)约心
黑鬓丝雪侵,青袍尘土涴。兀兀复腾腾,江城一上佐。朝就高斋上,熏然负暄卧。晚下小池前,澹然临水坐。已约终身心,长如今日过。
诗的题目《约心》不是指“与心约定”,而是指“管控心”,总之是“控制心”之意。开头四句所出示的自画像绝没有飒爽的感觉,左迁以来,由于是毫无实权的司马之职,每日的工作和思考从“朝就高斋上”到“澹然临水坐”,白居易可能有时有比下邽时代更强的闭塞感。服丧当然有官复原职的希望,但是现在是左迁之身份,经常将复兴视为乐观恐怕很难,他的思考一定在悲观与乐观之间左右摇摆,到了那样的境遇,他痛感到不得不控制内心。
接着,看看已引用了一部分的闲适诗《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是为元和十二年(817年),四十六岁时所作。“崔侍郎”是指崔群,钱舍人是指钱徽。对二人的信,白居易从左迁第三年的生活开始咏起。
旦暮两蔬食,日中一闲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
之后有引用的部分,其意思就是“世间之人都并非如此,为诸事所累而身心俱疲”。下面接着继续引用:
吾有二道友,蔼蔼崔与钱。同飞青云路,独堕黄泥泉。
两位友人与自身的遭遇成为云泥之别。
岁暮物万变,故情何不迁。应为平生心,与我同一源。帝乡远于日,美人高在天。谁谓万里别,常若在目前。
不变的友情。
泥泉乐者鱼,云路游者鸾。勿言云泥异,同在逍遥间。
我是在泥泉中游乐的鱼,二位友人是在云路中行走的鸾,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心境却相同。
因君问心地,书后偶成篇。慎勿说向人,人多笑此言。
往来的书信的内容当然无由知道,但白居易恐怕是向二人诉说通到“吏隐”的主张。
同年春天,庐山的草堂建成,白居易作《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接着又作《重题》三首,第三首广为流传,其中也可见到“身”与“心”。
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
如果看在江州吟咏“身”与“心”的一系列闲适诗,这首诗虽说是杂律诗,但颈联与尾联不难理解是在吟咏坚定的闲适境地,之后,在江州前后大约第四年的元和十三年(818年),已经四十七岁的白居易作杂律诗《遣怀》,此番与“身与心”相约定。
(3)遣怀
羲和走驭趁年光,不许人间日月长。遂使四时都似电,争教两鬓不成霜。荣销枯去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
从首联到颈联吟咏生命的有限性,末句有“生死”的词语虽然是理所当然,但也混杂着“穷通”,左迁江州时的白居易的念头常常与“做官”连接在一起。并且第七句“已共身心要约定”是他控制心的到达点。左迁江州对白居易的思想倾向、生活态度以及其诗作都是巨大的转折点。
(二)忠州以后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白居易写下《别草堂三绝句》宣布与草堂告别,转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年),四十九岁的白居易在忠州有一首感伤诗《我身》。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断,浩浩随长风。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
白居易说“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的原因是因为“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但其真实原因是因为像 “孤生蓬”那样的白居易还可能产生官复中央的可能性吧。这样,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正如期待那样官复中央,任司门员外郎。
两年后,长庆二年(822年),五十一岁的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杭州的闲适诗《咏怀》中,首先与中央任官的艰苦做对比,写出了地方官的轻松,之后,还指出心的状态的重要性而终结。白居易在江州时代以后并没有停止吟咏“身”与“心”。
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事有得而失,物有损而益。所以见道人,观心不观迹。
最后看太和八年(834年),白居易六十三岁,作为太子宾客任洛阳分司时所作的《风雪中作》。运用“身”与“心”的词眼写出了晚年的心境。至此,“身”与“心”的纠葛表面上似乎可以说变弱,但绝没有消失。
(4)风雪中作
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
暴风雪的夜晚舒适地睡觉。
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
从早到晚,身与心都无忧无虑。
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
但是,忽然想起了以前远赴为官的生活、黎明前的出勤,对自己的训导。在官期间身对这状况不得不满足,因此心必须知道自己的满足,必须控制心。末两句用“方寸”与“形骸”代替来写此意。
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
在趋向“老”这一种停滞(安定)的过程中,关于应该做官的自己的状态,白居易内部的纠葛正因为变淡,而不能消失。左迁江州时,白居易大概并没有想到后三十年之事吧,洛阳分司以后,直到晚年,屡次吟咏“身”与“心”,之所以充满闲适或吏隐的喜悦,对他而言,是“放弃脱俗的觉悟”的确认工作吧,不能把握住只是讴歌吏隐之事。
在唐代,终结了长期的分裂与不安定的时代,确立了新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寒门出身者参与政治中枢的情况逐渐增加的中唐以后,在士大夫那里,生命的有限性这一问题退为背景,在内心深处沉淀,变为时而触及时而浮出之物,取而代之,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作为士大夫应该担负责任,自己应该怎样做。总之,就是作为官僚的处身方法。用陶渊明的《形影神》来说,白居易承认 “神”的调停,其结局并不有效,确认自己的职责任务和存在意义在于听从 “影”所说的方法。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四十七岁,在江州的闲适诗《咏怀》中,特别是最后的八句,可以读出那种意思的表达。
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
结 语
以上围绕白居易的“身”与“心”叙述了鄙见,中唐的士大夫们大概作为官员都有应该怎样行动的意识。总之,在承认生命的有限性作为自明之物不得不被接受的基础上,考虑了应该为官的自我的理想状态。比如,吉川幸次郎关于韩愈有如下论述,与本文所述重合。
人所受到的种种限定,死虽然是其最大之物,但对他们来说悲伤已经并不是悲痛了。或者尽管有悲伤,但都任凭传统的诗人吟咏。人所受的限定或者万物所受的限定,对他而言是确定之物,已经变得不是他自身悲哀的对象了。
引用的拙稿里选取了韩愈的《复志赋》的“昔余之约吾心兮,谁无施而有获”、孟郊的《靖安寄居》里能看到的“外物莫相诱,约心誓从初”,其意识的基础之物都与白居易相同。
另外,川合康三也选取了感叹生命的有限性的晋代羊祜的“岘山”典故和春秋时期齐国景公“牛山”的典故,并指出六朝时期那样的感情洋溢得还要强烈:
进入唐代……羊祜以及六朝的悲伤里能够看出的感叹自己生命无常的浓厚心情,变得薄弱,……在唐代杜甫以及中唐文学者选取羊祜的典故变得稀少,以人生苦短引起他们关心的文学主题变得几乎消失,进入宋代……作为卓越的统治者称颂羊祜成为中心,羊祜所持的人生的悲哀逐渐远去。
如此说,思考中唐以及宋代的士大夫时具有启发性。白居易是其典型,或者,在中唐的士大夫中,白居易可能可以说是最具有自觉性的了。
那么宋代的士大夫们怎么样呢?作为以苏轼为首的士大夫们,很多都被认为继承了本文论及的白居易的精神状态。但是,现在笔者对其考察,还不具备论述的能力与材料。但是,白居易与陶渊明都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知识人,同是寒门出身不得不入仕为官。相对于与官场割裂靠种地生活的陶渊明,白居易怀抱着掺杂着羡慕与憧憬的羞愧的感情,对于两人的人生状况,宋代的士大夫们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大概产生了共鸣是容易想象的。
确实,白居易直到晚年,屡屡吟咏辞官隐居与闲适的喜悦。但是,那样他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平定与满足的境界。鲁迅当结束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这样说陶渊明:
据我的意思,既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这难道不是应该让我们思考吗?那也不应该仅限制于陶渊明吧。
附记:
本稿是我于2016年7月23日、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第三十一回例会的口头发表《身与心——围绕白居易的〈自戏三绝句〉的思考》的基础上总结的,当日得到了很多出席者有益的提问与意见,首先在此记录表达谢意。
拙论《关于“约心”》写作时间正好是十年前,作为总结本文所选取的主题的准备一环,是以把握“约心”的语义为目的的。但此后,由于诸多事情使得我失去了整理总结思绪的机会。现在,总算勉强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正是因为以例会的负责人杨维公为首的京都大学研究生院诸位的激发而成,在此记录表达感谢之意。
又记:本论文日文版原载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88册(2016年10月)。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