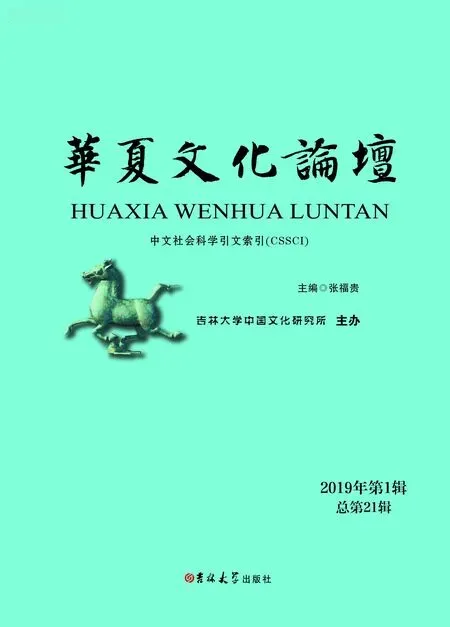遥远的银河
——儿童校园小说中的“另一种”童年书写
山 丹 侯 颖
【内容提要】校园生活作为儿童小说题材和内容的重要来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校园小说都在着力反映城市学龄儿童的生命状态。近年来,儿童校园小说在把握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新的脉搏之时,将视野拓宽到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这群有别于城市儿童群体的“另一种”童年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校园”不是儿童校园小说想象的故事背景,而是艺术化地表现儿童真实生命体验的生活场域。所以,儿童校园小说中的“另一种”童年书写更需要进一步走进这群被忽略的儿童群体的内心世界,体味他们的丰沛情感,展现“现实与理想”共筑的童年精神之实。
一、引 言
校园,是建立儿童认知事物与自我的机构,也是引导少年期的人达到尘世的完成地步的关键场所。儿童校园小说,以学龄儿童的校园生活场域为叙事空间,展现了中小学生读者最为熟悉的成长环境与生命体验。一方面,儿童校园小说的书写意味着成人对儿童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关照。与成人文学作家把校园当成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不同,儿童文学作家更应该表现出生活在真实校园的儿童生存现状;另一方面,由于儿童校园小说与教育的血脉亲缘关系,其创作担负着成人儿童文学作家对学校教育与家庭以及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及整个人类童年生命空间的审美坚守。
校园题材的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五四”文学期的启蒙式文化反思,到战争文学期的代际间伦理冲突;从建国文学期的集体式教育关注,到新时期的文学性生命反思,再到商品文学期的类型化叙事狂欢这样一个相对完善的发展过程。正如班马所说:“我国的儿童文学曾一度几乎给人一种‘学校文学'的印象。”,这一“学校文学印象”之说也印证了相关题材作品之丰富。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部分儿童文学作家仍沿袭了对城市儿童校园题材的类型化创作理念,同时,更多的作家却不约而同地“走出校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儿童小说从题材和主题到创作方式、手法都有了更为多样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直面具有时代性的当下童年生存现实时,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家在“隔与不隔”的取舍间疲于应对。正如刘绪源所说:“呼唤真正的校园小说”一样,无论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升上,当下的儿童校园小说都“呼唤”着能够直面儿童生活的作品。
作为校园题材的延续,2016年出版的“小布老虎‘好孩子'”系列长篇儿童校园小说,如邓湘子的《摘臭皮柑的孩子》、王巨成的《向阳花女孩》、冯与蓝的《穿过冬天来看你》和吴依薇的《升旗手》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来儿童校园小说创作的转向,是对农村留守或城乡流动的“另一种”儿童生存现状的一次凝眸。这几部“有温度的中国故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文学作家对“另一种”儿童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深度的理解与体味,也是“中国式童年”书写的一次有效尝试。
二、“另一种”童年的生活写真
“儿童文学是关注儿童精神生活、关怀儿童心灵成长的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就必须面对特定时代中的儿童的生存状况并对此做出能动反应。”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不断加速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出现的城乡间人口流动频繁态势,以及日益更新的现代传媒,对人类固有思维认知模式有了颠覆性的影响,也使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了儿童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于我国的儿童文学而言,如何用文学话语回应这些儿童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多元性和复杂性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已经有意识地将视线从传统的关注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群体,向更广泛、更多样的儿童群体转移。特别是儿童校园小说,更集中地展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大背景下,以及在传承传统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群体的前提下,对留守于农村里和漂泊于城乡间的不同儿童群体的生活进行了关照。如,冯与蓝的《穿过冬天来看你》,描写了来自两个不同成长环境的城市小学生如何相持面对生活困顿,在快乐与痛苦间感受友谊的真谛;王巨成的《向阳花女孩》和吴依薇的《升旗手》,分别再现了乐观开朗的进城小姐弟和从乡村来到大都市的小男孩在陌生环境中的成长快乐与烦恼;邓湘子的《摘臭皮柑的孩子》,描写了不同命运的三个留守儿童在苦难与磨砺中如何积极乐观地生活。
与市场导向下的一些关注城市中产阶级校园儿童的日常生活,迎合轻浅性与趣味性阅读需求的儿童校园小说作品不同,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家关注到了多元性儿童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内心世界,承担起的是具有文化价值与人文关怀的温度写作。这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家仍在坚守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同时,在广度与深度上已有所突破,从而也使得“中国式童年”书写更加完整与真实。
此外,作为表现学龄儿童现实生活的一种文体——儿童校园小说,能够更为准确地表现出儿童与成人的情感共鸣。特别是面对带有时代特征的新型儿童时,儿童文学作家在对儿童的生存现状进行体察时,也进一步走向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在对他们的童心世界进行叩问时,能够一致捕捉到当代不同生存环境下的儿童共同的情感困顿——孤独。曹文轩先生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化现象时,就一语中的地指出:“知识的竞争剥夺了孩子的群体活动所带来的儿童集体式孤独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儿童处境的变化,这种孤独感在一个物质极度膨胀的环境中,伴随着疲于奔波的父母对儿童的忽略,政策性压力下儿童玩伴的缺失等纷繁的原因,几乎成为一个时代儿童心灵世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反映“另一种”童年的校园儿童小说中,其表现更为突出。如,在《升旗手》中,男孩唐小鹿随父母来到城市后,面临着父母的离异,他在父母的爱恨交织的情感中,选择了跟随父亲生活。但是,父亲的忙碌使得他完全成了城市中的“孤儿”,每天都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生活。孤独是他生活的常态,一个人在冰冷的台阶上发呆;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中游荡,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吃饭,儿童式的孤独在儿童校园小说作品中刻画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摘臭皮柑的孩子》中,表现的是当下农村儿童生活的另一种现实。这些被父母留在农村的孩子,常年和隔代老人相伴,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老成的孤独,当青衫的父母回来时,这种孤独在其他幼小的孩童心中幻化成一种悲伤的嫉妒。在《穿过冬天来看你》中,女孩罗冰沁更是因为常年没有父母的陪伴而变得古怪、敏感,以及喜怒无常。即使后来罗冰沁被发现是一个家庭物质生活非常丰沛的孩子,但是在她身上仍然体现着缺少关爱与陪伴的孤独,而孤独的童心,是财富无法弥补的。
留守儿童与城乡间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似乎离我们遥远。但近年来,通过各种媒介的关注与报道,他们的种种命运牵动人心,大量的数据触目惊心,新闻报道骇人听闻。如,2017年除夕之夜,年仅17岁的留守少年因不满留守生活之悲伤与亲情间的疏离而愤然自杀。这一新闻报道立刻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反响:有人指出,亲情的分裂、失散的童年以及精神的摧残,使儿童的成长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与困苦;有人认为,儿童的留守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留守,对乡村家长的精神扶贫同物质扶贫同样重要;更有相关机构,直接发起了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与情感关怀活动。对这一特殊群体投入关切的目光和真挚的呼吁声,对他们心理与精神层面出现的问题之重视,充分体现了社会的人本情怀。然而,定式的偏见、过度的关注与繁多的报道,能否为这群儿童带来积极的精神抚慰呢?在信息时代下过度包装的儿童,是否“没有任何心情、没有任何思想、几乎连感觉也是没有的,甚至察觉不到他本身的存在”?这是需要我们时刻警惕的。
在这个敏感而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下,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在反映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内心世界上所做的努力意义重大。具体来说,尽管每一个儿童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与所有孩子一样渴望着爱与陪伴。不得不承认,这些孩子的选择大多是被动的:他们或者“被”带到了陌生城市,或者“被”留在了乡村老家,或者流动于城乡间。他们生活中的每一步都不能跟随着自己的意愿。而当父母们以给孩子创造物质财富的名义抛下他们时,带来的便是儿童情感的空白。孩子天性与本能的依恋和需要着父母。分离时间久了,他们的心灵一定会闹饥荒。与成人拥有对独处的强大适应能力不同,没有了关注与肯定,对于儿童心灵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因此,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对这一儿童群体精神世界的抚慰与关照,是十分必要的。
三、童年写实的审美反思
虽然,当下儿童校园小说创作正在试图铺展开一个曾被人们忽略的“另一种”童年的生存图景,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但是,在量上和质上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黄蓓佳在《天使街上的孩子们·代后序》中所说:“毫无疑问,儿童文学的阅读主体还是城镇的孩子,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含着金汤匙出生,锦衣玉食中长大,虽然也辛苦也挣扎,但是跟余宝的小伙伴相比,是不同的辛苦不同的挣扎。他们和余宝,也许就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彼此间的距离却如银河宇宙那么遥远。”可以这样说,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他们自发地关照了可能被忽略的儿童群体,力图展现留守和城乡流动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现实处境。然而,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儿童校园小说,在面对早慧的现代儿童读者时,缺少打动人心的艺术内核。就目前已出版的这一题材儿童校园小说来看,其内容的客观性,情感的真实性,主题的深刻性,以及创作的多样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表现“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相较于其他儿童校园小说来说,还要在童年写实方面进行审美反思。
首先,在表现儿童的生活底色上,相较于其他儿童校园小说的热忱,表现“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则略显凝滞。尽管也有类似于表现苦苦挣扎于城市底层儿童的黄蓓佳的《余宝的世界》,以及表现需要直面残酷现实的孤苦无依的农村留守孩子的三三的《仙女的孩子》等耐人寻味的作品频频出现。但是,这一类儿童校园小说在书写“中国式童年”的生活底色时是温和而保守的。也许是由于儿童文学作家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城乡间流动儿童生活的体察,抑或是距离这些弱势群体儿童的生存空间较远,所以此类小说文本中的“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更像是一个出离于现实的创作概念。如,在《摘臭皮柑的孩子》中,“留守”对于三个乡村孩子来说,只是意味着父母不在身边,以至于生活的喜怒在他们身上没有多少痕迹;《向阳花女孩》中的小姐弟虽然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却拥有完整和谐的家庭,团结友爱的老师同学,并凭借着一种“向阳花”精神解决了生活中的一切难题。这些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虽然没有落入一种刻意的自卑与内向的模式化桎梏中,但儿童文学作家对他们童年生活现实的描摹缺乏一种深沉和严肃的思索。对“另一种”童年形象缺少精准地掌握,便会出现叙述故事方式的无力,以及艺术展现形式的生涩,致使作品更像是泛化出来的模式化创作。
其次,在表现儿童复杂的情感上,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体现出不够精准性。其实,乡村儿童到城市生活时,远远超出儿童文学作家们所描写的那种理想的乐观。进城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城乡教育差距,还有城市生活的种种不适应,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评价的自卑与落差。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尚没有表现出这群儿童在适应新环境中的复杂的心灵纠葛。正如汤素兰在《我是小丑鱼》中描写的男孩,在乡村小学的优秀,在城市中却被打击,所以自嘲为“小丑鱼”一样,生存环境的改变对于建立秩序期的儿童来说是成长中的巨大困难。对于学龄儿童来说,他们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失去:用全部心力结交的朋友,给予他们全部关爱的亲人,引以为傲的学业成果等都付之东流。一个崭新的生活空间,一个迷茫的身份认同,甚至于一个不对等的教育水平,以及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倒他们幼小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学龄期儿童经历着从自我走向世界的社会化过程中,需要成人与朋友的相伴,家庭的陪伴,从而树立他们的安全感;在与学校群体的交往中,构建学龄期儿童的社会属性。一旦一个环节缺失,便会成为儿童成长道路上无法修复的创伤。如果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文本缺少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细腻情感的理解与关怀,读者便很难信服他们成长的艰辛,更无法体会到突破生存苦难的童年生命的真正力量。
再次,在表现儿童面临生存的难题与困惑时,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热衷于说教而缺乏反思。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目的,要包括带给儿童积极的行为准则和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儿童更好地成长,尤其是学龄儿童。为此,在儿童校园小说中,要不断地幻化出能够直接代替教育学龄儿童的理想化形象。这些形象抑或是通情达理的家长,抑或是亲切和蔼的老师,并能够在儿童困难之时出手相助。然而,在引导和帮助学龄儿童这一点上,儿童文学作家在面对学校教育本身时是缺乏应有的判断力。其现象在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中亦有存在。如,在《摘臭皮柑的孩子》中,把男孩青衫的母亲塑造成一位知上进、懂教育的理想母亲,然而她一边学习如何科学教育子女,却时刻把考上大学完成父母心愿作为对儿子的要求。这其中便存在一个难掩的悖论,拥有积极教育理念的家长却将“学习改变命运”的重荷当作维系亲子间代际关系,让孩子成为她梦想的延续。这显然是迎合了当下世俗意识中成人们所具有的那种惯性思维和从众思想之体现。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校园小说对学校教育,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性与巨大的责任感而言,尚有差距。诚如朱自强所言:“今天的儿童文学关注儿童现实的热情减退了,思考儿童教育本质的力量减弱了,批判儿童教育弊端的锋芒变钝了。”文学既不同于教育学,也不同于社会学或哲学,但却需要艺术的表现力,需要直面生存的难题与困惑。一旦成人作家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与思辨力,其真实性便将受到儿童读者的质疑了。
最后,在表现童年精神时,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缺乏对真实童年精神的信任与肯定。以成人式的目光关切并解决当下学龄儿童生活、成长中问题的儿童校园小说,与指向成人内心的儿童心性的文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蕴藏着成人作家通过儿童文学媒介对话儿童的心愿。然而,在面对现实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时,一些儿童校园小说作品中却缺乏对真实童年精神的信任与肯定,尤其是表现“另一种”童年中的一些儿童校园小说。这些儿童校园小说在关注这些生存于困苦中的孩子们时,没有发掘出“另一种”童年成长中的坚韧和顽强。如,在《升旗手》中,唐小鹿要被迫接受“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不方便”的成人式思维训诫,在法庭上选择爸爸。但其实,他内心更爱妈妈也更同情妈妈。面对家庭生活的裂变和成人意识的压迫,唐小鹿却毫无反驳之力。方卫平认为:“孩子被过早地投入了一种成人式的生活忧思和劳烦中,孩子自己的世界、童年自己的精神则被生活重重地遏制住了。”这种童年的精神至少包括幼小的孩童冲破残酷生活的坚韧意志,反抗冰冷现实的纯真心灵,不甘既定命运的顽强力量。然而现实的悲哀却是,当成人面对世俗的窘境时,安于现状,臣服世俗,并以过来人的姿态自诩,挟持并驯化着孩子的思维与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否定了儿童自身生命的无限可能。
四、童年精神的文化坚守
可以说,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展现了农村留守和流走于城乡间儿童生活的表征。但是,在真实地呈现这些儿童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上,还缺乏一种经得起打磨和推敲的严肃态度。如何书写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的真实?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深入地思考和探寻。
当下有些儿童文学作家认为,描写今天的孩子不必回到现场。诚然,文学高于生活本身,其艺术的创作需要建立在对描写对象所处社会生活历史与现状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其生活内在逻辑的彻底认识中。但是,缺失了对当今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生活、心理的观察和体悟,作家是很难真正地塑造出具有时代性的血肉丰满的学龄儿童形象。因此,儿童文学作家需要用客观而理性的目光、艺术而思辨的叙事,创作出体现童年精神,再现童年生存真实图景的文本,从而建立起能够沟通整个人类童年精神的文化之桥。
一是再现具有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集体记忆。尽管儿童文学作家无法真正重返当下儿童的身心状态,但是他们能够把控与儿童共存的文化空间,再现具有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集体记忆,那是“用来重建在每一个时代与社会主流思想相呼应的关于过去的意向”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些具有能指的文化符号必然能够唤起儿童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通过儿童校园小说文本在文学世界中建构起来的现实,是对时下童年文化空间进行还原的最佳途径。即当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的童年生存空间拥有了文化的张力时,才能达到文学的真实性。而这种理念应用到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形象的刻画上,便具有了日常感和真实感。
二是借助于文学情感传达童年精神的真实。对于儿童读者而言,再鲜活生动的生存环境描写也是一种镜像式的表征。而能够抵达他们心灵的却是借助于文学情感传达的童年精神的真实。这种情感的真实在儿童的内在生命中熠熠生辉:那是无论现实的生活多么艰苦,他们依然能够直面生活,用温情战胜冷漠,用欢乐化解悲伤,用智慧解读苦难的纯真童心的力量;那是《星期三的战争》中用机智和善意融入成长的男孩霍林清澈的明眸,是《安琪拉的灰烬》中苦苦漂泊在困苦里的少年弗兰基坚韧的嘴角,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经得住生活与人性拷问的霍尔顿纯善的心灵。当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校园小说在走进儿童情感世界时,需要的不再是简单地将孩子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解读为与成人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而是描摹出生活于不同地域和相同时代儿童的丰富、立体而真实的情感生活。这其中不仅蕴含着中国的儿童精神,也蕴含着儿童文学独有的审美力量。所以,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的作家,更应该借助于文学情感传达童年精神的真实。
三是以更为客观和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童年的自我与他者。这其中包括了儿童文学作家对时间横轴上的童年岁月之珍惜,亦包含了对时间纵轴上儿童生命之理解。正因为有了对童年精神的深刻领悟,恰如刘晓东所说:“成年之所以能够存在,又是对童年以自身为目的而展现自身这一过程的肯定,是对童年的生命创造,亦是对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命题的肯定。”也因此,儿童文学作家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以真正的“儿童本位”立场来对待异样生活、教育、观念左右下儿童本真的生命样式,以更加宽容、冷静与平等的方式解读现代儿童成长中的变迁。而这些方面在儿童校园小说的创作中亦有体现。如,班马在《六年级大逃亡》中,对待成长中学生之观念的尊重与认同;陈丹燕在《女中学生之死》中,理解学校之教育的犀利与理智;王安忆在《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直面校园与社会的深邃与尖锐等等。以上作品,依然是当下儿童校园小说创作需要吸纳的宝贵经验。
拥有童年精神这把打开儿童之门的钥匙,儿童文学作家才能拥有文学创作中另一种解读方式,以及面对儿童生命、面对时代更替、面对终极追问时,拥有更为宽阔的视野与理性的思辨。这也要求书写“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的作家,要以客观和严肃的态度对待童年的自我以及这些特殊的儿童群体。
四是需要儿童文学作家外向度地体察现实和内向度地挖掘自身。坚信童年精神的力量,不仅是成年人对现代儿童的成长之难的认可,也是他们对自己已经渡过的自我童年的尊重。特别是反映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生活的儿童校园小说,想要表现出这种力量,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更好地生活体察和自我挖掘。正如李学斌所指出的,“把现实中的孩子和理想中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和愿望中的孩子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家应当让现实中的儿童生活与理想化的童年真实,在文学中有效地并存。特别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童年命运的书写,不应是撕开一个儿童群体的苦痛给另一群人看的文字噱头和形式表征,而是在体察“另一种”童年的真实生活时不再加入矫揉造作的欺与瞒。并且,让这一童年特有的生命力量与审美价值成为儿童读者精神生活的向导。也就是,当儿童文学作家真实正视儿童独特的生命精神时,重拾其那份寄托于心底的理想式童年,是比教化更具有说服力的童年品格,是比引导更具有启发力的童年之思,是比启蒙更具有感染力的童年之美。
当“现实与理想”的童年进行精神交融时,能够让儿童读者跨越时空、代系与心灵的间隔,共同感受具有永恒意味的“童年真实”。而这份源自理想的童年精神,是“童年所享有的全能的爱,始终不渝地坚持用不断更新的自我理想化形式重获价值”。无论是当下的现实儿童,还是成人的童年情结,生发于童年真实之根的生命之树,正是文学能够提供给儿童与成人共同的精神之力。
五、结 语
总之,城乡变迁中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间流动儿童的生存空间,并非是距离我们遥远的银河,而是通过文学之眼与我们共享着一片童年的蓝天。一方面,“另一种”童年的书写,为儿童校园小说创作的题材和内容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儿童校园小说创作将不只是一团和气的轻喜剧和包裹着校园外衣的烂漫想象,而是对“中国式”童年群体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关照与体察。另一方面,儿童校园小说记录着“另一种”儿童的真实生活,不仅蕴含了作家对于真美善的理想与回望童年的一片安宁,还真实地记录了当下儿童个体的生存方式与成长的艰辛。
然而,如何深入到这个尚未被深刻理解和挖掘的复杂儿童世界,却依然需要儿童文学作家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由于儿童的心性所追求的,常常是向往光明的理想主义的事物,因此,任何流派的儿童文学,都应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儿童校园小说在展现更为丰沛和迥异的儿童生命经验时,需要儿童文学作家尊重学龄儿童,特别是“另一种”童年。所以,儿童文学作家在书写“另一种”童年真实生命体验的同时,要将根植于成人内心的理想化童年分享给直面苦难的儿童读者。这个承载了成人智慧的理想精神,既涵盖了当下儿童的现实又寄托着人类童年的美好期许,亦能够填补儿童生活空白,治愈儿童成长伤痕,丰满儿童思想羽翼。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