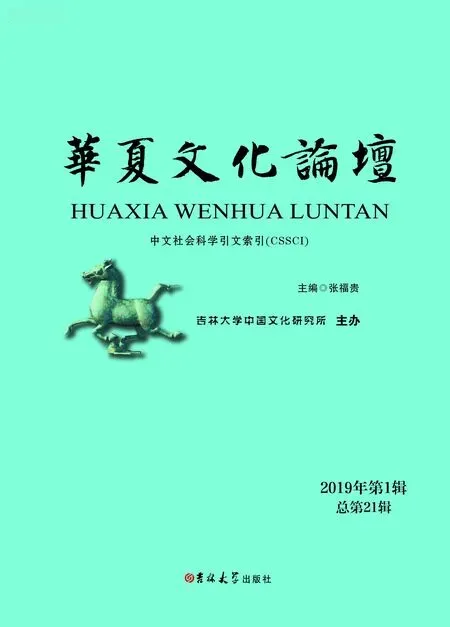苏轼游寺诗析论
赵 舒
【内容提要】苏轼作品中有大量游寺诗,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考察苏轼的佛寺活动以及对佛禅的态度。苏轼游寺目的从早年略带被动的一般游览转变为中年热衷亲近佛禅的主动游览,诗歌中对世俗因素的关注由多到少,对佛缘的论述也由浅到深。苏轼对佛教的态度是传统士大夫吸收佛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佛禅也参与了苏轼人生境界的建构,不过他终究是佛门之外的悦禅者、逃禅者。
苏轼集中有大量作品与佛禅相关,大致可以统计出来有490篇诗作与佛禅具有关系。苏轼涉及佛禅的诗作数量如此之多,让读者很难忽视。但人们在讨论苏轼与佛禅的关系时却得出迥异的结论,宋僧普济修《五灯会元》,以苏轼为黄龙派下黄龙慧南弟子东林常总之法嗣;而明代杨慎却举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中和胜相院记》等文章称苏轼诋佛。今人研究虽然多认可东坡对佛禅的接受是士大夫式的学习与受容,但更多的是从其诗文中抽取东坡与禅僧的交往、东坡使用的典故、东坡说过的崇佛语句等种种迹象证明预设观点。而另一方面,也有人通过苏轼言行中的蛛丝马迹,阐发“东坡排佛”的观点。我们则希望通过苏轼诗歌中的蛛丝马迹,寻求苏轼生平与佛禅关系之演进,而苏轼在佛寺的活动以及他对佛寺的观察正是一个较有效的切入点。
宋代佛寺通常兼具宗教场所和公共空间的功能,例如著名的东京大相国寺,在市集开放日就具备公共商业空间的作用。除此之外,宋代佛寺还容留非佛教徒居住、聚会宴饮、游览休沐等等。这些活动说明宋代佛教有相对的开放性,与世俗生活可以形成互动。这有利于佛法普及,广植福田,接引有缘人。苏轼虽然最终未曾皈依三宝,但他对佛禅态度的变化代表了大部分宋代文人的经历。我们拟通过苏轼游寺诗的文本分析,缘迹求真。
一、游寺目的由一般游览到主动亲近
寺院对于不同的人士有着不同的意味。有人愿意亲近佛禅,乐意前往寺院烧香拜佛、听经闻法;也有人因为羁旅行役,路过寺院顺便游览,或有人隐居备考借宿寺院,情况各异,其人对佛禅之态度也有差别。苏轼游寺的目的由相对被动到主动亲近。
东坡于嘉祐二年(1057年)丁母忧,归川守制。服阙与苏洵、苏辙沿江出蜀,途中遇山水名胜辄登临亲近,《寄题清溪寺》《留题峡州甘泉寺》两首诗歌就作于此时。虽然苏轼是主动游览清溪寺、甘泉寺,但长江水道的固定航线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水路舟行加速了他们旅途的枯燥烦闷,暂时离船游览需要选择合适的机会。由行船条件决定的旅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通过制科考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任。签判凤翔是东坡仕途的起点,但作为一个新科小吏他有很多公务要奔走。因行政事务到寺院居停,也是一种被动选择。例如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苏轼“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期间东坡有《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诗写道:
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乱山横翠幛,落月淡孤灯。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僧。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
冯应榴辑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云:“《一统志》:崇寿院在郿县动五十里横渠镇南”,可知此诗正是作于此次公务活动期间。东坡山行时“马上续残梦”,是一种早行状态。平时尚在酣睡的时间出门,要在马上补足睡眠,夜晚“落月淡孤灯”,常规的生活状态统统被打破。他虽然也借机游览太白山诸寺院宫观,但是顺便而来,并非专程前往。
同样在凤翔,东坡还曾因求雨到寺院投宿,此种经历恐怕也很难被说成是主动的游寺。苏轼有《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从诗题可知东坡自七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的祷雨磻溪的行踪。诗中备述道:“龛灯明灭欲三更,敧枕无人梦自惊”“夜入磻溪如入峡,照山炬火落惊猿”“横槎晚渡碧涧口,骑马夜入南山谷”。寺院在苏轼的这次公务活动中,与其说是旅行的地点,不如说是投宿的场所。虽然在此情况下,诗人也有别样的体验,但过程本身并非诗人主动选择。
苏轼在公务闲暇也不是没有主动前往寺院游览,但都透着消遣时光的意味。如其嘉祐七年(1062年)重九,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云: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重九登高怀远是旧时传统,东坡没有参与同侪集会,而是独自游普门寺。在诗中他并没有着笔于寺院,而是将笔触停留在了重九怀弟望乡的情感抒发上。有时候,东坡游寺的时机甚至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比如杭州吉祥寺的牡丹非常出众,苏轼写过《吉祥寺赏牡丹》,但他在并非牡丹花开季节的冬至也独自前往游览,并作《冬至日独游吉祥寺》云:“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此外,他还有因人际交往到寺院送行、饮酒的记录,如《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这些游览活动都可以算是公务需要之外,东坡主动前往寺院游观。其中甚至有不少苏轼与禅林人士交往的诗篇,比如《病中独游净慈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灵隠因次韵答之》《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这都是苏轼逐渐亲近三宝的痕迹。但当时文人访僧论道几乎就是一种风气,单从诗歌来看,苏轼在寺院的这些游览活动,还只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览,而非皈依性的主动亲近。
贬谪黄州以后,苏轼寄寓过定惠院僧舍。东坡在黄州写信给朋友说:“见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得便……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他不但寄寓佛寺,诵读内典,在生活和精神上都与早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还在佛寺洗浴,并作《安国寺浴》。梁银林教授释读该诗以为:
苏轼在安国寺的这番沐浴,与其说是身体之洗刷,毋宁说是精神之澡雪,心灵之洁净。他要消除的,是尘俗的妄想,是功名利禄的“羁梏”,甚至世间的荣与辱、净与秽等分别的概念,他都要将它们从自己的心里“清空”,从而成就自己的虚寂清净之心。显然,苏轼的“澡浴”是摒弃了世间烦恼的一次隆重“洗礼”,是其归诚佛僧的一个重要标志。
若以此而论,东坡黄州之后游览佛寺的诗歌出现更多思辨的色彩,多出礼敬佛法的意味。所以到后来,他写出《赠东林总长老》《题西林壁》等颇有禅意的诗歌似乎也就不稀奇了。到苏轼晚年贬谪海南后,甚至写出《入寺》这样细致书写朝拜世尊的作品。
总体上说,苏轼的游寺目的从早年略带被动到中年亲近禅僧,是受当时士大夫禅悦之风的影响。而到黄州之后,则更具逃禅的倾向。
二、游寺关注世俗因素之由多而少
寺庙本身由于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前贤遗迹等自然文化因素的组成,吸引着文化人前往观光。而士人羁旅行役、隐居备考也往往与寺庙关系紧密,这类现象早已有学者备述之,不赘。由于寺院与世俗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多多少少会在寺庙中发现世俗记忆的影子。前代人物、当时贤达在寺院中的遗迹,寺院中口耳相传的历史信息,都构成了寺院的记忆,而游览者对这些记忆的取舍往往取决于主观意志。总体上说苏轼对寺庙的世俗记忆越来越少提及。迹由心生,个中缘由也不能不推及东坡对佛禅的态度转变。
嘉祐四年(1059年)丁忧服除出川,沿途游览期间所作第一首寺院游览诗是写于峡州的《寄题清溪寺》。清溪寺是鬼谷子故宅,苏轼自注云:“在峡州,鬼谷子之故居。”这首诗说:
口舌安足恃,韩非死说难。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奸。遗书今未亡,小数不足观。秦仪固新学,见利不知患。嗟时无桓文,使彼二子颠。死败无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穷,不若愚自安。遗宫若有神,颔首然吾言。
全诗是站在咏史角度立论成篇的,从韩非、苏秦、张仪的人生际遇与鬼谷子的关系谈及人生的成败得失。阐发“巧不若愚”的个人观点,而只字未涉佛教内容。此期另一首游寺诗《留题峡州甘泉寺》,同样在“吊古悲纯孝”的基调下展开,而不言寺院本身。 “吊古”之“古”,也就是流传的历史记忆。而甘泉寺建在传为古孝子姜诗夫妇的故居,诗人自注云:“姜诗故居。”通篇在陈述行旅所见遗迹、民风,感慨其乡村生活的和美。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也曾有《和丁宝臣游甘泉寺》诗咏该寺,其作也提及甘泉寺的世俗记忆,但是有考据癖的苏轼写道:
江上孤峰蔽绿萝,县楼终日对嵯峨。丛林已废姜祠在,事迹难寻楚语讹。空余一派寒岩侧,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岂解惜清泉,蛮俗那知为胜迹。
并在“丛林已废姜祠在,事迹难寻楚语讹”句下写道:“寺有清泉一泓,俗传为姜诗泉,亦有姜诗祠。按:诗,广汉人,疑泉不在此。”苏轼游览峡州的两处寺院,关注重点都在寺院成为寺院之前的世俗记忆,而几乎没有提及僧院,以致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写于道教宫观而与佛教无涉。实际上宋代寺院因前人宅院改建的情况并不罕见,灵隐寺就是钱鏐舍宅为之,王安石也曾舍家为寺。
在凤翔时期东坡有《凤翔八观》组诗,写地方风物,类似后世所谓的八景诗。其中写到普门寺与开元寺的唐代古画、天柱寺的佛像、真兴寺的高阁。虽然画、像反映了佛教主题,但作者关注的还是王维、吴道子的画技,杨惠之塑造佛像的技巧,而在真兴寺阁的描写中,也将笔墨集中在了对修建高阁的节度使王彦超的美颂上。如其诗歌中“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王维吴道子画》)等句关注点是留在寺院的王维、吴道子遗迹。王、吴二人留给当地人的记忆是高明画家,这样一个较为贴近凡俗的印象。至于真兴寺高阁,更是写到建阁高官的写真,及修建高阁的宏伟壮观。
在游寺过程中,苏轼关注到的僧众也多与世俗因素有关。比如游终南山时,他写过《爱玉女洞中水既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诗歌对凡夫俗子热衷的契符在本该出尘脱俗的方外世界得见,表示了不解与“长吁”。苏轼游寺关注世俗因素的现象直到乌台诗案之前,都没有太多变化。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赴黄州之贬,途经光山县净居寺,为赋《游净居寺》诗。诗序中出现僧众记忆,其云:
净居寺,在光山县南四十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寺僧居仁为余言:齐天保中,僧惠思过此,见父老问其姓,曰苏氏,又得二山名。乃叹曰:“吾师告我,遇三苏则住。”遂留结庵。而父老竟无有,盖山神也。其后僧智顗见思于此山而得法焉,则世所谓思大和尚智者大师是也。唐神龙中,道岸禅师始建寺于其地,广明庚子之乱,寺废于兵火,至乾兴中乃复,而赐名曰梵天云。
这段序文中详细记录了寺僧居仁向苏轼讲述他记忆中的寺院历史,其中不乏神化的痕迹。苏轼这首诗借自己游览山林的体会,抒发险些落入红尘网罗之中,感喟“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刑名非夙学,陷穽损积威”的窘境,以及脱离危机后的隐居意愿。诗中较此前写俗世记忆的作品最大不同在于 “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等句用到了佛家典故。而至此以还,苏轼人生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黄州时期,他由积极事功转而韬光养晦。在这个阶段他开始了洗心向佛的人生新阶段,苏轼戒杀、施舍、祈祷等佛教行事也多发生在黄州贬谪之后。此后苏轼游寺诗即便写到世俗事典,或凡俗记忆也多半与佛家人事有所牵连。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守杭州曾作《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诗。诗题长而确,记述了苏轼到龙井辩才所居处,探望辩才大和尚,双方以虎溪三笑的典故互相戏谑的事。
晚年苏轼再贬岭海,过虔州天竺寺,寺中有白香山遗迹,而诗人回忆起他童年时曾从苏洵处得来的记忆,道: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诗。
诗歌所写的人物皆非佛门僧众,但苏轼此时已经号为“东坡居士”有年,所道乐天遗迹也是虔州当地的佛门文物,东坡的记忆虽然是俗世记忆,却与佛门密不可分。
约言之,苏轼写寺庙时的关注重点,从着力于世俗记忆到关注佛家相关内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苏轼内心对佛禅态度转变的一种体现。人们诗歌书写的内容往往是其内心关注的外在表现。论者每每举出苏轼用佛家典故说明他在青年时期对佛教的向往,似乎未达一间。内典是北宋士人能接触到的书籍,他们学习佛教经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学以致用,在诗歌中用佛典同样正常不过。而书写诗篇时关注的因素、注意的历史记忆,以世俗还是佛禅为重点,实在是与其对佛教关注度分不开的。从这一点上说,苏轼对佛家的态度有一个由起初的甚不关心,到后来的放在心头的转变过程。
三、游寺诗议论佛缘之由浅到深
苏轼游览寺院由早年较多关注世俗,到渐渐与高僧大德交往,礼敬三宝。虽然他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家弟子,但其游寺诗中发出的议论、抒写的情感却由早年不涉佛禅,到后来体现禅悦风习,发生了佛缘由浅及深的转变。
譬如前文所举苏轼早年出川,所作《寄题清溪寺》《留题峡州甘泉寺》,其诗歌结构是前数句或叙述典故,或说景致,而结尾抒发议论,前者抒发福祸相依的感喟,后首总结乡村之乐的缘由是孝子之遗风,所发议论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显然谈不上佛缘。此种情况在苏轼早期诗歌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他在凤翔期间,以公务奔走地方,投宿寺院。整日辛劳奔走,诗人发出了“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僧”(《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的牢骚语,其中透露出误入牢笼里的悲哀。有些诗歌中甚至表现出浓浓的乡思,如 “门前商贾负椒荈,山后咫尺连巴蜀。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诗人见到寺院山门背着老家特产辣椒等物的商人,立即联想起山后不远就是故乡的土地,遂生发出归耕垄亩的念头。
此时,即使是闲暇游寺,东坡抒发的情感也似乎与佛门相去甚远。比如他游终南山,作《仙游潭五首》,其中的《南寺》《北寺》与其他各首合观,就是按游程叙述的。《南寺》称自己一行人“东去愁攀石,西来怯渡桥”,“野馈惭微薄,村沽慰寂寥”。到了《北寺》更是“畏虎关门早,无村得米迟。山泉自入瓮,野桂不胜炊”,饥肠辘辘的诗人自我调笑道:“信美那能久,应先学忍饥”。此处抒发着野游的喜乐,在野馔和村酒中体味旅行的非日常化生活。所谓的“忍饥”之类的议论,纯粹是旅行感受,其中根本没有涉及佛禅的义理。
早年这类较为表面化、浅层次的议论,到年岁稍长,阅历转多之后,略有改观。熙宁四年(1071年),三十四岁的东坡通守杭州,赴任途次于润州作《游金山寺》诗,从“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写起,直接说到家乡所在与千里宦游的状态,奠定了全诗基调。随后“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四句写登临所见与羁旅行愁的状态,又用僧人留客启发下文观赏落日的景观描摹,最后却将情感落在“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的想象与议论之中。全诗叙写的依然是宦游羁愁与欲归隐而不得的无力感,当然,这种感慨对于三十四岁的诗人而言似乎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嫌疑,但其抒发的情感较早年即事议论的疏浅已经有了深化。相较于早年苏轼游寺诗中僧人形象较少出现的现象,至杭州任上,苏轼与杭州高僧大德的交往呈现紧密趋势,显露出禅悦迹象。
东坡在与禅僧长期交往的过程中,显然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到守密州时,他的游寺诗就体现出一定的禅意。例如《光禄庵二首》其二有云:
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觅光禄,雪中履迹镜中真。
诗中体现出人生无常、世界虚幻的意味。而到贬谪黄州以后,苏轼诗歌中的佛禅意味也就更加浓郁。最出名的当属《题西林壁》诗,该诗传唱千古,经久不息,不过清人纪晓岚以为:“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尚不取厌,以为高唱则未然。”虽然持论过苛,然敏锐地嗅出诗中所带的佛禅意味。当然,此前施元之注该诗也曾引用《华严经》:“于一尘中大小刹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各转法轮。”到了黄州之后,苏轼的整个人生境界与前期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人生态度有了相当转变,而其中佛缘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有学者曾撰文指出东坡早年所作《维摩诘像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之“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二句“对于维摩经中讲述的自身虚幻不实的空观思想的理解是颇为准确的,但对于取消一切差别的不二法门的义理,则似乎还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因典故运用去考察苏轼的佛缘,是观察苏轼与佛禅关系的一个角度,而本文所作的是因迹求源,同样不难发现东坡生平由不亲近佛禅到渐受禅悦之风影响,最终洗心向佛。这种讨论提供了打量苏轼的另一个向度,我们认为东坡的确与佛禅关系日深。不过,将其列在某位大德门下,过度强调佛教信仰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却未必合适。苏轼对佛教的态度是传统士大夫吸收佛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他经过生活洗礼,对佛教由淡漠到接受,不过他终究是佛门之外的悦禅者、逃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