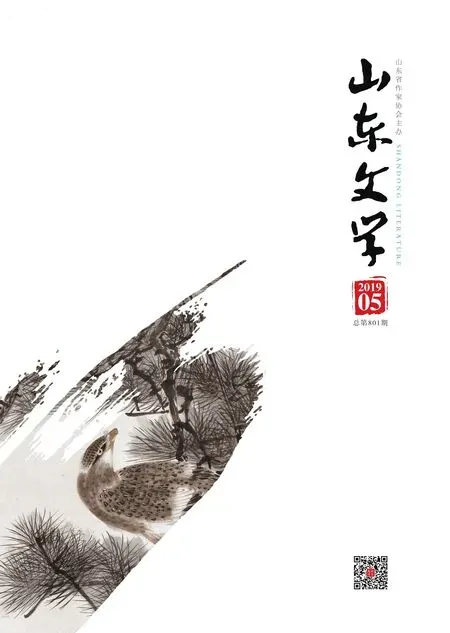旧光焰
张 毅
有一天在梦中,我沿着熟悉的街道往前走。我越过几个车站和商店,希望找到路边那个绿色邮筒。我想给记忆中的故乡发一封信,人们告诉我,你的故乡已经消失。是的,现在,我们的故乡只有梦中才能见到。而随着时间流逝,那些梦中的旧地址就像一张年画,在微暗光焰中愈加清晰。
高密那个乡村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地址。那是一个安静的乡村,胶济铁路从村后经过,一条河响在记忆深处。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黑夜和寒冷。黑夜降临前,村庄上空飘着一层薄雾,农人赶着牛,扛着农具,说着去年的玉米、今年的麦子。喊牛的声音、找孩子的声音、农具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地缭绕在村庄四周。这样的夜晚,我们常隐身于草垛之间,藏猫猫像一个寓言,使人生极具游戏的隐喻。我们藏在草垛的阴影里,忐忑地等待伙伴的手从背后伸来,心里既惶恐又惊喜,但伸向我们的往往不是伙伴的手,而是乡村孩子的命运。那些村庄的孩子在贫困封闭的状态下,送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这样的乡村小学读书结果可想而知,既是时间的荒废,更是对知识的误读。我很多错别字都是小学老师教的,他们照着葫芦画瓢,大胆向我们传授了很多错别字,他们的知识极其贫乏。后来,每次读错别字我就想起那些小学老师。我愿意原谅他们,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谁会为一个字的对错负责呢?
记忆被一场场大雪笼罩着。雪落在肃穆的树枝上,落在高高堆起的草垛上,落在故乡开阔的平原上。北风从村后的高坡鱼贯而来,发出“呜呜”的鸣叫,河流冰冻的声音从地表传来。读高中时,我每天顶着寒风,用棉帽蒙住脸,步行10里去县城求学。雪野里,我像一片雪花随风飘荡。冬天过去,暖风频吹,屋顶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一串串钟乳石一样的冰凌在暖风吹拂下,发出隐隐的爆裂声。能够看出冰凌日渐缩短,冰水从冰凌尖上落下,在地上溅出一个个小土窝。夜里偶尔传来冰凌的坠落声,让人梦里多了几分凉意。白天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串冰凌在屋檐下摇摇欲坠,好像不会坠落,就在我转身之际,身后突然响起一阵破碎声。
我在那个村子看见生命中第一场雨和雪,听到亲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知道了黑夜与白昼的关系,懂得了四季轮回的规律。现在,村庄已经被一片厂房覆盖。每当火车路过那个地方,我的眼睛常常一片潮湿。
随着时间的改变,我生活的地址也在不断变化。从那个乡村搬到高密火车站没几年,我又搬来青岛。记得来青岛之前,父亲阴着脸说:上那地方干什么、人生地不熟的?在海边生活的愿望,让我一路风尘来到这里,也算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车站。城市生涯是从住在一间半地下室开始的。青岛老区有许多这样的日式建筑,砖木结构。我住的这栋建筑没有门牌号,因为条件太差,朋友问起住处时,我总是语焉不详。我说,啊,那地方就是大连路和黄台路交界的一个胡同,进了胡同往左拐,再往右拐……拐来拐去连我自己也糊涂了。那个地方拥挤、阴暗、潮湿,八平米的空间把人的感情压成平面,四季轮回将生命构画出底色不同的画面,而黑色是最原始的一张。那种真实我决不会忘记,犹如进入没有出口的迷宫,争夺生存空间在那时留下深深的痕迹。房间里白天见不到阳光,却有一些昆虫活动其间,蟑螂就是这里的常客。白天的时候,蟑螂们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夜里只要一开灯,就可以看到地上、桌上大大小小的蟑螂四处乱窜。我家碗碟每天吃饭前都要再冲洗一遍,因为这些碗碟经常会有蟑螂的痕迹。一个夜里,儿子突然被什么惊醒,我听到他在床上大声叫喊。我赶紧起来开灯,发现儿子枕头上有一只蟑螂,正瞪着眼睛和我对峙,我赶紧举起身边的苍蝇拍,这时蟑螂迅速跑到枕头下面,我翻开枕头,蟑螂又迅速跑到床下。我拿起手电筒,翻身跳到床下,蟑螂继续用挑衅的眼睛看着我。我再次用苍蝇拍扑打过去,蟑螂却消失了。我翻开家里的旧家具、纸箱、暖水壶,这时我才发现,目光所到之处都有许多蟑螂用挑衅的眼睛看着我。我决定彻底消灭这些蟑螂。我到商店买来蟑螂药,放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但很快发现,蟑螂们丝毫不见减少,甚至还有增多的趋势。动物专家讲过,当一些动物被杀时,这些动物会释放一种信息给同类,让同类避免被杀死。不知道那些被杀死的蟑螂是否也给同类释放了这种信息?后来,我使用了另一种灭蟑螂方法,在报纸上涂了一层蟑螂胶,这种胶有一种吸引蟑螂的成分。第二天把报纸掀开,发现上面粘了一层蟑螂,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在挣扎。两周后,蟑螂逐渐减少。但一个月后,我看见顶棚有几个黑点在移动,我抬头去看的时候,黑点很快消失了。我知道蟑螂们又出现了,我和蟑螂的斗争直到搬离那个地方才结束。
我住过的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八号码头。那里是一道风的走廊,我把那里称作“北海道。”八号码头是后来修建的,进入港区后沿波光粼粼的海岸线往北走,越过几个泊着货轮的泊位,一直走到一片长满荒草的地方,那里就是8号码头。8号码头有几个深水泊位,可同时停靠多艘5万吨级船舶。那些年,八号码头业务繁忙,海面常泊着装满集装箱的货轮,货轮巨大的钢柱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来自各国的船员常从高高的舷梯上走下,沿海边的水泥路走出港务局。这里有一条铁路专运线,是为进出港货物运输修筑的,同时还修建了一些铁路工房。我住的那处工房位于八号码头北面,那里位置偏僻,周围杂草丛生,除去正在作业的港区工人和运输货物的汽车,偶尔会有拾荒者流落至此。我每天朝九晚五的往返于“北海道”和单位之间,看惯了早晨海边的景色,听惯了夜晚海上的涛声。工房西南方向有一道海岬,像一艘军舰插入蓝色海湾,远处胶州湾的夕阳揉碎万点微光。夜里,除去港区孤零零的灯光外,周围一片黑暗。有夜航飞机从天空掠过,两朵翼灯星星一样忽闪着移动,虚幻而飘逸,翼灯很快就不见了,半晌,空中传来隐隐的轰鸣声。几根强烈的光柱交叉着从夜空扫过,那是军港值班官兵在巡视海空。一阵汽笛从海面传来,那是一艘正在靠港的货轮。夏天的时候,阳光下会看见戴草帽的钓鱼人在岸边竖几支鱼竿,气定神闲地等鱼上钩。我能根据雾中的笛声判断这是一艘正在靠港的船以及它的吨位,也能通过笛声判断这是一艘即将出发的船。我能听出附近路过汽车的载重量,那些慢慢驶过且发出“轰隆”声的,是满载煤炭或矿石的运输车。到了冬天,北风裹着胶州湾的寒气迎面扑来,冷风刺骨,大风刮得人左右摇晃,我只能佝着身子往前走,稍有不慎就会被风刮到海里去。那时,我每天带着上学的儿子,骑着自行车穿过港区的水泥路,先把儿子送到学校,再去位于前海的单位上班。码头散落着许多大型起重设备,货场经常堆满海外运来的红色矿石和大堆煤炭,阵风吹来,煤灰和矿石粉末满天飞舞。水泥路上常有一层黑乎乎的煤灰,或是红色的矿石粉末。每次从水泥路上经过,我都努力加快速度,让自行车迅速穿过空中弥漫的灰尘。
一年夏天,我从单位回家途中遇上一场暴雨。那个下午,灰色的云层在天空聚积着,一群雨信鸟尖叫着从空中掠过,翅膀扇动的声音异常清楚。天空像有千军万马在集结,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扑过来。一道闪电划开雨幕,很久才响起沉闷的雷声,一时间,天地间仿佛有一千匹野马掠过。那是一场罕见的风暴,闪电在天空炸裂,向四处放射出蓝色的光焰。我听到风在耳边“呼呼”响着,风力逐渐加大,海边的树像跳大神一样左右摇摆,树干一棵棵无声折断了,海上涌起黑绿色的波浪,很快,暴雨垂直落下。暴雨持续下了一个小时,随后天空布满了飞逝而过的云彩,我住的工房前后一片洪水。回到家时看见屋里黑乎乎的,暴雨造成了大面积停电。雨水正从满溢的檐槽滴落,风从屋檐下和玻璃裂缝处飕飕地灌进来。碎石路上铺满被风吹倒的树木,附近的工房都断了电,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外面,谈论着这场暴雨带来的结局。然后人们开始向远处走去,那里有一个小商店,只是那个一向灯火通明的商店现在一团漆黑。我这才想到大家是去买蜡烛,但是,这段时间商店恰好没有蜡烛。人们用同病相怜的眼神互相安慰着,各自回到自己屋里,在黑夜中安静地等待着。半夜的时候突然来电了,工房所有窗口都在这一刻亮了。外面传来夸张而急切的说话声,人们互相通报着:来电了,来电了。好像大家刚刚经历了一次灾难,而现在则是一个光明的节日。
离开8号码头前,我独自一人在岸边看落日。那是个秋天的傍晚,风呼呼吹着,我看见水泥路上有一个人影。那个影子越来越大,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个和我一样的父亲,他正骑着自行车走在我经过的路上,身后也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因为风大,自行车被吹得歪歪扭扭,他躬着身体使劲儿往前推着。风像考验我一样正在考验着这个年轻的父亲。我的经历,正在被这个年轻父亲复制着。一样的烈日炎炎,一样的暴雨如注,一样的似水流年。
时间快得让人揪心。记得刚来那阵,望着从老家带来的坛坛罐罐,心里不觉怅然。父母一直在高密老家,我每周都回去看望他们。那时,冬天的每个早晨,母亲都要在院子里生炉子。母亲用旧报纸引燃木柴,将蜂窝煤放上去,一股黑烟从烟囱升起,母亲一边大声咳嗽,一边用破扇子对着炉门哗哗扇动着。这时,火焰从蜂窝煤上蹿起,母亲的咳嗽渐渐平息了。前几年,我给老人买了一套新房子,新房收拾好后我让母亲去看了,准备来年春天搬家。就在这时母亲突然病倒了,不久母亲去世了。母亲像一片落叶融进土里,眨眼就不见了。老人去世后,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从此,我的根也就没了。
想起每次搬家都要扔掉一些杂物,有几件东西一直跟随着我:一只祖传木钟和母亲用过的“凤凰”牌缝纫机。木钟已经停了,指针永远指在一个位置。小时候最喜欢给木钟上弦。我翘着脚把木钟从桌子上搬下来,轻轻敞开那扇带玻璃的小木门,取出里面的铜钥匙。铜钥匙在手心里凉凉的,我用它对准弦孔,用手轻轻一扭,表盘里发出咯吱吱、咯吱吱的金属声。直到扭不动了,我知道弦已经上满了。咔咔,咔咔,我听到指针在走动。现在木钟停了,但是我们家还有一个指针在运行,那就是我。在人生的时空里,我是一个不断跑动的指针。
其实一直想停下来,像那只老旧的木钟。搬到东部后,还是不能确定这会否是自己最后的家。望着不断变化的家具,心里一阵茫然。世事更迭,亲人离去,如一股秋风吹皱往事。回想自己迁徙的经历时,我总是把窗帘垂下,让声音静下来。
那一刻,有种东西像一把刀子从心中划过,带着灼人的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