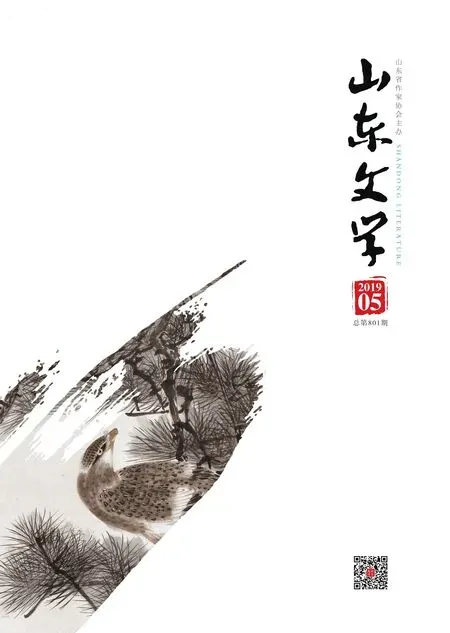生长颤抖
微 紫
我七十年代的童年,是能吃饱的,主粮是地瓜面、玉米面,麦面馒头只能在过年时吃两天。
读书的动力,是改变命运。土地之上的四季劳作,不啻于终年残酷劳役。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知道,乡间劳作无田园情趣可言,被锁在土地上刨食得以生存的时日,与监牢里的服刑并无不同。虽然不是监狱形式的高墙大院,然而户籍制约,工资与获得方式,已经是一种无形而终身的宣判。
上学是唯一的希望。要用书桌前的博弈,博出不同于父辈的命运。但是这种几率是有限的,只限于天分聪明而勤苦的极少数。大部分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路纷纷落马。小学老师自己也只是小学毕业。他从来不笑,对待愚钝的学生和惹事生非的学生只有巴掌。他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一个民办老师,紧捆在他困窘的生活里,心中没有空隙容纳对学生的耐性。他将锄头竖在教室门口,教室没有门,只是一个门洞,上完课就带上几个孩子一起去他农田里干活,被选中的孩子非常得意。在乡村,有几个孩子能坚持读到初中,以至高中再考上大学呢。他们大部分一出征就纷纷弃盔道旁,放下书包,拿起镰刀,早早跟父母上山干活了。越早越好,祖宗三辈都吃土坎垃活着,父母们不相信祖坟上能冒出青烟。迟早要下学干活,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认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账就行了。上多了也没用。所以,上完小学,陪伴我一起读初中的同学就了了无几了。
父亲心里和手里都有一个无形的鞭子,打着他自己,也打着我和弟弟。长年的辛劳是一本最活色生香最有实证力的教育课。他带着我们在大太阳下的山野里干活,顶着烈火,流着冒不完的汗水。肩上拴着绳子跟他一起拉车,弓着抬不起的腰,牛马一样。父亲说,不上学,就永远这样,不是一天,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星空,有时我们也谈论它。夏夜躺在屋顶上乘凉,父亲将他中学水准的物理学知识全部兜售给我们。认识几颗常见的星,比如牛郎织女星、北斗星、北极星(模糊不辨,不知我理解的那颗是否是父亲指认的那颗),也找出了银河所在。知道这宇宙浩瀚无边,我的想象力在它的边缘处被穷尽并坍塌。星空凛然遥远,除了展示着朦胧的美学启迪,并不如这片屋顶和下面的大地给我们的感觉来得更实际。除了地上,人们还喜欢在屋顶上活动,比如晾晒庄稼,纳凉,缝被子,甚至端着饭碗爬到屋顶上吃饭。有人丢了东西在屋顶上叫喊,指桑骂槐。夏天屋里太热,有的人睡在屋顶上,醒来时东西莫辨,从屋顶上掉下去会将腿摔折。村庄里没有楼,有人遇到心结,选择去跳屋顶。屋顶不过三四米高,跳下来不足以死人,摔残摔伤倒是极有可能的,这就是长期的苦刑了。
当然,在农村,真想死的人不是跳屋顶,而是跳井、喝农药、上吊。这在乡间是常有的事情。
读书,考学是那么重要。唯有这条路,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阶层。而居于社会的哪个阶层,直接关系我们的生存姿态。是继续卑微,还是扬眉吐气,一吐后快。
父亲时常凝重低郁的神色,会让我感到自己的快乐是一种罪过。我想只有当他看到我们终于将捆在身上的生存之锁解开,将铁链扔下,终于自由抽身离开的时候,才能解开他长年锁着的神情吧。而我,就是父亲的解锁人,我甚至就是父亲的解放者啊。父亲在等待我的解放与解救。我有一种急迫感、压力感。所以我平时拼命努力,但在每次考试时又患得患失,乍喜乍忧。
我可以谴责父亲不超脱,没有古代文人那种超脱生存世俗,放身物外的境界吗?我可以要求父亲应该有那种处困局而豁达的姿态吗?我是否可以这样要求父亲的做人境界呢?我能设身处地吗?
我忽然痛恨自己一回忆童年,就要写到物质困局,怎样拮据,于是心灵怎样被囚禁。仅仅因为那些困乏,就让生命失色,就损伤了从容与骄傲,就麻木了对光线的感受。但是我不能不继续回忆,是那些烙在我记忆上的印迹,成为了我心灵的底色。
没有新衣服穿,一件小花褂穿了几年了。开始母亲是按大号做的,但是我长了,它小了。又小又短,袖子短成汗衫,布料也酥脆了,洗的时候不敢用力搓。鞋的大脚趾处漏了洞,走每一步都带着羞耻感。就日日带着这种羞耻感在学校,在同学之间。诸种羞耻感一直伴随过了童年少年,而成为性格的一种定格。如果从来不曾感到这些,或者感到过但漠视那些羞耻,是怎样一种成长呢?与现在我的性格会有迥然差异吧?
一个女孩被崭新时尚的衣服打扮起来,像花朵一样美,像公主一样高贵,受人敬仰与喜爱。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一个梦境。因此,我特别喜欢看画报上女孩的样子,都是衣服特漂亮特好看的城里女孩,天生尊贵,而我小时候是个多么寒酸的小女孩。我从小不愿意把这样的自己拿到别人面前去。但是这种想法埋在我心里,从来不说给父母,增加他们的烦忧。
在那张小学毕业时我与几个小伙伴的合影上,烙着关于这种感受的永久记忆:照片中的我,穿的正是那件短了足有三寸的淡紫菊花小花褂,布料脆弱稀薄,袖子短到肘部,既不是正常的褂子,也不是正常的短袖。照相馆里提供有一个道具,一束塑料花。我抢先将那束花拿在手里,两手端在胸前,铺展开的花冠部分刚好遮盖住我的袖口,使人看不出它到底有多短。我的两个小伙伴站在我的两边。我们脸上的笑都是又拘谨又兴奋。那是我一生的第二次照片。第一次,是遥远的周岁照了。那两个伙伴,照相的次数也不会怎么多。照相前,在家里我对着镜子练习过照片里需要摆出的微笑。她们估计也是。我们平时都不是照片上那样笑的。我的十一岁以一种掩饰过的烂漫愉悦留在那张黑白照上。
接父亲下学的那个早上,阳光很灿烂。金黄色的光从东方穿透树木射过来,耀眼但温煦。记住这个早晨这束光,是因为在这束光里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那是一年级的第一次考试,也是今生第一次,6岁,考汉语拼音,得了43分。我的学前知识教育一片空白,心理状态极其懵懂,无知到不懂43这个数字如何读,不懂得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参加了考试,知道这个分数不好看,被老师罚站在了讲台上,回到家被母亲大声训斥。而父亲是否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感到了他强烈的失望。母亲的失望是大声斥责,巴掌拍在屁股上。父亲的失望是无声的,他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说,也不看你。他的心里,似乎收回了前六年对你全部的温和,也收回了他对你寄予的全部希望。似乎这今生第一次考试向他宣证了,这是一个不会有出息的孩子。
第二天早饭时,晨光映照着村子,房屋、树木都是金色光亮的,我像往常一样领着弟弟去父亲放学的路上迎接他。在那片开满白花的绿油油的土豆地旁,我们会迎到父亲。他会与一群学生一起披着晨光走来,走在下早学的路上。在这片土豆地旁,父亲微笑着走到我们身边,抱起弟弟,一手领起我,走回家,去迎接母亲摆在院中小圆桌上简单而喜悦的饭食。每天都是如此,像迎接每天的晨光一样如约迎接父亲渐近的笑脸。
但是这一次,父亲脸上无丝毫笑意。他走到身边,抱起弟弟,看也没看我,径自撇下我在后边,一个人向前走去了。温暖的晨光倾刻从我身上散尽了,父亲的温情也撤退得如此彻底。此后的图景模糊。只知道自己一下子是那么自知了,不再敢无所顾忌地向父亲索要喜爱。这一切,源于43分带给父亲的巨大失望。沉默,不去搅动热闹,像一下子长大了,也像变成了另一个孩子。每天放学回来,傻乎乎地写字。甚至不懂得为什么要写,只是傻傻地抄书,憨憨地写。看到一行行字在纸面上整齐地排布上去,渐渐有了一种莫大的喜悦。它们那么好看,是我创造的。下午放学回来,直写到天色昏暗,日暮的翅膀覆盖住纸面,仍然意犹未尽。每天以这种行为取得母亲的表扬。而父亲仍是不冷不热,没有笑脸。
一直到第二次考试,我惴惴地将85分的成绩放在父亲面前。这个数字,我仍不小心会读作58,而且完全不懂得85与58到底有何不同,有什么差距,只知道它终于缓解了父亲的脸颜。但是从此,我不再有晨光中拉着弟弟迎接父亲的后续记忆。它可能的确至此终止了。这件事的确给了我教训。此后,我一直是努力的,我懂得,换取父亲的温暖与笑颜,唯有以学习的努力。
人世有欺凌,也是从上学之初开始体会到的。上一年级时我刚满六岁。农村孩子上学晚,同班孩子大都在八岁之上,十一二岁亦有。我坐在水泥台子课桌的第一排,最边角。和我同桌的是一个王姓男孩。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不是出于恨,而是实在早年记忆镌刻太深的缘故。不知为何,他对我种种为难,以欺压我为乐。他占据水泥台桌的大部分,将我挤在边上,划线,而我一旦不小心越过,就打我。班里王姓孩子很多,都是一个宗族的,他们彼此以为亲。我有一次不由自主对王姓男孩做出了一下反击,他便觉得自己受了大屈,哭起来,所有王姓男孩女孩一起上来骂我,推打我,还叫来了男孩三年级的姐姐,告诉她说我欺负了她的弟弟。她大骂我,并指挥弟弟打还给我。所有王姓孩子都站在旁边看热闹,并帮腔骂我。而我在惊慌害怕的同时,内心最大的反应是惊异与疑惑:他们何以这样对我?他们为什么这样?这种从我稚嫩心田里产生的对人性的最初疑问,竟然比所有的数学题难解。而我当时不知道哭,更不会辩解,只是呆呆地承受。这种情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哭,再也不想上学,父母才有机会了解到这件事,找老师处理。老师为我调了位置,情况才得到制止。但是我刚入学时的那种自由烂漫的意态大受损伤,对自己与同学的相处再无信心。周围的世界变得让我感到不安,生出本能的小心自护。虽然后来因为成绩不错,较受老师肯定,在班级不至沦落到被嫌弃和嗤笑的地位,但因为胆小羞怯,也因为年龄一直最小,从心理,从经验能力,都处于弱势,在班级里从来都是边缘人的角色。
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爱上了阅读。契机是父亲给我借的几本刊物带来的。
那几种刊物是《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民间文学》。书中忽然洞开的世界所带来的新奇与迷恋感,是教科书从未带来过的。课本天生是一种枷锁,而课外书是一种自由。
我自沉浸进去,就没再舍弃这种爱好。只是书籍太少,刊物更新也慢,每个月我都在盼着,每天都在问父亲:刊物到了没有?父亲将到达的刊物先带回家来给我看,我看完后他再带回学校还给学生。
每次还刊物时我都不舍,因为送走它们,就意味着接下来一个月我又无书可读了。有时我会央求父亲将它们留几天,再读一遍。
我清晰地记得那种无书可读的饥渴感。它不来自胃,而是来自心。无书可读的日子,心像一片缺水的田,有干裂冒烟的痛感。凡见小伙伴有小人书,我必厚着脸皮上前去借。凡走亲戚串门,进门也必先搜寻家里是否有书籍报刊。然而乡村终归是书籍的沙漠,大部分时光还是无书可读。
父亲说,他上高中时曾经存了几箱课外书,文革时,全部烧掉了。这话引起我心中一阵深深的痛惜。父亲忽然想起什么,说:你爷爷窗台上有本书呢,去看看还在吗?
我到了爷爷的屋子,看到他窗台上有本砖头样的发黄发暗的书,没了封皮,上面搁着他的老花眼镜。这块书砖头是爷爷专门搁眼镜的。我拿走了书,爷爷只能将眼镜直接放在土砖窗台上了。
这本缺损且发黄的书,有四五厘米厚。我先后看了五遍,最后几乎能背下来了。书的名字叫《欧阳海之歌》。这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慰籍了我对文字的巨大渴意。这本书是我少年时代,家里唯一的文化遗产。长大后,我才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部书一出版就得到辉煌的待遇,它因血液鲜红而得安全终老到发黄发烂。被父亲烧掉的那些书,都没有这样的命运,我也无福在少年时代读到它们。
每天下午六点半,收音机里,中央儿童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讲故事”极大地告慰了我无书可读的饥渴。
父亲曾有个小收音机,坏掉后无钱买新的,父亲就买了半导体零件,亲手制作了一个。父亲能教中学各门功课,对于物理学尤为熟谙。他竟然用蓝漆木板作壳,用母亲的紫碎花布作音箱,为我制造了一个收音机。我抱着它,听了很多年。
下午六点半,母亲还在田里劳动,屋门是锁着的。我放学回家,无法进屋听收音机。于是,我将自己变成一条鳗鱼。
我们的屋门下部有一道木栅。我把栅门拿开,地面与门之间的空隙有十厘米,能容我爬进去。我趴在地上,将身子紧贴住地面,头偏着,腮贴着地面,先进头,再伸臂,双手趴在地上,慢慢往门里收缩身子。就这样慢慢爬行到屋里,起身,顾不得拍去满身满脸的灰尘,打开蓝漆收音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节目频道。“嘀嘀嗒嘀嘀嗒”的序曲音乐刚刚结束,故事正要开始,我长舒一口气,坐下来,愉悦地沉浸于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中去,忘记屋内光线昏暗,忘记外面门上还有把锁,忘记屋外夜幕正缓缓降临。
三年级时,作文课成了我生活里最兴奋最期待的时光。因为每次上课,老师必读我的作文。虽然一向严厉的他从来不惯于用言辞直接表扬学生,但是宣读本身已经使我得到极大的满足。那些苦于在作文课上写出一个字的同学,纷纷用艳羡的眼光看着我。而我也在每次写作的过程中尽享创造与编织语言之乐。有一次丢了钢笔,我不敢告诉母亲,就以替同桌小芹写作文,换取她的钢笔用,使用了很长时间。
我告诉父亲,将来我要做写作文的人。父亲笑了,说,那叫作家。又说,当作家很危险。为什么危险?我极其纳闷。写错了要被批斗,父亲说。我仍是懵然。父亲的态度似乎又有点含糊,没有执意否决我的意思。之后,他倒是更加殷勤地为我借书,在他所遇不多的机会里,将能借的书为我带回家来。
后来,父亲打算为我订一本刊物。这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家里没钱,父亲还是决定鼎力而为。于是母亲去借。我们在家里等待。
黄昏,母亲回来了。她的脸上带着忧愁与凄惶。钱倒是借来了,十几块钱,是借了好几家才凑齐的。
“孩子呀,你知道借钱多难吗?一定要好好读书!”母亲说。
那个黄昏,我的心里暮蔼一般沉重。
一个霞光满天的黄昏,夕光把绿油油的麦田融成金子。我与伙伴们在田野里割草。
她们不曾读过课本之外的书,也不曾听过小喇叭故事。而我听到的那些故事,装在心里,每天都在身上激荡。我极想把那美妙的另一世界分享给她们,分享给没有听过与看过的人们。
于是,我给伙伴们讲起了故事。她们停了手里的镰刀,瞪大眼睛,专注地看着我。我脑海里回荡着那些听过读过的故事,故事的人物和情节激荡着我,我用我所能达到的声色情态极力模拟着它们,表现着它们。激情在我的身体里与声音里燃烧。
低头的时候,看到自己方格子鞋尖上的破洞,就把脚往草丛里藏了藏。西天边,霞光正烈。它们的光辉如此璀璨,那儿仿佛正是人们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