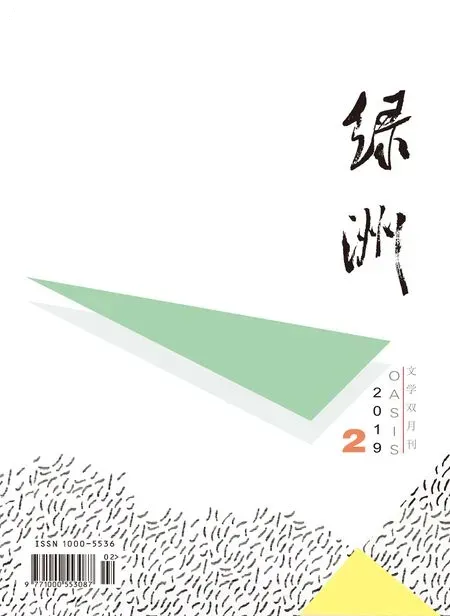西厢记
卢一萍
一
恋爱过的人都知道,她那一眼有多要命。
这是最后一班地铁。车上的人不多。晚归的人大多一脸倦意。一些人合眼假寐,其他人几乎都在看自己的手机。而我的手机刚好没电,只好无聊地坐着。我就看人。我是回过头去看人时看到她的。我看她时遇到了她那要命的眼眸。
她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我不知道她是多久站在那里的。她云髻高耸,面部化妆纤白明媚,额饰梅花花钿,面靥斜红,项戴璎珞,腰垂红色腰带,饰有香囊,穿着齐胸襦裙,酥胸半掩,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脚穿凤头翘头履,完美地托起石榴色曳地长裙,手腕上戴着玉镯,手里看似随意地拿着一支玫瑰。她手里没有手机,耳朵里没有耳塞,她的样子过于古典,与周围的一切都不搭调。我想她或许是个演员,太晚了,没有卸妆就往家里走;或者是那种唐装秀——文殊坊一带经常有穿汉服、着唐装的女子出没。
我忍不住想再看她。没想她也在看我,还朝我微微一笑。好像认识我似的。她的微笑多么迷人啊。我不由在心里赞叹。我也报以微笑,然后羞涩地移开目光,心里不禁有些伤感地想到,她也不过是我偶遇的无数让我心动的女子而已,一世一面,无缘再见,不知其姓名、年龄、住处、故乡,不知她是干什么的,更不知她人生的故事。这就是人生的无奈。我低下头,不知为何,眼睛潮湿。我记得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车门开了,几个人下了车,几个人上了车。我仍没有抬头,但我希望她没有下车。我希望她还在这列地铁上,希望她在我的不远处多停留一会儿。有人坐在了我身边。我没有去看。有无数人在我身边坐过,很多人没有必要去看。但我看到了那唐朝的履、唐朝的裙裾,闻到了一阵清爽的气息,微微有一种花的香味,是几种花香混合而成的香气,沁人心脾。我侧眼看去,发现端坐一侧的正是她。她的身体坐得很直,腿和脚是并拢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而她的骨子里也的确散发着这种气质。我也不由得端正了身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把她弥散在空气中的气息全部吸纳到我的肺腑里。我有些沉迷。每一秒长似百年,挨着她的半边身体因为紧张,没了知觉。我想和她说话。但心里涌出了万千言语,却说不出半句。
地铁提示到了骡马市站,车随即减速,停下时的惯性让人身体往前倾斜。她的左肩触到了我的右肩。她转过头来,声音很轻、却十分清晰地说,公子,冒昧了。
听到这样的称呼,我觉得她很俏皮,忍不住笑了。我本想应以“小姐,无妨”,但想到“小姐”这个名词已被败坏,便用成都通常的称谓说,美女,无妨无妨。
她含羞一笑,未露一点牙齿。
蒲柳之姿而已,公子何往?
我到文殊坊,马上就到。
真是凑巧,小女子也是。
说着,车已到站。她礼让说,公子先行。
我很听话,似乎愿意做她让我做的任何事情。
我感觉到了人们为她的美投射来的目光,感觉到了那目光中以前未曾察觉过的重量。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上电梯时,她小心地提着裙子,跨前一步,与我并排站着。
请问公子是回家么?
是的,美女要到哪里?
小女子么?我还真不知往何处去。
美女从外地来?
正是。小女子对成都一点也不熟悉,又是晚上,有些害怕,见公子面善,便想寻个依靠。
我听了,心中欢喜,便说,美女,没事的,文殊坊附近有不少旅馆。
多谢了!她的手在身侧一礼,道了万福。
我又笑了,你可真是幽默。
幽默?她想了想这个词,是好笑吗?
你看,你又幽默了。
哦,我叫你公子,你该称我小姐的,可你叫我美女。美,只是一个人的外貌,而它如同烟云,转瞬即逝。
是应该这么称呼,可是小姐这个称呼……
公子这么说,是不是现在不能那样称呼了?
我本想告诉她,又想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词现在是啥意思,她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所以没有说什么。但她却追问道,为什么?
因为会引起歧义。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没想到她真的不知道“小姐”这个称谓的词义已经演变。我想她此前是不是一直在国外生活呢,即使那样,她也该有所听闻的。我说,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啊,小姐现在成了那个什么呢?我想着措词,也就是过去青楼女子的代称;而公子除了在古戏里,已没人这样称呼男人。
怎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的世界已堕入恶趣。
哦,原来如此!她有些吃惊。那小女子该怎么称呼他们呢?
正式场合一般称女的叫女士,年龄大的女人就叫阿姨或老人家,年轻点的一般叫大姐,与你差不多的可以叫美女;男士一般叫先生。
原来如此啊,但我还是习惯公子叫我小姐。
我们来到了地面上。街道和楼房有些颓靡。车辆已少,路灯如昼,夜空昏昧低沉。
美女,哦,小姐……你想住哪里?
小女子也不知道。我想在文殊坊里先走走。公子如不便陪我,请回家去,不过,公子该告诉小女子您的尊姓大名。
免贵,姓王,名实甫。这么晚,我怎能让你一个人转文殊坊呢,我肯定要陪你。
王实甫?难怪与公子有缘。小女子姓崔,名莺莺。
崔莺莺?那不是《西厢记》里的美女么?是网名吧?我也有个叫张生的网名呢。
真是凑巧。公子这样想,那就是了。
你那名字作为网名也太正式了。
我喜欢正式一些的名字。那我就叫你张公子吧。
无妨。我差点对他拱手一礼,那张生和崔莺莺不是王实甫笔下的一对有情人么?你看,我们多像是在网聊。
是么?她低头前行。你看,我们都可以演《西厢》了。
崔莺莺待月西厢,可这成都难得有月。
不管有月无月,那个崔莺莺都会等着张生。她的声音略带惆怅。
二
白家塘街的路灯被稠密的小叶榕遮挡住了,显得很是昏暗。除了两家美容按摩店,其它店铺都关了门。这是一条普通的街道,过去的痕迹已难以寻得。
过了红石柱街,我们从金马街拐进文殊坊。仿建的旧建筑给人一种恍然回到民国、回到晚清、回到元明、回到唐宋的感觉,一切如梦。只是电灯和偶尔开过的汽车会提醒你,你还是活在当下的这个朝代,不可能有张生,也不可能有崔莺莺。这个叫崔莺莺的女子,只不过与我叫王实甫一样,最多与《西厢记》中的主角同名而已。
莺莺小姐,小生冒昧问一句,你是到成都来旅行的么?
也算是吧。我很早就想来看看,我是卓文君的粉丝,也喜欢薛涛。但我主要是来寻一个人,以了却一份前世之缘的。
我看她说得那么正式,就开玩笑说,小姐该带着红娘的。
红娘到美国去了,给一个司长做了小。
是小三的意思吗?
小三?公子说的是小妾吧?也算是吧,反正是跟了那个司长。
我忍不住转过头去看她,但她很正常,容貌是人间的,灯光可以照见她的脸庞,身上的香味虽然独特,但也是人间的,她走起路衣裙“簌簌”,脚步也有声响。我想触摸一下她的手,她挨着我的那只手拿着那支玫瑰。
小姐手中的玫瑰像是真的。
小女子上地铁时,一个小孩卖花,跟着我,说是为了挣学费,我就买了一支。
那就有可能是假的,我看看。我说完,伸手去拿她手里的花。我的手触到了她的手背。她手背上的皮肤温润细腻。我轻轻地摸了摸玫瑰花瓣,又闻了闻,有玫瑰花香。我说,真是一支玫瑰。
小女子从没想花会有假的。
世界变得让人难以相信。我给自己找了一个伟大的托词,把花递给她。我有意地、再次触到了她的手。她的手娇小,手指修长圆润,每一枚指甲都是完美的,在路灯的照耀下,隐隐有些透明。你的手真美啊,像观音的手!
她害羞地转过了头,把接玫瑰花的手也收了回去。
公子,万勿轻薄小女子。
小姐,我是由衷赞美,无半点轻薄之意。
“小姐”这个称呼叫了几次,似已恢复本来意味。但我老怀疑自己身处的时代。我穿着运动鞋、牛仔裤、T恤,背着双肩包,但走在她身边,我老有穿着古人袍服的感觉;我也有在古代的文殊坊带着一位大家闺秀闲逛的错觉,我的目光会不由得越过文殊院的飞檐,去确认那些高楼是否还耸立在那里。
小女子喜欢公子的君子之风。
时下哪有君子!这个词早就没入古籍了。
那时下还有闺秀么?
人都变得粗鄙了,并已习惯了粗鄙,如果还有闺秀,那就是你。
纲常是朝廷的事。
朝廷的事不妄议也罢。
我们来到了白云寺街。她看了一眼街边的座椅,说,小女子要歇一歇了。
我忙掏出包里的纸巾,帮她擦了座椅。
谢谢公子,公子先请。
小姐坐,小姐坐。
她坚持让我先坐。我推辞不过,只好坐下。她随后才在离我两尺远的座椅一头坐下来。我望了一眼对面的爱道堂。这座尼姑庵在都市的数百万家灯火的俯瞰下,显得格外静谧,像一尊吉祥卧的佛。
三
小姐,听你口音,并不是四川人,冒昧地问一声,你从哪里来呢?
从你的戏本中来。她回眸一笑。
小姐又幽默了。
我不是叫崔莺莺么。
哈哈,小姐说话真有意思。
小女子也冒昧地问一声,公子怎么取了王实甫这么一个名字?
父亲给我取的,我姓王,甫是辈分,父亲希望我诚实为人,所以名字中就有了这个实字。他哪知道历史上有王实甫这个人啊。我呵呵笑了。
所以说,这就是所谓冥冥之缘。正是那个叫王实甫的用笔墨创造了我,才使你我得以在文殊坊相会。
你是演电视剧的演员?
公子是说戏子?小女子不是。
那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古代戏剧?
她摇摇头,淡淡一笑,没有作答。她的笑带着一丝伤感,更让人心动。
那你怎么穿了这身衣服?这也太“大唐”了。
好看么?
好看,像古戏中的仙女。
公子净说好听的。
我说的都是真话。
刚才走着,感觉不明显,坐下后,就觉得夜晚有些寒凉。
你冷么?我一边问她,一边把外衣脱下,要给她披上。
她触电似的一下站起,连连推辞,公子,我不冷的。
小姐,莫要嫌弃。我执意给她披上衣服。
谢谢公子体贴!公子如愿意,可否再陪我走走?
求之不得,即使这样一直走下去,我也乐意。
文殊坊面积并不大。但街巷相连,曲径交叉,像是永远也走不完。路过汉服馆,我说,有不少女孩子也喜欢像你这样,买件古服穿上,玩点穿越感。但我见过那么多,都没有小姐穿着好看、相宜,因为她们没有那种古雅的风度和气质。
公子难道就没想过我穿的是真正的古代的衣服?
要是那样,你身上的衣服就无价了。
公子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我?
怀疑什么?小姐骨子里透着妖娆,有些妖艳。难道你是妖?我想起了前几天刚在电影院里看到的电影《捉妖记》,接着说,那我就可以写一出《新捉妖记》了。
小女子倒希望公子写一篇《新西厢记》,这样,你和你前世的那个王实甫就有了呼应。她回过头来,媚然一笑,小女子倒不是妖,但可能是鬼的,公子难道不怕么?
我看她一眼,笑道,如果你是鬼,我愿意在鬼里加一个未字。
公子知道,魑魅魍魉都是鬼。
有小姐这样的魅力鬼,鬼不是比人更可爱么?
没想到公子对美如此执迷。
对小姐的美,谁能不执迷啊!你这么漂亮,只身出来,父母不担心么?
双亲早已仙逝。
那,小姐还有什么亲人?
她神情黯然,小女子曾定过终身,那位公子姓元名稹,我与他青梅竹马,后来他金榜题名,将小女弃了,娶了豪门闺秀韦丛。
我听她这样说话,忍不住笑了,好在没有笑出声。小姐肯定是学古文的,都知道元稹娶了韦丛。元稹是真写过《莺莺传》的。我语带嘲讽。
小女子没学什么古文,但就在古文里活着。
我就说嘛,不然你说起话来,怎会总是这么古雅。那个元公子为了富贵荣华,无情无义,属势利小人,小姐不嫁也罢。
可小女子无依无靠,沦落风尘,孤苦之状,公子哪能体会!她说完,忍不住长叹一声,以袖拭面,楚楚之状,令人心碎。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沉默良久,鼓起勇气,站定后,对她说,小姐,我还没有女友,你若看得起我……
她羞涩地低头道了个万福,多谢公子不弃!其实小女子深知,我与公子的缘分,是前世注定的,我来成都,正是为了见你。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激动地揽她入怀,紧紧拥住,以致害怕这是梦境而不敢闭眼,不敢呼吸,生怕在双眼闭合之时,一呼一吸之间,成为泡影。我……我没有做梦吧?
她在我怀里轻轻挣扎了两下,似在告诉我,回答了我刚才的疑问。我闻到了她头发的清香,感觉她的双手有些迟疑地、轻轻地揽住了我的腰。
我爱你!我说。
小女子亦然。
我低下头,捧起她的脸。她的脸朦胧、精美,像世上最完美的工艺品。她的眼睛开始是睁着的,黑而幽深,有路灯闪亮;然后,她的眼眸慢慢合上;她若兰的气息洒在我的脸上,进入我的肺腑。我的嘴唇触到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这种颤抖一下波及开来,遍及她的全身,然后传递给我……
她的身体变得更加轻柔,似乎正在化开;我的身体也倍觉轻盈,跃然欲飞。
四
我把她带回我的家里。那是我租的公寓,就在文殊院西侧,临人民中路。文殊院就在文殊坊内,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我喜欢黄墙青瓦,暮鼓晨钟,所以一到成都就住在这里。公寓只有一居室,有些像酒店的客房,有卫生间、一个很小的厨房。家具只有一个简易衣柜,一张1.5米宽的床,一个双人沙发——上面堆着我的脏衣服,四个塑料小圆凳,一张小方桌——我在上面吃饭和写作——上面放着我已用了七年的笔记本电脑,到处堆着我的书;还有一个一直没法用的空调,一个很难出现图像的电视机——从一开始,它们就是老板的摆设。
我想成为作家。但只在几家小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没有一点名气。我靠在一家小书店打工维持生计。每天值17∶00点到24∶00点的班。这个时候去书店买书的人很少,我可以看书,也落得清闲,但收入微薄,每月不到两千元。所以,我只租了这个位于楼角,没有窗户的房间。
带他回家时,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该把她带到这样一个寒酸的地方。但我也知道,对于相爱的人,即使狗窝,也是仙境。
穿过很长的走廊,来到走廊尽头,打开门,推开房门,一股潮湿的酸味扑面而来。我只好说,请小姐在门外稍等,我要让屋子透透气。
公子,无妨的。吻过她后,她似乎更害羞了。
就两三分钟。
邻居听到说话声,推开门。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姐,靠在网上招揽顾客,是个脸色发青的漂亮女孩,我和她相处不错。作家,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跟谁说话啊?还有女人,听声音很迷人啊?
晚么?跟平时差不多吧。我敷衍道。
怎么只有美女的声音啊?藏到屋里去了?
我牵着莺莺的手,有些自豪地看了她一眼,这是我女友,你没看见啊?
她朝我身边看,是有一股女人香。然后用不屑的口气接着说,你会有女友?是小姐吧?找小姐就找小姐呗,不要不好意思了。知道找小姐了,进步了啊。不过你他妈的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就在你隔壁,也不照顾老娘的生意!
我想告诉她,我的女友是一位真正的小姐,话到嘴边,又觉得说出来也不对劲,就说,你神经哟!
你才神经呢!她说完,“呯”地关了门。
我牵着莺莺的手,把她让进屋,请她在圆凳上坐下。
屋子脏乱。我很是尴尬难堪,忙着收拾。
她站起来,公子,我来帮你拾掇吧。
不用,很快就好的。我说着,把沙发上的衣服塞进衣柜里。
这么多书啊?她顺手拿起一本,翻了翻。
都是在文殊坊和一些旧书网站淘的。我喜欢那些旧书。
她把手里的书放下,又拿起一本。是《全唐诗》中的一册。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她轻声吟道,声音婉转,十分动听,吟罢,像是自语道,没想有这么多诗流传到了现在。
刚才那首诗就是那个唐朝负心汉元稹写的,那前两句谁都会引用。
她没说话,继续翻阅,突然掩面而泣。
我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关切地问道,小姐,你这是怎么了?
这一问,她哭得更伤心了。我看她打开的书页,是元稹的《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闻花气睡闻莺。
狋儿撼起钟声动,
二十年前晓寺情。
我不知道她看到这首一千二百多年前一个唐人写的诗为何如此伤感,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我把那本书从她手中拿过来,把那首诗又读了一遍,还是不理解那首诗与她有何关系,只当是因文生情,就劝慰道,小姐,你不要这么难过……
她点了点头,背过脸去,拭了眼泪,带着哭音说,真是对不起公子。
小姐多愁善感,读诗生情,可以理解。
没想这等诗,也流传至今了。
是的,这么好的诗,流传下来也很正常啊。
小女子喜欢唐朝,但有时也令人感伤,因此失态,请公子谅解。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令人感伤、甚至悲怆的事。
也是啊。我知道唐朝距今已过千余年,如今的天地已大不同了。我看到飞机像宫殿一样在天空来往,地上跑着火车和汽车,再也没有马车了,也没有骑马的人,甚至很难见到马了。
只有在留下的文字里才能找到那个朝代的气息了。其实人并没有变化多少,不过长衫变短褂。
人心古今同吧。
正是。因为爱、因为情、因为生离死别依然,人就还是古人,世界也依然老旧。
但现在的生活倒真是便捷简单。小女子和公子在一起,已无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看《西厢记》里崔莺莺的大胆、开放,和今人其实无异。
那是公子写的戏本,只能说作者希望崔莺莺那样罢了。
我笑了,我哪能写得出那样的经典啊。
谁让公子和那个王实甫同名呢?王实甫凭了一个女子的悲剧,得以不朽。你何不再写一出新西厢记?
可惜我没有那样的才华。我笑了,岔开话题,小姐肯定饿了,我给你煮碗面吃。
小女子不饿,公子烧点水喝即可。她迟疑了一阵,说,小女子走了远路,还想……洗漱……那个“洗”字发音很低,几乎听不见。她说完,低了头,满脸绯红。
好的好的,我先给你放热水。我说着,进到卫生间,打开热水器,把里面自己的袜子、裤头扔进洗衣机,又把里面拾掇了一番,然后看着温度上升,把冷水放掉,再出来,找了一条毛巾,递给她,满是柔情地说,水温是调好的,你打开就有热水。
多谢公子。她进到卫生间,又退了出来。公子,水在哪里?
是热水器,我用的是热水器。我再次进到卫生间,教她怎么使用。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她指了指抽水马桶。
我看着她,不相信她没有用过这东西。我不知用哪个合适的词来回答她,想了想,就说,用来……出恭的。我说着,打开马桶盖,坐在上面即可。
啊?她颇是惊讶。
现在都用这玩意儿,完事后一冲即可。我给她指了指马桶开关。这些东西小姐难道没有用过?
她点点头,羞涩地笑笑,我说过,我来自戏文里,戏文里哪有这些东西!
我也笑了。小姐真会开玩笑。
说完,我让她试着开了热水器的开关,见她会了,才走出来,替她关好门。
我烧着开水,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水流声,终于放心了。
小姐,水温怎样?
公子,刚好的。她的声音里带着水汽。
我打开煤气灶烧水时想着突然拥有了这么一个绝世美人,还是有做梦的感觉。
二十多分钟后,水流声停了,过了一会儿,她穿戴整齐地走了出来。她面色红润,头发湿漉漉的,乌黑发亮,披到了臀部。
我把泡好的茶递给她。
茶很香啊。她用纤手端起茶杯,闻了闻,嘬起小嘴,吹了吹,品了一小口。
这是今年的春茶,我妈采摘、制作的,前几天刚找人带来。
没想到公子老家还有这等好茶。
是的,老家云顶山上产云顶茶,虽无名气,但茶确实好。
如此好茶,我有清福了。她端坐在凳子上,一边品着,一边翻我堆在地上的书。
公子有《西厢记》吗?
没有,不过,你如果想读,我可以给你买一本。
不用,我只是问问。
我想起她对现代生活的陌生,颇是好奇,便问她,小姐,你老家是哪里的?
小女子博陵人氏,幼居崔庄村,真名崔小迎。十岁时,父亲去烟粉作坊做工,举家搬迁,到了沁园。后来,小女子到了浚县,住在浚县第一实验小学里。
浚县当属今天的鹤壁市,沁园在博爱县,可惜我都没有去过。
公子以后或许会去的。
小姐喜欢看《西厢》?
小女子就是那里面的人。
我“哈哈”笑了,是啊,你叫崔莺莺么,这么说来,我叫张生,也是里面的人了?
也许的。但你是王实甫,这个张生的原型是元稹。
真是大诗人元稹?
正是。小女子和元稹邻村而居,八岁时他父亲逝世,我父母将他带到我家,视同己出。我和她从小一起玩耍,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便在沁园私定了终身。沁园是汉明帝刘庄为其五女刘致建造的园林,颇为有名,常有名流大家、士绅官宦来此游玩,元公子因此结识了令狐楚、韩愈、白居易、李绛等人,受其熏陶,习诗学文。元贞十七年春,十五岁的元公子以明两经而擢第,人夸他少年俊才,说小女子是出水芙蓉,郎才女貌。不想元稹后受太子少保韦夏卿赏识,与韦家千金成了婚,从此再未谋面。
我听得云山雾罩的,突然怀疑她的思维是否有什么问题。我说,元稹曾作《会真记》,也就是《莺莺传》,写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那个崔莺莺难道就是你么?
正是小女子。她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最让小女子不解的是,元公子为何要借张生之口,诬我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甚至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他的说法我不作辩解,时人自然心明。
是啊,后人都说元公子借张生美化自己,有污德行,被人诟病。鲁迅说他的《莺莺传》“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这个鲁公子说得好!欲盖弥彰,元公子定然没有想到。
我有些害怕起来,我一次次偷偷地观察她。但她的确是人——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美人。她看上去也是正常的,但我感觉她似乎无法区别现实与梦境。
那小姐为什么要找我?
我要感谢你重塑了我。《会真记》在世六百年,我都是一个尤物、妖孽,你写了《西厢》,才让世人对小女子有了新认识。当然,小女子不是相国小姐,而是贫寒闺秀。因为爱元公子,才与他私定终身。他攀附豪门,娶了韦丛,我心中痛苦,无人能知。小女子知他用心,为他着想,从此隐退,未做任何纠缠。可元公子为了荣华和浮名,辜负天高地厚情也罢了,最后却那样写我,真是令人心伤。
可我跟王实甫确无关系。
公子若与他无关,为何取了一样的名字。
我前面说了,是我父亲给我取的。
除了公子,自王实甫逝后,极少有人取这个名字。
我不信。说着,打开手机百度了一番,发现今人的确很少有用这个名字的。我有些无奈地望了她一眼。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和他相隔数百年。
这说明公子和他有缘。
我淡淡一笑,不知该说什么。
和她虽然相识短暂,但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她。她恍惚的状态让我忧虑。但她又回到了现实中,似乎一下从唐朝回到了当下。她品了一口茶,请问公子高堂可好?
高堂……?我想了想,终于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了。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年事已高,身体尚好,但我一事无成,婚姻无着,所以老人时常为我忧心,现在,她如果知道我有了你这个仙女,一定高兴得很。
公子,小女子出身贫贱,哪是仙女?但小女子相信缘分到后,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但愿真有这样的缘分。
“愿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这是公子在《西厢》里写的话,那公子可愿与小女子遂了前世缘分?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愿意,永生永世。
可不能立誓,不然,小女子每生每世都会来找你,你每一生每一世都爱着同一个人,那会多么无趣。
我愿意。
我们已定终身,那小女子该怎么称呼公子?
我们可以称呼彼此的名字,结婚后你可以叫我老公,我叫你老婆,当然,也可互称亲爱的。
已无名讳?也不能叫相公?
那是老规矩、老称谓了。
那小女子和公子就互称亲爱的吧。
但在长辈面前还是叫名字好些。
亲爱的,我听你的。她说完,格格笑了。这个称呼也不错。
我有些奇怪地看着她。我发现她不是因为幽默,也不是因为好玩,而真的是对现实世界一无所知,好像真的来自古代。
亲爱的——,老公——!她像好玩似的,把两个字音故意拖得很长。
亲爱的老婆。我也叫了她一声。
老公是老公子的意思?可你不老啊!老婆,听着也怪,但我的确是很老了。
亲爱的,你永不会老的。
亲爱的,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我觉得她是那么美,那么迷人。我把她揽入怀里,开始吻她。她喘息着,那种娇喘,令人迷醉。
我感受了她完美的、令人沉醉的肉体和娇柔万端的激情。柔情蜜意充满了这个简陋的房间,溢满了这座庞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因为爱,这个房间变得像整个世界一样丰富了。
她安静地躺在我怀里,温润如玉,气息喷在我的胸口,痒酥酥的。我打开灯,我想看到她的脸,她的肉体,我要记住她肉体上比尘埃更微小的部分。她如花绽放,比花娇艳。我抚摸她,充满无限柔情。
五
屋子没有窗户,我醒来时,屋里依然很暗。但从过道的动静可知,很多人已经起床,街上已渐渐喧嚣。
摸摸枕边,枕是凉的。摸摸另半边床,床是空的。小姐。我轻声唤道。没有应答。莺莺——仍无回应。亲爱的——还是无人答应。我心头一慌,翻身而起。开了电灯,看卫生间没人,推门去看过道,过道也是空的。我跌坐床沿,神魂俱散,又问自己,莫非是春梦一场?回想之后,一切都无比真切,细看枕上,竟有她的四根落发。我把它们小心拾起,想把它放入书中。才见餐几上多了一册书,竟是旧版的《西厢记》,书上放着一缕青丝,青丝下压着一张纸,展开之后,是用毛笔写的娟秀繁体小楷:
昨夜歡情深,
今朝別意濃。
西廂無覓處,
白雲付西風。
我读罢,悲声难抑,胸中疼痛,吐出一口血来,人不由得往下倒去,人还没有触地,便没了知觉。
醒来时已不知何时。我艰难地爬起来,屋子还是空的。我踉跄着推开门,一束强烈的阳光像一柄巨刃,劈开过道。我沿着昨晚走过的路去找她。我怕她只是出去了,特意留着门,没有锁。我神不归位,恍惚着,但每一步我都记得很清晰。我一步不落,在文殊坊里转了好几圈。每间店铺、茶舍、饭馆,包括文殊院、爱道堂,我都去找了,但没有她的踪影。然后,我又进到地铁站,在昨晚与他相遇的地方站了很久。我希望她能像昨日那样重新从地铁里走出来,但那么多人涌出地铁,就是没有她。我沿着昨天的路径走出地铁,再走入文殊坊,再走回家。我多么希望她坐在那个简陋的餐几前,正一边安静地翻看一本书,一边等我。但屋子里还是空的。
我又从屋子里走出来,走进文殊坊,走到地铁站,再返回。就这样往复多趟,以致引起了地铁站保安的怀疑。
我突然记起她昨天说过她住在河南浚县第一实验小学的话。我想那里至少可以问到她的下落,便决定到那里去找她。
我敲开了邻居女孩的门。她开门见我,惊讶得张大了嘴。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我想去看一个朋友,想跟你借一千块钱。
你这个鬼样子怎么去看朋友?她把我拉到她屋里的穿衣镜前。
我看到自己的确像个鬼。头发凌乱,嘴角和左脸都有血迹,胸前的衣服上也有。我早上起来,有些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吐了一口血,没有收拾。
你不会是去看哪个女人吧?昨晚你还对着空气说你有了女友,我看你是想女人想疯了!她从钱包里抽出十张百元票子,递给我,你知道,这是老娘的卖身钱,早点还我。
谢谢,谢谢!我三个月内一定还你。我回到屋里,换了衣服,洗了脸,把她留给我的书连同那缕青丝包好,带上,小心地装好钱和身份证,就准备出门。临出门之际,担心她会回来,便把钥匙交给了那个女孩,说如果有个女孩来找我,可以把钥匙交给她。那个女孩不屑地撇了撇嘴,鬼来找你。
我还不放心,又在门上贴了纸条:
莺莺,
你如回来,钥匙在邻居女孩处。
万望等我,我最多十日即归。
实甫,6月11日
六
我买了当晚从成都去安阳的火车,在安阳下车后,我坐班车到了浚县。到达那里正是下午,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第一实验小学,在学门口,我问保安,大哥,您是否认识这学校里姓崔的人家。
保安把我打量了一番,说,俺这学校里只有教师宿舍,只有一个姓崔的老师。
我心中不禁一喜,她是叫崔莺莺么。
保安摇摇头,她刚从河南师范大学分过来,俺只晓得她姓崔。他指了指来客登记本,说,你写下来俺看看。
我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崔莺莺”三个字。
崔莺莺?崔莺莺,保安在嘴里念叨了几遍,突然转过头来奇怪地盯着我,你找崔莺莺?
我点点头。
我吃惊地又盯了我一阵,怎么和古戏里的崔莺莺一个名?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犹豫了一阵,说,她是我的女朋友,我前两天在成都还见过她。
保安吓得往后跳了一步,你不会碰到鬼了吧?俺们这学校里还有一个莺莺坟。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俺们这个坟里的崔莺莺死了一千多年了。他朝校园里指了指,你看,那里还有一块莺莺碑。
他的话把我吓住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立着一块古碑。
这怎么可能呢。
保安打量了我一番,小伙子,俺看你是想进去参观这个古迹吧?这里不收门票,你何必搞这些名堂,大白天的,瘆人得很。
那我可以进去看看么?我扯了个谎,我其实是四川大学的研究生,要写一个崔莺莺生平事迹的论文。
不行,现在还没放学。
那我放学再来。
等到孩子们都出了校门,我给保安买了一包烟,又到了校门口。他接过烟,抽了一支,打开了校门,带我来到坟前。
我看到,那碑高宽均约一米,左边及右下角已残缺,上有“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袝墓志铭”的正楷碑文,历经沧桑,许多地方已漫漶不清。
我对保安说,碑文中只说崔氏,并未提及崔莺莺。
崔氏就是崔莺莺嘛,俺们这里的人都知道,这地儿埋的是唐朝的那个崔莺莺。保安说完,转身回校门口的值班室去了。
四围寂静,夏蝉凄切。我抚摸碑石,呆立良久,恍若梦中。想起与她的相识、相爱,心里凄然,头抵碑石,不禁泪如雨下。
正在这时,那个保安来叫我,小伙子,那个姓崔的老师从教室里出来了。
我偷偷地抹了泪,往教室那边望去,果然看见一名女老师正在锁教室门。但从背后只能看到她的齐腰长发和直垂到脚后跟的白色连衣裙。当她转过身,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那不是崔莺莺吗?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几步跑到她跟前,莺莺,你真跑回来了!
她站住了,看着我,您是——?
我是王实甫啊?你走时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王实甫?你是哪个孩子的家长吗?
你怎么啦?不认识我了?三天前,我们在成都一起相处过。
她笑了——是那种我见识过的含蓄、古典的笑。您肯定认错人了,我大学刚毕业,还从没去过成都呢,不过,如有机会,我倒是很想去玩玩。
你是崔莺莺么,跟《西厢记》里那个崔莺莺的名字一样?
是啊,怎么啦?
我拿出那首诗作,面对他念起来。昨夜欢情深,今朝别意浓。西厢无觅处,白云付西风。
这首离别诗很有意境,不好意思,我大学虽然读的是中文系,可我记不得它是古代哪位诗人写的了。
小姐,我还有个网名叫张生。
她一听,顿时芳容变色。我是一名人民教师,你怎么能用这样的话骂我呢!她说完,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走了好远,她又回过头来,盯着我,你这个家长真没教养!她的目光冰冷,满是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