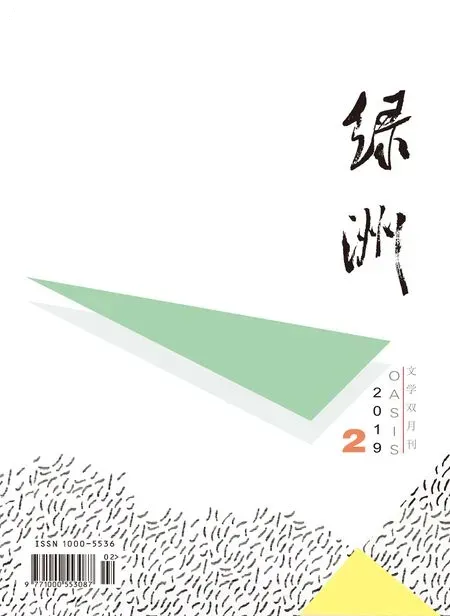蛐蛐在歌唱
杨新生
我所在办公楼虽使用有十多年了,但建筑质量是过关的,坚实得像一座屹立在车站广场的白色堡垒。
办公室位于三楼,墙外包着一条十多米长的大凉台。几扇大窗户都是密封良好的塑钢框架,严密的平板玻璃。透气的几扇窗户,外面也加了隔阻蚊虫的密实纱窗,蚊子、苍蝇之类的飞虫,只有在外窥探的份了,无法飞进我幽静的办公室,骚扰我安逸的工作。
可是一只意外的闯入者,还是在这夏雨浇淋,艳阳交替的六月,不知是在哪一天,神奇地进入到了我高立半空,近乎密封的办公室,并以自己的方式,大声地告知它的到来,它的存在。
因为它在唱歌!无所顾忌地歌唱!
这是一只蒲松龄在《聊斋》中倾情写过的“蟋蟀”,我们称之为“蛐蛐”的昆虫。我已有许多年没有见到过它们了,可是谁知它竟然潜入到了我的办公室,安然地在这里落户开唱了。
这是一只爱唱歌的蛐蛐,有着美妙的歌喉,清脆的嗓音,还有不知疲倦的力量。它歌唱的时间没有固定,想什么时候唱,就“蛐蛐……蛐蛐……”地开唱了。唱累了,想休息一会,戛然而止,就没有了声响。过上一阵,也许是睡醒了,烦躁了,寂寞了,或者是想家了,它又开始“蛐蛐……蛐蛐……”地唱起来了。
刚开始听它唱歌时,一直感觉它是被关在门外的凉台上,寂寞地趴在门缝里歌唱。也许是祈求我能够把它放进屋里,躲避暴雨的侵袭,烈日的炙烤。可是没几天感觉歌声愈来愈近了,起身查看判定: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它以什么特殊的方式,早已潜入我的办公室内,就在我办公桌旁的副桌下面,潜伏安家了,得意洋洋地间歇歌唱着。
我对蛐蛐是熟悉的,它曾给我童年的时光,带来过无限的快乐。可现在我早已丧失儿时的童趣了,再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掂个小瓶,跑到离家好远的田地渠沟旁,像是一个职业探秘者似的,小心地翻开沟沿上一块块泥土,凭着感觉,循着声音,既惊又喜地寻觅、捕捉,这些通体黑亮的,会蹦、会叫的小虫,带回家中成了母亲养的母鸡们,欢喜争啄的美食。因而,此次对于它的到来,既没欢迎,也没惊扰。
这只意外闯入的蛐蛐,并不在意我的冷漠和无视。它应该知道我是善良的,它无疑也是幸福的。偌大的两间办公室(一间卧室),足可以作为它恣意歌唱的舞台。既无天敌的捕食,也无人为的毒杀;既避开了六月风雨的侵袭,也躲去烈日的暴晒,安逸自在,只管凭着自己的性子和心情,撒着欢地举办个人演唱会吧。
也许是这只蛐蛐真的理解了我的宽容和美意,“蛐蛐……蛐蛐……”它的歌声似乎就没有中断过,总是攒着劲儿,仿佛一个曲调不变地在歌唱着,但是留神仔细倾听,还是有着不少的变化哩!它的歌声有时是舒缓的,像是柔声细语的诉说,诉说饱含在心中的爱恋;有时它的歌声骤然变得激越起来,像是激烈的争执、愤怒的咆哮,在宣泄积聚在胸中的愤懑;有时它的歌声是时断时续的短暂停顿和再续,像是与谁在平和地辩论和交流,推心置腹,思想碰撞;有时它的歌声是清丽而欢快的,伴着黎明晨曦映入室内的光亮,它的歌声愉悦而清脆,仿佛也在欢呼新的一天开始了,呼唤值班留宿的我该起床了。
这只神奇的蛐蛐啊,你来自哪里?为什么总是这样倾情歌唱?你嘹亮的歌声,打开了我封闭的心灵,吹散了我阴郁的心绪。让我再次触碰到了一个神性的世界,使我蒙尘的心田拂过了和谐有爱的清风。
六月的初夏,莺飞草长,百花争艳,这只抛弃了室外风光明丽的盛夏时光,独自与我为伴的神奇蛐蛐,一直坚守在我的身旁,放声长啸,低吟浅唱,抒怀至情。它把上天的眷顾,大地的问候,通过它小小的胸腔和不竭的歌喉传递着。让我在这美妙的六月,每天都陶醉在天籁之声的盛宴中,感受着异样的欣喜和幸福,感恩着自然的造化和神性光辉的福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