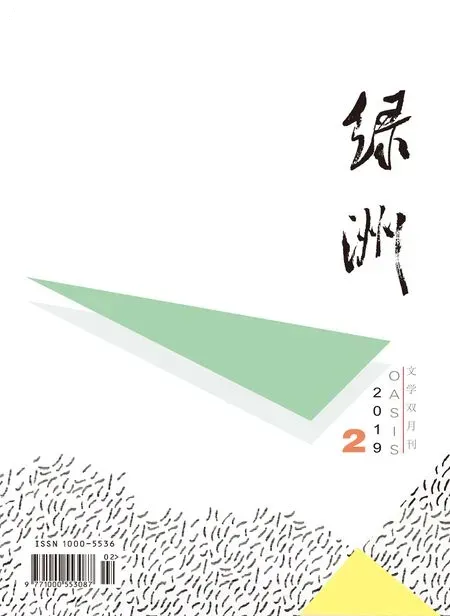柳枝词
叶尘
贵奶奶满头白发,明晃晃地,沐在三月的光中。脑壳渐渐低垂,在胸前一顿一顿。
柳树成林,贵奶奶躲在一棵老柳背后。隐隐约约,村边边上,娘老子颠着小脚在高喊:章雪柳,你个砍颈的,死到哪里去了,今日还不把你那双马脚裹起,我就不是你娘。
喉咙里痰一上一下,“呼噜呼噜”响。娘老子的喊声还在起伏:章雪柳,你个砍颈的……
贵奶奶猛地抖一下,睁开一双眼,婆娑,昏黄,一窝浊水,收不住地顺着沟道流淌。院门口有老柳,笼着一团烟绿。贵奶奶对柳说话:我娘喊我回去呢!
竹躺椅本来是能躺的,但贵奶奶坐着就打起了瞌睡。人老了就这样,晚上睡不着,白天坐哪瞌睡跟到哪。刚还自说自话,转眼嘴巴张得吓人,鼾声高高低低,像风刮过柳林。
贵奶奶右手拄拐棍,左手撑椅子,缓缓提起皮影似的身子。她身着立领、侧襟、盘扣的青布褂子,一摇三摆的,像极了皮影戏里的人物。贵奶奶挪到屋檐下手摇井旁。手摇井是贵爷爷在时打下的。以前大家都是到院门前的小河里提水吃,走上几步,“咣当”一声,舀一桶水,提回家就淘米煮饭,祖祖辈辈都如此。后来,血防院说洞庭湖区有血吸虫,吃河水会得大肚子病,于是家家户户都打手摇井。井水含铁,井筒土黄土黄,水泥池上生着的苔藓也染成了黄色。连水泥池放水的洞眼外,还有一条黄尾巴拖起老长老长,让人感觉日子被锈钝了,泛着老照片的色调。
井旁有个木桶,桶里是贵奶奶的衣服。除了里衣裤,其他都是侧襟的老式衣服。贵奶奶抖抖索索,拿起一件,前襟后背,一一扯平,往屋檐竹竿上晾,可手抬不上,脚抻不直,再不是那个麻利的“马脚”,只好作罢。
娘老子坐在雕花宁波床上,用白布一层一层把小脚包好,塞进菱角尖似的三寸小鞋里,嘴里不停数落:看你这双马脚,将来谁要你?背着一张犁,拖泥带水的长工德贵正好听见。后来,他用“马脚”这个名,唤了她一辈子。
许是这双“马脚”注定了一生的劳碌。别的细脚婆婆移着小碎步还摇摇欲坠时,她一双大脚打在泥地上,“啪嗒啪嗒”响。就在几年前,她还照样洗衣煮饭喂鸡种菜。只是她活得太久,隐隐地惧那命硬吸后人阳寿的说辞,便没轻没重地不顾惜自己,可摔不死锤不烂,像颗铜豌豆。
八十八岁这年,贵奶奶赶鸡进笼,绊到门槛,栽翻在地。乡邻断言会中风,谁想,她脑壳清白,嘴也没歪,但腿脚到底还是落下毛病,慢慢地萎缩变形,使不上力。病痛缠上身,心底竟放下块石头,有些欢喜。贵奶奶再没出过院子门,每日里痴望着门前的老柳。老柳逢春,吐芽绽绿,柳丝丝在院子里舞。贵奶奶接连又看了两年春柳。
老柳是成亲时,贵爷爷亲手栽下的。那时,村里大大小小的柳到处都是,跟那辈人一样,土改、1954年大洪水、人民公社、大跃进……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有的没了,没有了就会扦插新的柳,而有的九死一生,存活下来。村子里依旧春风荡漾,柳絮扑飞,仿似春雪。晒衣服衣服上沾着,晒菜菜上沾着,连头发也沾,冷不丁吓一跳,以为一夜就白了头。贵奶奶正是柳絮飞时出生,她爷老子读过私塾,便给了她“雪柳”这么个名。
老柳越发地弯腰拱背,树的一侧,被岁月掏空成一个大洞。这柳下从清静到热闹,又从热闹到静寂,晃眼六七十年。最先在这柳下的是贵爷爷和贵奶奶,那时柳还嫩着,像刚出嫁的新姑娘,能掐出水来。天气晴好,饭桌就摆在柳下,席地顶天,豁敞。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贵爷爷走。
年轻时,他们在树下扯谈,说成亲时,仅有几间茅屋,洞庭湖上刮来一阵风,就能把屋顶掀翻。两人在堂屋里拜天拜地,再拜了贵奶奶爷娘的灵位,抓一把糖打发看热闹的乡邻和细伢,便作了数。
贵奶奶说,你那天的样子好蠢,什么话也不晓得说,只一个劲地作揖。
贵爷爷就说,你那天穿着那桃红的褂子,脸衬得几好看。
后来,这柳树下,添了大女儿大儿子。贵奶奶耳朵里有“依依呀呀”的声音,像歌谣。那是大的带着小的,含混不清地唱歌。眨眼,大和小蹦蹦跳跳,还能帮忙洗菜煮饭。再眨眼,没有了大女儿大儿子。那个春天,梅雨下得人的心又湿又冷,好长好长的日子,贵奶奶都不敢去屋前小河里提水。青石码头生出绿色的毒牙,河长了血盆大口,太狠啊,一回就吞了两个。
日头已到中天,并没有声音,只有风一下一下拨动老柳。老柳间,有光随着柳丝晃来荡去。贵奶奶又花了眼,柳下,正热闹着。贵奶奶炒出香喷喷的豆子、芝麻,加上浸盐的姜丝,用这几样泡出的茶,叫豆子芝麻茶。贵奶奶掰着手指头算了算人头,小儿子,儿媳,四个孙伢,如果小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伢回了娘家,或又有三五邻里,手指掰了好几轮,都掰不完。但贵奶奶一个不落,不分大小,每人一碗豆子芝麻茶。每个人都记得贵奶奶的芝麻豆子茶,热乎,香甜,还有点咸。
但贵爷爷最喜欢的,是酽得浓浓的滚烫的苦茶。想不清他那个嘴是什么做的,又烫又苦,张口就往嘴里灌一大口。贵爷爷几口苦茶下肚,精神就来了,声音洪亮,喜欢讲古,也喜欢讲鬼故事。他捞起肥大的裤子,指着腿上的一块大疤,说那是他做长工给人开荒时,遇到野猪,跟野猪打架留下的。他又讲土改队如何抓地主,如何拿地主吊边猪,如何把地主罩在箩筐里,一根蜡烛没点完,不准出来。讲得唾沫星子直飞,瞥见贵奶奶来了,立马就闭了嘴。转身又讲起鬼故事,什么吊死鬼、药死鬼、迷路鬼,讲得那些细伢子越围越紧。若是夏天,天上的星子也越挤越密,再挤一点,就会掉下来几颗,一伸手把它接住。
贵奶奶想喝点茶,豆子芝麻茶,垫下肚子,或者一碗苦茶也好。贵奶奶左顾右看,左右摸索,不知要看什么,也不知要摸什么。
有人扒开竹篱递话,贵奶奶,你崽伢要我搭个信,中午他两口子在河对面吃烂肉(丧饭),吃完了再带点好菜给您老人家。贵奶奶便想喊那人帮忙倒碗水,举着脑壳瞧半天,只看见一团灰乎乎的影子。等她想起来一个名字,那人早已走了。贵奶奶先前没留意,耳朵也不好用,这会子仔细听,是有“铿铿锵锵”的声音。心里就有些怄气,难怪那两只脚跑得飞快,衣服都没晒。要你们带什么好菜,我没那么好吃!一怄气,贵奶奶那两片枯叶似的嘴唇就越发凹了进去,扁成了一条线。
衣服没晒,晃荡着箩筐似的大屁股出去了的是继媳妇。前头媳妇拉扯大四个儿女,没享一天福就睡到了村边的柳林子里,不足五十就走了。继媳妇比儿子小十来岁,打牌嚼槟榔,胸前一对奶子张扬得收不住,随时能跑出来。贵奶奶摇头叹气,前头婆娘是根草,后头婆娘是个宝。
是哪个呢?贵奶奶默神。是那张五吧,好长日子不见影了,原来他总是要跄到这院子里,没声没气地坐一阵的。熬过冬,没熬得住春,他还只八十,比自己小一截。这样一想,便又生出那活得太久的惶恐来。惶然坐上一阵,贵奶奶又垂顿起脑壳,头点几下,身子大惊一下,反反复复,就这么混混沌沌打瞌睡,似乎总能听到谁喊她的声音。
继媳妇回来时,日头已经有些西斜,贵奶奶也醒醒睡睡好几回。继媳妇用塑料碗打包了好几碗菜。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妇人,也是常年四季在牌桌子上。她长着一张鲢鱼嘴,吧唧吧唧,你媳妇对你好呢,晓得你喜欢吃盐菜扣肉。贵奶奶说,是呢是呢。看着那堆得满满的肉菜,贵奶奶知道等会继继媳妇又会拿到冰箱里去冻着,以后好几天都热这些席面上的菜吃。贵奶奶想掉眼泪,怕别人讲这老厌物好吃懒做,这么大年纪还吃得这么多,又怕别人讲不识好歹。眼泪真淌下来了,但她淌泪的毛病已有好些年,谁知道她为这淌呢。贵奶奶不愿吃那些菜,说肚腹不好,要吃茶泡饭。继媳妇也不多讲,给她用茶泡了饭,端过来时,眉头朝同来的妇人跳了跳。
新民呢?贵奶奶问她。
还在灌猫尿,骂都骂不动,混吃等死的鬼。继媳妇声气大得很,贵奶奶便噤了声。
贵奶奶把一碗茶泡饭送进肚里,尿早已胀得难受。腿像是两根死木,她几乎有些拿不定主意,到底先动哪条,哪条还长在她身上。贵奶奶试了几下,刚把身子撑起,又跌坐下去,忍不住叫唤了一声“哎哟”。继媳妇胡乱地晾衣服,也不抖开些,湿嗒嗒一团就搭在竹竿上,好像那是一块块讨人厌的抹布。对于贵奶奶的“哎哟”,她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么的,晒完衣服提起桶就进屋去了。贵奶奶看着那抹布一样的衣裳,捶揉了半天腿,然后自己再试了几次,呲牙站了起来,慢慢挪到卧室里。
贵奶奶睡的是暗红色架子床,漆迹斑驳,靠墙那三面是细圆木的围栏。四个角上各伸出根粗长些的圆柱子,往上搭出高高的床架子,罩着白色的蚊帐。蚊帐好久没换洗了,帐顶上有些黄色的脏印渍,不知哪来的,也许是老鼠的尿渍,贵奶奶常在晚上听到老鼠的“吱吱”声。这在从前,贵奶奶是不能容忍的,隔三差五就会和媳妇把家里的帐子洗了,床铺草晒一番。
她那些孙伢们都踩过帐子。土布帐子吸了水,提不起揉不动,就用洗衣粉泡在大木盆里。孙伢争相着一顿猛踩,踩得脚丫子白白嫩嫩,踩得泡泡堆起一盆,又捧起泡泡使劲吹,杨柳风一来,能上天。孙伢们的笑声也上了天,越发起劲,帐子踩了一道又一道,直到浊水变成清水。帐子白白净净,一家伙晒干,晚上支起来,床铺草也重新铺好,就像是睡在阳光和风里。孙伢都往架子床上拱,争着和她睡,她一人屁股上一手板,说你娘的也洗了,跟你娘睡去。她这个精精瘦瘦的婆婆子,带过的细伢就跟那结的葫芦瓜一样多,孙伢、外孙伢,甚至外曾孙伢,一年四季满地打滚爬高打架,热闹生气又让人生烦。眨眼的工夫,一个个都不见了。贵奶奶牵着挂着,却又一天天地空洞下去,一些带过的细伢,从老远的地方回来,她左看右看看不出到底是哪一个细伢长成了这个模样。
架子床边,放着一个坐便器。贵奶奶坐在坐便器上,解了裤扣,再一点一点把裤子褪下去。贵奶奶正对着摆在墙边的老料。老料早已上好沥青,泛出森冷的光。贵奶奶总觉得那老料蒙灰多年,早已等得不耐烦。
贵奶奶再挪出屋门口时,西斜的光照着老柳,一个又一个金色光环在柳叶间闪烁,像是谁在朝她眨眼。继媳妇大概又去了道场,老人的道场正是村里人相聚的好时候,一连几天,吃酒打牌或看道人做道场,放肆地撒欢。
晚上贵奶奶还是不肯吃菜,吃了一碗茶泡饭就上了床。上了床,并没睡着,白天还好打发,晚上的日子才真正开头。天渐渐黑去,一切都静寂着,久久地静寂着,让人觉着人世间的热闹不过是打了个瞌睡做了个梦。贵奶奶脑子里白惨惨地一片,觉不出味,空得可怕。其间,儿子和继媳妇回来过一次,好像是要拿箩筐,毕竟是去帮丧事,该出的力该借的东西是不能推辞的。儿子问,娘老子吃了饭没。继媳妇说,肚子里长牙尽是名堂。儿子回了一句,小点声气……两人渐渐行远。
贵奶奶身子僵硬,想翻身又翻不动,霸蛮挪动,发出“哼哼”的呻吟。实在睡不住了,贵奶奶就撑起来摸几粒床头摆的葡萄干吃,这都是孙伢买的。葡萄干嚼在嘴里,酸苦,吃什么都不是原来的味。
夜深,“铿铿锵锵”的声音便清晰多了,道人先生带哭的夜歌子通过扩音器凄凄凉凉地送来,跟在耳边一样。道场做到了哪里?今夜要上黄泉路过奈何桥了么?其实贵奶奶不去看也知道,一辈子看过的道场,不晓得有多少,有时站在屋门口,听到平原上不知哪里飘来的唱腔,也能听得眼泪涟涟。
送亡灵,路上行,
桥头柳啊,莫挂心,
三关六朝盘问你,
你是阳间的贤德人……
贵奶奶好像看到谁踯踯躅躅地上了路,一会是贵爷爷,一会是媳妇,一会又是老女儿,又或者是这村里故去的人……贵奶奶就这样听了一宿的锣鼓和夜歌子。
柳色老成了些,清明雨来了。天阴冷灰暗,贵奶奶只能整日地坐在床铺上。
细孙女来到贵奶奶床前时,贵奶奶正打瞌睡。孙伢们都在远处的城里有家有细伢,每年总会在这时节派个代表回来挂青。细孙女回来,自然又是大包小包,蛋糕呀灯芯糕啊保暖衣裤啊,一样一样摊在贵奶奶面前。串门的人说,你老人家福气好,孙女子孝顺。贵奶奶展开一脸的枝枝杈杈,笑得老树逢春的样子,说话也利索了些,连连招呼着:她嫂子,你吃你吃。
孙女顶着清明细雨去柳林里挂青,儿子扛着一把锹跟了去。贵奶奶从床上下来,挪到后门口坐着,举头张望。贵奶奶就好像看到他们走在那田坎子上,穿过一丘又一丘的田。
前几天天气好时,田被犁翻了,没翻进泥土的红色紫云英黄色油菜花东倒西歪,雨在白亮的田水里打出一个又一个圆圈。两爷女走向田尾巨大的一团绿中,这绿被雨洇湿,暗沉。过一道低坎,又上一道高坡,疏疏密密的柳树屈着手臂,向上伸展,或者低回垂向土地。每一棵柳,都有一道密语。高坡上,坟影重重,旧坟里添新坟。
那靠南较大的坟堆是贵爷爷躺在里面。两爷女先拨了坟头草,再拿锹往坟上添新土,然后把挂着纸扎红球的长长竹竿插上坟头。红球和垂着的红纸带就在风里招啊摇。细孙女点烛、烧纸、磕头,然后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起来。鞭炮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有人挂青。细孙女又到柳林边她娘老子的坟上重复了同样的程序,照例会无声地站上一阵,好像在听她娘老子是否睡得安好。然后两爷女一前一后地回家,都很少做声。
晚上,细孙女脱了衣服就往床里头爬。贵奶奶知道,她怕那摆在墙边的老料。从小就胆子小,如今几十岁有细伢的人了,还是这样。贵奶奶拿起细孙女修长的手,凑到眼跟前左看右看,唉声叹气,你要多吃呢,太瘦了。孙女就笑,我都胖得要减肥了呢。
一会子,贵奶奶拿过细孙女的衣服,抚平抚平,又拿起来比对比对,说,太短了呢。细孙女搂着她笑,奶奶,这叫短装。
贵奶奶举头看了看孙女子,短装这个名词,她没懂。过了一会,贵奶奶碎碎念,腰子露在外面,有寒气。仿又记起了什么,捞起衣服往裤腰带上摸索。细孙女更加好笑,捉住她的手贴在脸上,奶奶,我有钱,我也带了好多衣服。孙女问,奶奶你冷不,你的手才凉呢。
没阳气的手呢,要进土喽。贵奶奶哼哼着说。她的手有骨没肉,又冷又硬,布满老年斑,谁还能看出这是以前被她娘老子骂“不沾阳春水”的手呢。
天气有些回暖,田里四处都是青蛙叫。青蛙叫,好犁田。德贵每天都在田水里滚,半夜三更他睡不着,提着马灯到田里看水,看稻子抽穗扬花。他种的稻谷,穗长浆多粒大。一些低产户说,土地老爷是德贵屋里亲戚。
贵奶奶在一团黑里无声地笑。她的菜园里,辣子正结得驮断了树,黄瓜长得像丝瓜,南瓜到处滚,冬瓜就干脆像一个个年画上的胖伢。老柳下的饭桌上,菜都用海碗装。菜少一点,贵爷爷就会置气,推碗扔筷的,你这个婆婆子,小里小气,连个菜都舍不得炒。
贵奶奶手往细孙女身上摸,往上提了提被子。细孙女好一阵子没做声,应该是睡着了。
日子像灶膛里烧湿柴,烟子把眼睛都薰瞎,才好不容易红火起来。贵爷爷和贵奶奶打算翻新屋。那是村里第一个红砖瓦屋呢。红墙红瓦,看起来亮堂又让人喜气洋洋。主持祭梁的木匠师傅筛酒祭天、祭地、祭八方神灵,将鸡血洒于大梁上点光。瓦匠扛梁登梯,一登一祝:下有金鸡叫,上有凤凰啼,此时正上梁……围观的众乡邻连忙齐声接口彩:子孙发达,富贵满堂。
笑声滚动,贵奶奶咧开了嘴。那是瓦木匠将准备好的“梁粑”、糖果、香烟往下撒,大人兜起腰围巾接,细伢子趴到地上抢,闹成一团。
孙女子翻转了一个身,把手搭在贵奶奶的腰上。贵奶奶又把被子拉上来些,幸福得叹了口气,自己的孙伢不怕和老人睡,不嫌有老人味。
奶奶,这人生到世上,为什么又要死呢?细孙女突然说话,原来她一直没睡着。贵奶奶啐骂了她一句:鬼妹子,你吓人呢。
你和爷爷再苦再苦,也活得劲火喧天。细孙女说话没头没脑。贵奶奶也牛头不对马嘴:活着讨人嫌呢。细孙女抱紧了她,埋着脸,含混地说:你不在了,我们回哪儿呢?
烟雨连绵了好几天。贵奶奶忽然咳嗽得厉害,咳起来不把肠子吐出来不算完。孙女子买了川贝枇杷膏,又用胖大海煎水,喂贵奶奶喝。贵奶奶嘴上却反反复复是这么几句,老了呢,没用了呢,何不死呢。孙女子便哄小孩似的哄,你不老呢,你比我还小呢。洗脸、喝水、拉撒,孙女子都细心地服侍着。隔一阵,贵奶奶就说,你出去玩呢,陪着我没味呢。孙女子又哄,我只喜欢和奶奶在一起呢。贵奶奶便一会翻开孙女的衣服,数数有几层,一会摸摸手,看热不热,在彼此眼中,都是初生的细伢。
贵奶奶要孙女子扶她到阶基上坐坐,看看雨。一对燕子,在屋檐和雨里的老柳间来回穿梭着。孙女子指给她看,屋檐顶上有个圆而小巧的泥窝,不知什么时候筑起来的,里面钻出几只毛没长齐的小脑袋,看到老燕子回来“叽叽喳喳”地叫得更欢。孙女子笑着说,小时候,吵着要爷爷捉燕子,爷爷说家燕不能捉,就搭个楼梯把我送上去,让我看一看摸一摸,那老燕子冲过来就啄了我一口。
贵奶奶枯土似的脸上便也浮起一层水亮的光,说那是家燕护崽呢,连命都不要的。贵奶奶歪着脑壳,默神一阵,又说,你们老小尽做些顽皮事。
细孙女又说,小时候,这样的天,你和妈妈在灶屋里一个剁猪草,一个煮猪潲,一屋子的白气,只看得见人影子,成仙了似的。然后你从那白气里出来,变戏法样拿出一只刚煨好的红薯。那是埋在瘪谷子里做种的陈年红薯,煨得金黄,糖多得流了出来。两个姐姐争多,哭闹打架,你老人家收拾不了场。妈妈也从白雾里出来,一个一板屁股,最后红薯都归我吃了。
贵奶奶张着空洞的嘴笑,笑着笑着就一阵猛咳,孙女子急忙搀扶着拍她的背。看阵雨,两祖孙又沉默了一阵。孙女子期期艾艾小声地说,奶奶,明天我就要回去上班了。
第二天,天放了晴。孙女给贵奶奶洗帐子、被单,刷坐便器,忙了好一阵。等孙女子忙清,贵奶奶就要她扶她进屋,打开一个柳木箱子。箱子里端端正正摆着一套“蓝衫”,还有寿鞋寿帽。孙女子吓了一跳,问奶奶你这是做什么?贵奶奶说,晒晒,春上潮湿,怕长霉。
孙女子不敢拿,贵奶奶便要她拿了个楠竹筛盘来。贵奶奶在筛盘里垫上一层白布,把“蓝衫”摊开,寿鞋寿帽摆好。贵奶奶做这些事的时候,轻手轻脚,脸上又浮起一层说不出的光,很洁净的光。贵奶奶吩咐孙女子端到院子里,置在那个水泥砌的洗衣板上。目光牵着,唯恐有什么差错。
这种衣物,因为避讳,也因为贴身穿的为白色,外边的是蓝色,村里人都称之为“蓝衫”。按村里规矩,“蓝衫”归做女儿的置办,父母双亲上了六十以上,女儿就该考虑这些事了。这似乎比在世上时的吃穿更重要,若做女儿的没放在心上,父母就会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地提醒。世道不同了,现在也有去街上买现成的。贵奶奶硬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制了出来,男女式样各一套,男式为对襟,女式为侧襟。
吃了中饭,孙女子又帮贵奶奶洗了个澡,交代好继妈帮忙收“蓝衫”、帐子、被单等。儿子发动摩托车,送孙女子去镇上搭长途车。孙女子提着行李爬了上去,喊了一声“奶奶”就别过脸去。摩托车扬起一道尘烟,“突突”地走了,转瞬就不见了影。贵奶奶弯腰干咳,头发散落,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这院子里依然充满阳光,依然有风在老柳的枝叶间穿梭。这满院的阳光把那柳照绿了一年又一年,把贵奶奶满头黑发照成白发,把满院的笑声照成空寂的光阴。
太阳快落山时,儿子帮忙收拾了“蓝衫”,帐子被单却扯也扯不清,只有喊女人来帮忙。女人叽叽咕咕说着一连串话,虽是叽叽咕咕,贵奶奶也能零零碎碎听到几句。
孙女子打堆,还不是晃个影就走了。
你娘命长,命硬,看你活得过她不……
贵奶奶对柳说,以后的日子都是他们过,继媳妇只是嘴巴差点,声气大点,爱打些牌,其他也没什么,总比儿子一个人老了没人做伴要好。
接下来又是一个夜晚,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夜晚。夜半,贵奶奶慢慢地挪下床,打开柳木箱子。儿子收得马虎,她把“蓝衫”一件一件地掸开,再齐整叠好。
女儿先她而去。就在那几年,女儿、贵爷爷、媳妇挨着个地先后离她而去。女儿是重度感染血吸虫病。媳妇是子宫癌。贵爷爷是食道癌。贵奶奶后悔不该把女儿嫁到那个农场,那是血吸虫病最厉害的地方。贵奶奶后悔不早点提醒媳妇去检查身体。贵奶奶后悔每天给贵爷爷泡滚烫的茶水。日子里的因果,似乎并不遵循她信奉的善因善果,她便相信命数,把罪孽都揽到自己身上,是自己吸了他们的阳寿。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一丝一丝的痛楚游过残年。
送亡灵,路上行,
桥头柳啊,莫挂心,
三关六朝盘问你,
你是阳间的贤德人……
夏天来,柳色浓郁,却生起了虫。虫子摇头晃脑,牵起长长的丝,吊在空中,让人心惊。贵奶奶想要儿子施点药治治。但正是双抢时,儿子没放在心上。贵奶奶饭量越来越少,渐渐地吃一餐不吃一餐。儿子和继媳妇每天都在忙,没忙就在牌馆,也没注意她这些。贵奶奶神气一天比一天委顿黯淡,脑子也越来越不清白。会看相的人道得平常:油尽灯枯。
双抢收的稻谷,放在场院里晒。继媳妇总是嘟嚷着这老柳讨嫌,不仅生虫,还挡太阳,砍了算了。继媳女还说,别个屋里都把屋前屋后的柳砍了,换成了速生六九杨,隔两年就砍掉,卖给纸厂。
儿子起先没做声,他是在这柳下滚大的,以前爷老子年年修剪枝条,打药防虫,从没人说过要砍掉。但耳朵被聒噪多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就有些招架不住。原先,他没这么软弱的,每天衣服袜子总会有人清好摆到面前,饭端到手上。如今年纪老了,不仅勤快了,脾气也好了,老了老了,有一个暖脚的,心里就不会空。
老柳就这么被锯掉了。拉大锯的声音,来来回回。
那天,贵奶奶几乎只能卧床了。
待到天气转凉时,贵奶奶精神头似乎又好了些,人也清白了些,饭又吃得多点了。
贵奶奶从床上起来,还喊继媳妇帮她洗了个澡。继媳妇在倒洗澡水时,“呯呯呯呯”,谁都听得到。村里人说,这个老鬼,命真的硬。
这天晚上,贵奶奶睡下。因为洗了个澡,好像把一身的尘屑洗净,身子轻便得不得了。夜深时,似乎有一抹淡雾从身体里飘出,往上越过房梁,越过幽暗的云彩,穿过一道惨白惨白的光。
贵奶奶进入了柳林,有歌声从柳林深处传来。她盛了些饭菜,用柳条篮子装着,盖上一块手巾。歌声在林子里缠绕,她向歌声走去,给唱着歌放牛的人送饭。那歌应该是他自家那边的山歌,他靠在那棵柳树上,忘情地唱。他到她家做长工两年多,还从没唱过歌。他总是一副憨笑的相,大概就像他自家那边的山。贵奶奶从未出过这个平原,没见过山真正的样子,听了这歌从他嘴里唱出来,便想,这山应该不净是石头,还跟这个柳林子一样,花花草草逗人爱,杨柳丝丝惹人缠。
贵奶奶继续往深处走,忽然就听到一声喊:章雪柳,你这个砍颈的,快回来哟……
贵奶奶落气时,匆匆赶回来的后人围了一屋,她再不能睁的眼睛缓缓流下泪来。孙女子们自然是要哭的,哭得肝肠寸断。那些细伢却什么都不懂,只觉好玩。细伢好奇,问姥姥为什么穿的是那种衣服?脸上为什么蒙着白布?姥姥为什么要睡在那个匣子里?这些问题,大人也不能回答,望着细伢鲜嫩的脸,忍不住发了笑。乡邻反复地说往日的好处,说这个婆婆子一辈子顾后人,怕天气热,后人难办事,硬是要等到天气凉快了,才走呢。
道场照例做起来了。出丧前的那天晚上,满天的星子默默低垂,平原上夜歌子牵牵绕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