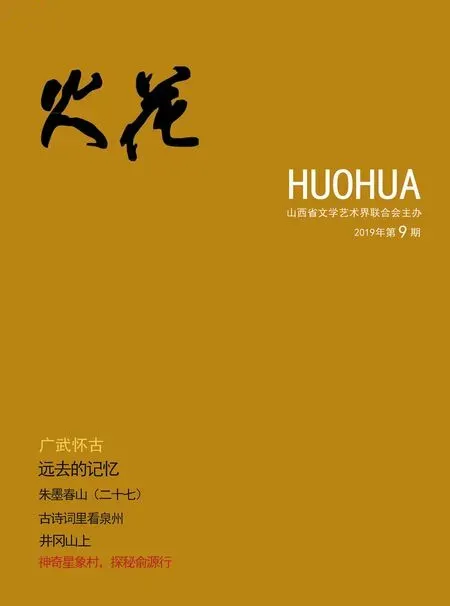老屋,母亲
傅友福
一
回家?多久没有回家了?记忆的存储器里没有半点印象。还好,下了决心,终于可以抛下一切杂念,回家了。
快到家门口,突然有种少小离家老大归的痛苦。
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套用在现在的家乡,似乎合适的。萧条一词,又在脑海中闪现。
是故乡陌生了我,还是我疏离了故乡?此时,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歪论,也突然横亘在我和故乡之间。
值得庆幸的是,我开始用有限的脚步,丈量故乡的孤寂和宁静。
听说我要回来,母亲早早地等在家门口。晚风轻拂,龙眼树下,母亲的银丝随风飘动着,她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眺望着远方。
看到母亲,心中陡然地悸动一下,想说什么,却一时得了失语症似的,没有说出口。本来这次回来是要在新盖的楼房里住下,在外奔波这么多年,房子就是自己身份的象征、成绩的总和。有人说那是归属感,房子一至三层,虽然比不上有钱人家的别墅富丽堂皇,但总算可以摆脱昏沉的老屋,离开那肮脏、破旧、老朽的老屋。可母亲说新房子刚装修,有种难闻的味道,对孩子不好,所以一家人只得暂时委屈在老屋里。
接过我行李,母亲的步子有点蹒跚,八十高龄的她,经历过无数的人世沧桑,确实是老态毕现了。她就像一部机器,经过了中修和大修,如今正费力地延续着生命。我的眼睛一时定格在母亲身上,眼角潮湿的,心中浮想联翩。
这时候,我突然惊醒起来:我有多少年没有这样近距离注视或直面过母亲?为什么我会把母亲给忘了?是不是很多在外面奔波的人,都是这样无视自己母亲的存在?眼前这位老者,难道就是生我养我育我的母亲吗?还有多少人,都有这样的健忘症?
是的,在外面奔波多年,为了生存,为了生活,我早就练就了处世不惊遇事不乱冷漠看待世间人事的铁石心肠。与此同时,我也忽视了母亲的感受,虽然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我什么,或者埋怨我有时候一个月不和家里通一次电话。
母亲是老了,虽然还没到老态龙钟的地步。但从她吃力地提着行李的手,我知道,母亲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人了。
“砰”的一声响,我的头部碰在了老屋的门眉上了。“小心点,这门眉都快让你碰掉了。”母亲说着,马上让我蹲在地上,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部,并用嘴猛吸我的头部,她说这样伤处才不会淤积着,才能活血,减少疼痛。
母亲的这动作小时候曾经多次经历过,顽皮的我没少磕磕碰碰的,而每次母亲都是以这种方式给我疗伤的。
母亲猛吸了几下,还不放开,我一直告诉她,没事了,她才放下心来,进厨房泡茶去了。
望着母亲的背影,泪水模糊着我的双眼。我抬头看着老屋,唉!老屋也老了,老得让我认不出她本来的面目。
二
老屋是典型的闽南式皇宫,我们闽南一带的民居称作“厝”,其中有一种就是模仿“皇宫式”的建筑风格建造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结构的房子。这边的古厝,座座屋脊高翘,雕梁画栋。古厝门前的墙砖上刻有石浮雕,庄严厚重;窗棱上镌花刻鸟,装饰得巧妙华丽;门墙厅壁上有名人书画点缀,篆隶行楷,水墨丹青,各具韵味;匾额有书、卷、扇、菱等,别具一格;门窗有圆、拱、菱、方等,形式多样。随处可见的木雕、泥塑、砖雕及石雕,工艺精美,多数采用透、浮、平雕等手法。雕刻内容丰富多样,有禽兽、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图案古朴。古民居精美的雕饰,不仅集中表现了闽南成熟的雕塑艺术,而且反映了受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南洋文化和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可以算作是闽南建筑的大观园。同时古民居以其宏大的规模、严整的布局、精美的雕饰、丰富的内涵,又被誉为一座地地道道的清朝闽南建筑博物馆。
可是,这种典型的建筑风格,近年来也开始在闽南大地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情感的钢筋水泥楼房。
我家的老屋据说是二百八十年前,由族中在南洋谋生的六兄弟共同建成的。纵观她的布局,仍不失当年的威风和富足。可老屋真的老了,老得让我产生很多陌生感。天井里的板石破碎了几块,周围的石缝里长出了不知名的杂草。上厅的木板也破烂不堪,房顶上的瓦片更是破碎了许多,一旦下雨,就会滴滴嗒嗒漏下水来。斑驳的木柱子上,让白蚁蛀得千疮百孔,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似的。柱子上的油漆对联,也残缺不全了。我真的怀疑自己,我就出生在这儿吗?
三
母亲看我对着老屋发呆,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我:怎么,你回错家了?
不,没有,妈,我不是这意思,只是感觉她老得让我认不出来了,所以,就觉得她有点陌生感了。
那是,她总会老的,是不是我对你来说,也有了陌生感?母亲叹了一口气。
母亲没有上过几年学,说的话却很有哲理。
没有,我没那意思。
母亲叫我到偏房门前的木交椅上坐着喝茶,她那爱怜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我们身上移开。
这把交椅是清末留下来的老旧式黑漆交椅,坐在交椅上喝茶,脑海中马上闪现出先祖们坐在这把交椅上指点江山的情景。茶叶是用老屋的那口老井水泡的,清甜可口,纯洁自然,完全没有城里自来水那股难闻的味道。母亲介绍说,老屋这口井,几百年来养育了一百多个诞生在这儿的父老乡亲。虽然她也老了,可她的清泉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奔涌着。
母亲是1957年夏天嫁入我家的。据父亲在世时闲聊说,他只用三元钱,就把母亲“骗”到手了。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母亲怀上了大姐。当时,二十二岁的母亲没有学识,粗手大脚,是典型的大山女儿。
记得我家有个红木箱子,箱底下有一本母亲珍藏许久的《识字课本》。小时候,我曾经看见过母亲会偶尔翻出来看一看,继尔从母亲的口中传出一声轻轻的叹息,然后母亲又用红布包好放回原处。我不知道母亲这声叹息中蕴含着什么深刻的内容,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这本《识字课本》,凝聚着母亲大半生来对文化的追求,以及记载着母亲追求知识的苦与乐。
那个时候,村里正兴办民校,身怀六甲的母亲很想在孩子出生之前学点知识。她知道,这样对她以后带好孩子是很有帮助的。当母亲羞羞答答地把这个想法跟奶奶说后,奶奶竟一口回绝了。没有学识照样可以生儿育女,“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奶奶的“明智之言”。母亲当下没话可说,也不敢反对,但她对于识字的渴望,却与日俱增。有一次,趁奶奶串门不在,竟腆着大肚子走到民校的门口。看着启蒙教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母亲兴奋得差点跳起来。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大肚子的母亲时,母亲却羞得赶紧离开民校。
见此情景,人们就在背后说母亲,阿英这人很憨,也可爱。
母亲并不因为人们诧异的目光而退却,去民校的时间更勤了,只是民校没过多久就关闭了。母亲最终不能在孩子出生前学到知识,她感到非常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六年后,乡里通知各村举办扫盲夜校,规定凡是在四十八岁以下、没有达到小学文化水平的村民,都要参加扫盲学习。因此,母亲第一次领到了一本《识字课本》。听大姐讲,那时候母亲干活特有劲,走起路来也是噔噔响的。一旦闲下来了,母亲就捧起《识字课本》,一字一字地读。
可是,这种快乐很快就在母亲脸上消失了。虽然母亲每次也不例外地参加扫盲,可等她到学校一看,大家有的在打牌,有的在侃大山,有的在织毛线。没有人在认真学习,培训老师也不见了,母亲失望地走回家里。后来,大姐对母亲说:“妈妈,倒不如你也别去了,反正去了也没有学上。干脆让我来教您,好吗?”母亲深思片刻,说:“好,你来教我吧,只要不影响你的功课,现在就教!”
母亲的识字进步很快,大部分农作物、家具、都能倒背如流。母亲甚至于对汉字有着无限的崇敬,她很认真地对汉字的组成进一步深入了解。可是,好景不长,大姐升学入高中后,学习相对紧张了,能用来教母亲识字的时间也少。母亲只好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
本来母亲还是想挤出一点时间来学习,至少可以自学。可父亲突然英年早逝,家境变得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只好再次放弃。丧夫之痛使母亲再也提不起学习的勇气来,那本《识字课本》被她用红布包起来,放在箱底。红布包上面残存着斑驳的黄点,那就是母亲伤心的泪痕啊。
1974年,四十八岁的父亲由于得了脑溢血,在医院里呆了一天后,就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去世了。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没了父亲,这个家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要抚养五个大小不一的儿女,还要在那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让五个儿女健康成长。记得那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闽南地区对夭寿而死的人的三天守孝期一到,就让我们兄妹五人继续上学去。大哥不同意,他说他有十六岁了,能帮她干点农活,不想上学,要在家里帮母亲。母亲不同意,大哥不听话,母亲出手打了大哥。打过之后,又抱着大哥对着父亲的墓地的方向泪如雨下。大哥只好听从母亲的话,乖乖上学去了。就这样,母亲不得不起早摸黑,除了侍弄好几亩责任田外,还要抽出时间编织草席(草席是我们老家的特产),以便换来零钱,供儿女上学的学费和家里的油盐等开支。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未有一餐准时吃饭,等到我们吃饱了,锅里也只剩下“对影成三客”的米汤了。
母亲穷,且憨。大山养育着她坚贞不屈的性格,也让母亲从小就认识了很多治疗一些头疼脚疼的草药方子。很多有求于母亲的乡里乡亲也早就知道母亲有这一手绝活,于是,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上门求要,母亲就会打着灯笼出门而去。当时生产队的农活那么忙,母亲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她这一习惯却从没有改变过,且从不收取他人一分一毫。这也是母亲憨于他人之处。
母亲更憨的是事儿,还在后头。当时,我们村经常有走村串户的货郎。这些货郎外出的时候,经常带着干饭中午吃。如遇到好的人家,会帮他热一下饭。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母亲只是帮人家热一下饭,我们也没话可说。她总是另外给货郎炒一个好菜,或者用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咸肉,为货郎炒菜。我们站在一边看也不行,她说这样对客人不礼貌。每次我们只得流着口水,端着红薯稀饭,远远蹲到墙角下,不时还用小眼睛偷偷看着桌上的菜肴。
自己没钱找人借钱,以应他人之急,也是母亲之憨的一种。父亲去世后,家里的余钱少之又少,少许的几个钱,是母亲和大姐编草席换来的。可一旦有人向母亲开口,家里没有也要向别人先借,这叫做借他人之钱去借给别人。记得那是父亲忌日的当天,借钱的人是我们村最穷的二呆,没儿没女,一个人过日子。母亲听说他要找个对象,尽管自己没钱,还是找刘大婶借了八十元钱给二呆,还请二呆吃了一餐饭。为此,大哥大姐都说母亲比二呆还呆,这种人借了你的钱,何时能还?
这回,母亲生气了:“谁没有困难的时候?能帮的不帮,那还算什么乡亲?我借给他钱,就是要让他早日成家立业,过上好日子。就算他日后没钱还,他这辈子也会记着咱们的好的。”
简单、朴素的语言,没有生动的教条,却折射出母亲助人为乐的憨厚之心。我们兄妹五人,就是在母亲简单而朴素的教育之下长大成人的。因为,母亲早早就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谦虚谨慎、乐于助人、努力向上的种子。
我也曾好几次想重新点燃那蕴藏在母亲内心很久的向往文化的火种,但当我面对早生华发、饱经风霜而过度苍老的母亲,我的念头又很快被打消了。母亲太苦了,不敢让她再增加这种额外的负担。
憨厚的母亲已经老了,她那日渐孱弱的身体再也经受不了任何刺激。我为母亲的不幸感到无限的悲哀。母亲天生的憨厚,母亲天生的睿智,不可能被归类为没有文化的行列。
突然间,我一下子醍醐灌顶了:想想母亲对一家人的贡献,其实,母亲早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了,而她那在生命晚风中飘荡的银丝,不正是母亲文化的精华吗?
四
母亲看到我还在发呆,就跟我唠叨起曾经居住在老屋的人们。老屋本来有七户人家,目前除了独身的老歪叔和老二婶,再也没人居住了。寂寞的老屋也似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静静地座落在那儿,无言无语,风霜雨雪从不动摇。她在等待命运对她的最后宣判。
母亲又说歪叔可怜,七十多岁的老人,身边无一男半女的,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更可怜的是老二婶,四个儿子都盖了新房子,可她却孤独一人住在老屋里。“他们怎么都这么狠心呢?”母亲说的他们我知道是谁,虽然不是说我们兄弟,可我总感觉母亲是否话中有话,影射我们呢?
老屋是老了,老得没有人理她,似乎谁都忘记老屋曾经给过我们的诸多好处,也曾经养育着我们。我们儿时的欢乐、年少时的憧憬、成年后的成功,难道说没有老屋的滋润吗?
母亲也老了,老得快走不了路,可我们依然在外面奔波,依然故我地为金钱、为名利、为地位而忙碌,在人生的道路上驰骋着。我们也只是认为每个月准时给母亲汇了钱款,母亲有了钱花,就算是尽孝尽职了。目前,我们兄弟也都盖了新房子,是让母亲住进新房子,还是让母亲和老二婶一样,让她终老在老屋里?
一想到这儿,我的头部突然发麻起来。总有一天我也会老的,如母亲一样,可我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
对了,该打扫一下老屋,我可是从这儿出发,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的。
于是,我叫来了妻子,一人一把扫把,从老屋的大厅开始,认认真真地打扫,这也是老家年前的除尘习惯。除掉了尘埃,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我觉得这习惯得告诉儿子,让他们也要保留这种习惯,一代一代传下去。
当天晚上一家人睡在老屋里,我突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