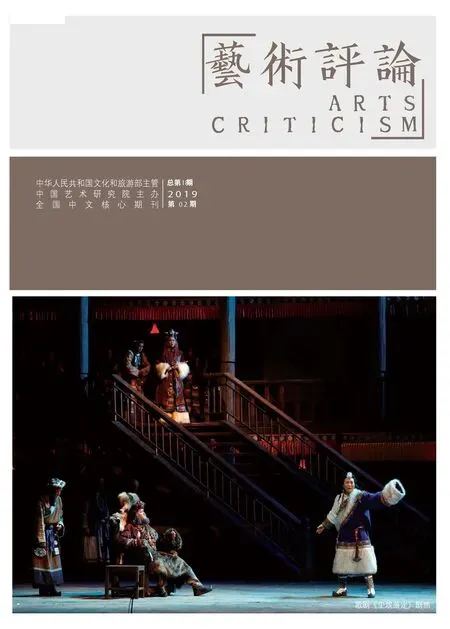抽象与“后抽象”[1]
何桂彦
在讨论“抽象”与“后抽象”之前,一个关键的前提,是我们在怎样的语境中展开。换言之,什么构成了讨论它们的艺术史情景?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不能绕开西方抽象艺术及其形成的艺术史谱系;第二,离不开中国抽象艺术自身的本土逻辑;第三,与抽象艺术相关的批评话语、理论体系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学理依据、评判标准是什么。
马奈、塞尚、毕加索、蒙德里安等呈现了西方抽象艺术基本的发展轨迹。开端始于马奈,比较后面的代表艺术家一个是莱茵哈特,一个是斯特拉。为什么马奈是西方现代艺术的起点?这与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的批评体系有关。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抽象艺术的内部发展结构已非常严密。在今天的欧美,它已经被奉为经典,也被学院化了。
就它整个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早期抽象、盛期抽象,第三个阶段是“反抽象的抽象”或“观念性抽象”。那么,这三个阶段的艺术史逻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与抽象艺术的创作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关于早期的抽象艺术,其最重要的话语之一是源于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早在1825年,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圣西门就谈到了政治的前卫。与此相伴而生的另一个概念是审美的前卫。政治前卫与美学前卫,如果与艺术领域联系起来,就在于打破既有的艺术创作观念与学院模式。我们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是追求艺术本体的独立,实际上,倘若没有19世纪中期的“为艺术而艺术”,抽象艺术就缺乏孕育的艺术与文化土壤。这个问题反过来说,为什么18世纪、17世纪没有出现抽象艺术?很显然,抽象艺术是需要土壤的,然后才是审美观念的革命。这个土壤就是西方伴随着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化,观念的革命则源于启蒙运动以来所掀起的批判意识。其中关键的思想是文化反叛与个人解放。除了圣西门,这种思想在德国、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中表现得也十分强烈。19世纪中期的时候,法国的波德莱尔是关键,他对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倡导,以及对马奈等艺术家的支持,为美学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艺术本体的范畴,为早期抽象艺术铺平道路的是对“平面性”的追求。所谓的平面性,感觉上十分简单,但在理论与观念层面,它所意味的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一个二维平面描绘表象世界的整套话语体系的失效。从意大利的布鲁内莱斯基发明透视,以及在二维平面以视错觉为基础所构建的观看与视觉机制,在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坍塌。换言之,如果平面不走向独立,就意味着抽象艺术没有起步的根基。第二个是追求反叙事性。在19世纪中期以前,几乎所有的西方绘画都追求叙事性,也即是说,是有故事的。同时,绘画为政治、为王权、为赞助人服务。当然,“为艺术而艺术”并不必然会催生抽象,但假如没有对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追求,抽象艺术同样不可能产生。
有了上述两个基础,就为“有意味的形式”创造了条件。从英国的罗杰·弗莱,到美国的格林伯格,再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兴起,在抽象艺术的谱系中,形式——结构批评是最为重要的脉络。甚至,形成了形式批评为主导的现代主义批评传统。在1908到1910年间,对现代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沃林格,当时他的《抽象与移情》一书出版,曾对德国艺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下来是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他两人私交很好,学术思想也有相同之处。20世纪初,形式主义批评为早期抽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但是这个时候的抽象有一个特点,它与盛期现代主义的抽象最大的区别,在于艺术家在创作时,还无法离开一个具体的“物”。这个“物”既可以是静物,也可能是风景,也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所谓的“抽象”,就是艺术家对所画对象进行概括,使其抽离出来,转化为“有意味的形式”。弗莱在20世纪10年代为塞尚辩护,也是这个原因。今天,中国大部分抽象艺术家的作品,或者他们所理解的抽象,大多仍停留在早期现代主义阶段的认知与审美观念上。
第二个阶段是盛期现代主义抽象,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家是波洛克、德库宁、罗斯科这代人。在这里,我想提及两位批评家,一位是格林伯格,一位是罗森伯格。他们是同时代的批评家,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重要推手。但是,这两位批评家的批评话语完全不同,格林伯格是形式主义,而罗森伯格则认为是“行动绘画”。1952年,罗森伯格发表了著名的“行动绘画”一文,认为抽象的形式只是“行动”的副产品。换句话说,艺术家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作的行为,以及“行动”过程释放出的解放性。这种批评话语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想有密切联系。在这两位批评家之前,还有一位重要的批评家与艺术史家,他是迈耶·夏皮罗。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夏皮罗的观点对格林伯格,以及当时的美国艺术界曾产生了影响。其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当时的转变。1936-1939年间,因为斯大林在党内的“清洗”,导致了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失望,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幻想。这个转变对抽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1936年的时候,夏皮罗有一篇文章,讲的是《艺术的社会基础》,当时的艺术看法仍然是支持现实主义的。但在1937年,他的观念产生了急剧的转变,明确地支持抽象艺术,这在《抽象艺术的性质》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再有就是托洛茨基《创造自由的革命艺术宣言》产生的重要影响。通过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抽象艺术与左派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另外还有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是纽约现代艺术馆的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1936年的时候,他策划了一个现代艺术展,目的是希望将欧洲的现代艺术带到美国。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抽象艺术已经有了存在的土壤。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抽象艺术怎样才有自己的特点?与欧洲拉开距离,或者如何才能建立自己的表述和话语权?因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批评中,一些核心的批评话语已经形成,如“行动绘画”“大画幅”“色域”“无中心”等。当时,摆在格林伯格这代批评家眼前的任务,是怎么超越巴黎的现代艺术,让纽约成为欧美现代艺术的中心。故此,对于批评家来说,就需要提出新的批评话语,并给予新的抽象艺术以理论支撑。就格林伯格而言,也是他最大的贡献,不是提出了几个概念,而是通过形式批评——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将美国抽象表现纳入到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整个现代艺术的发展谱系中。他的观点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形式简化,一个是自我批判。简单地理解,在他看来,抽象艺术发展最为内在的逻辑是形式的不断简化,而且,其遵从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也即是说,后来的一定比此前的高级,而且形式表达会更纯粹。稍加思索,会发现这个逻辑是很难成立的。关键的地方,在于格林伯格为“形式简化”赋予了合法性,因为他将其与西方的现代哲学联系起来,而这个哲学的根基来自于西方的理性批判传统,这集中体现在康德的思想中。亦即是说,只要西方现代文化继承和推崇理性批判的传统,那么,抽象艺术就始终会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而形式的不断简化正是理性批判的外在显现。对此,格林伯格在1962年的文章——《现代主义绘画》中作了深入的讨论。按照他的理解,西方的现代主义抽象,发展到最后,会出现一张空白的画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幅抽象画,尽管它可能不太完美。假设以中国艺术教育的思维,或我们对绘画的既有认知,是根本不会同意格林伯格的批评理论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艺术发展并不遵从所谓的内部批判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重视美术史的语境与线索,不断以“新”的来取代既有的创作范式。
在形式批评——现代主义的批评理论体系中,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不仅战胜了欧洲,取代了巴黎的地位,而且形成了自身的话语权。同时,在这个话语体系中,还蕴藏着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前卫、原创性、精英意识、白人男性的优越感等。这也就是盛期现代主义抽象的特点。到这个阶段,抽象艺术家不再需要面对一个表象世界,不再需要有一个再现的对象,相反,完全可以依靠形式去构筑一个自律的抽象世界。这套话语也成就了现代主义的个人神话。当然,这个体系也存在隐患,如果按照线性进化的方式不断向前发展,当一幅空白的画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幅抽象画的时候,必然就走向了极致,根本无法再向前推进了。所以,迈克尔·弗雷德在1966-1967年间曾与极少主义有过交锋,有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并且坚持现代主义一定要消灭材料的“物性”。他认为西方现代绘画仍有发展的空间,但绝不是走格林伯格所指出的道路——形式简化,相反,是沿着既有的规范与惯例向前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抽象艺术界普遍有一种焦虑,就是发现,抽象艺术几乎很难再向前发展了。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所说的“反抽象的抽象”,也可以理解为观念性抽象。它的运作逻辑是怎样开始的呢?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格林伯格的理论和现代主义体系釜底抽薪的是极少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极少主义艺术家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是推崇的,但1966年前后,他们走向了反面。尤其是极少主义向后极少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全新的抽象话语,即观念性抽象。在极少主义之前,还有两位反现代主义抽象的开拓者,一个是弗兰克·斯特拉。早在1959年的展览中,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黑色绘画》。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对于自己的作品,他反复强调,这些形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形而上的思想,更不是个人神话。那么,斯特拉到底想做什么?他是怎样思考抽象问题的?实质上,他要针对的就是盛期现代主义,就是波洛克、德库宁等所推崇的抽象形式中蕴藏的精英性、原创性、崇高感。斯特拉要粉碎的就是抽象艺术构筑的个人神话。但是,悖论就在于,斯特拉的作品仍然保留了抽象艺术的外观。这是一种新型的抽象吗?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反形式的形式主义,一种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观念性抽象。另外,还有一位艺术家,他是莱茵哈特。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新学院主义的十二准则”。什么是绘画?它应该是无肌理、无笔触、无形式、无构图、无明暗、无空间、无时间、无尺寸、无比例、无运动、无对象的。莱茵哈特所要针对和破坏、颠覆的仍然是现代主义的整套逻辑。新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真按这种说法,不仅抽象艺术,包括绘画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死亡。
在理论上对形式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理论做彻底否定的是批评家罗莎琳·克劳斯,她早期曾是格林伯格的追随者。她认为,支持西方抽象艺术的现代主义叙事的失效,根源是——“格子”。格子导致了现代主义体系的坍塌。事实上,现代主义体系最核心的思想,是认为形式的自律可以捍卫主体的自治。什么是“形式自律”?简单地理解,是认为抽象艺术家作品中的点线面,完全可以构筑一个新的、自律的精神世界。然而,克劳斯却说,其实我们都被骗了,是格子为这套话语提供了支撑。因为,在她看来,在西方绘画中,自从透视主宰了二维平面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格子”为中心的视觉与观看机制。在这个系统中的艺术家几乎是集体无意识地就会受到这种视觉习惯的支配。在克劳斯的理解中,格子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叙事的原罪。因为格子是自律的、封闭的,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正是这种排他性,成就了现代主义的神话。20世纪70年代恰好也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时期,所以,克劳斯十分坚定地认为,是“格子”欺骗了观众。以克劳斯的批评理论为标志,形式主义批评进入了后结构主义阶段,自此为止,已完全背离了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道路。
于是,抽象还有可能吗?这是20世纪60年代那代艺术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批评家来说,既然格林伯格的理论已经失效,那么如何形成一套新的批评话语呢?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批评话语与解释不断涌现。比如,对波洛克的评价,也不再强调其抽象的现代主义特征,而是从身体、偶发、书写和过程性切入。甚至在一些法国哲学家的评价中,认为波洛克的绘画,实质是一种身体性的排泄,有一些污秽的东西。同样,对日本的“具体派”如白发一雄的解释,就完全放弃了格氏的形式主义,而是将其与东方的禅宗、日常的行动等思想联系起来。包括对Twomply的解释,也是强调个人的、微观的、书写性的因素,甚至将书写、绘画行为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疗伤。不难发现,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观念性抽象之后,批评与阐述理论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有了西方这个背景,现在我们谈中国的抽象艺术与批评话语。当然,中国抽象的评价与价值尺度肯定来源于本土的文化立场与艺术史上下文。也即是说,我们自己的梳理与阐述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西方。刚谈了那么多,并不表示我完全认同西方的批评理论,更不是拿这套理论来评价中国的抽象艺术。而是说,在一个国际化的语境中,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西方的理论就放在那里,是无法回避的。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有很多批评家参与到抽象的展览与批评话语的建构中,譬如高名潞、栗宪庭、李旭、易英、朱青生、王端廷等等。我的问题是,像高名潞、栗宪庭,他们对抽象艺术最大的推动是什么?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栗宪庭的《念珠与笔触》并不能代表中国抽象艺术的全部?而高名潞的《极多主义》是否会狭隘,是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不是我现在要去讨论的,相反,我想说的是,2003年,通过上述两个展览,两位批评家都提出了新的评价中国抽象艺术的批评话语。对于中国当代抽象的发展,实质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让我想起了意大利批评家奥里瓦先生。2010年,他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策划了《伟大的天上抽象》。奥里瓦曾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出过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集中的一次展现,是他负责策划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奥里瓦上一次来北京,尤其是通过这个展览,给予中国的抽象艺术很高的评价,并且给展览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伟大的天上的抽象》。我反复读了奥里瓦的展览文章,后来也写了一篇评论。虽然奥里瓦是意大利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曾成功地推出了“超前卫”,提出“文化游牧”概念,但当他在评价中国的抽象艺术时,除了由衷的赞美,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是他的整个评价标准都是西方的,更准确地说是格林伯格的。按照这种逻辑,即便他高度地肯定中国的抽象艺术,无非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原有的谱系中,增加了几个中国的抽象样式而已。这是需要我们冷静反思的。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因为知识背景与文化情景的不同,奥里瓦的解释难免有局限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抽象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遮蔽,甚至有完全被误读的危险?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抽象艺术做过什么?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形式美”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抽象。这个阶段的任务简单、明确,打破僵化的一元化的现实主义体系,让艺术回归审美、回到艺术本体。然而在后来抽象却率先遭到批评。所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抽象艺术绝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换言之,在那个时期,选择抽象,就意味着艺术家选择了反叛。并且,美学前卫或反叛的背后是蕴含着社会态度的。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像上海的艺术家余友涵、丁乙,北京的孟禄丁、马可鲁,四川的王川、朱小禾等等艺术家,都创作了抽象风格的作品。这个阶段正好是“新潮美术”时期。当时抽象艺术的主要任务,是形成个人的风格和建构现代主义的范式。然而,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新一轮中国的改革开放,于是,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下,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迅速式微。实际上,“新潮美术”只有短暂的四年,尽管时间短暂,但任务着实很多,既要推动思想启蒙,又要完成语言变革,甚至还要追求与西方同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出现了,就是社会学叙事和审美叙事的砥砺与对抗。这种矛盾最突出的体现,在于“时代需要大灵魂”和“纯化语言”的拉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大灵魂”最终胜出,甚至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纯化语言”就失败了。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当社会学叙事具有绝对主导的时候,推崇现代主义语言变革的抽象无疑就会处于边缘。从这个角度讲,“新潮美术”的谢幕,已将抽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没有完成自身的现代主义的革命。而这一点也是中西抽象艺术最大的区别,也是中国的抽象不能进入第三阶段,即“反抽象的抽象”最为内在的原因。因为西方盛期现代主义的抽象遵从内在逻辑的推进,是以前卫的立场对既有的系统与范式进行挑战。但是,由于缺乏现代主义的谱系,而且它原本就是一盘散沙,那么你的反击,与既有系统所形成的张力从何而来呢?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抽象在创作上是十分多元的,在媒介、表现、观念等方面都有体现。但在本次展览上,却很少看到抽象水墨的作品。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抽象艺术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水墨领域。比如杨诘仓、张羽、刘子建、王天德、李华生等人的作品。我也想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国抽象艺术至少在语言上可以跟西方同步了。也可以说,中国艺术家有了足够的自信,也有了相对成熟的方法论,可以创作出相对完美的抽象艺术。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时还有一个时间差,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中国的抽象艺术一旦进入国际,在面对西方时,你如何变得强大?如何觉得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在的问题不是艺术家,而是批评家需要面对的了。换言之,中国出现的新的抽象,是需要有新的批评话语予以支撑的。于是,当我们回过头再讨论“念珠与笔触”和“极多主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栗宪庭将“念珠与笔触”与女性纳鞋底结合起来,我也有不认同的地方,但至少,他在用中国的方式为创作予以阐述。譬如,针对高名潞的“极多主义”,尽管批评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极多”背后实质隐藏着西方的“极少”,也有人说“极多”与中国的“都市禅”的结合十分牵强,但是,最重要的地方,在于高名潞是从本土的艺术史逻辑与上下文去构建自己的批评理论,例如,他就特别提出了“极多”与“新潮美术”时期“理性绘画”的关系。就批评话语与原创的理论来说,这两位批评家的工作都是值得尊重的。受他们的启发,2008年,我在北京偏锋新艺术空间策划了“走向后抽象”的展览,也是希望呈现一些不同的、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抽象的作品。
那么,什么是“后抽象”,其实指的是观念性抽象。我举一个例子,以谭平的抽象作品为例,我不是从审美、形式表达的角度去理解的,而是强调这些形式背后的规则,以及创作的方法论。亦即是说,抽象语言背后的生成逻辑才是关键。比如艺术家笔下的覆盖,就是一种典型的观念性表达。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不停地重叠、堆砌,一遍又一遍,时间、过程、身体性体验是重要的,最后观众所看到的只是绘画的遗留物。再比如说孟禄丁的作品,完全消解了所谓艺术家的才情、性格、天赋,因为作品中那些抽象的形式是在“去主体”的前提下,是机械在相应规则的设定之下产生的。有必要补充的是,我所说的方法论,不是简单的庸俗的工具论,而是说,艺术家要将自己的方法、语言生效的逻辑放在既有的艺术史背景中去考量,不断推陈出新。
再有就是立足于传统东方的美学观念,然后做观念性的转换。比如说李华生的作品。其作品的特点,在于艺术家给自己限定了时间,从一天到一个月,由线生成面,让格子不断蔓延。在这类作品中,过程和时间不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画一幅画所需要的自然时间,而是涉及到东方人对时间、对过程的理解,就像佛教中的“日课”,抽象的形式仍然只是创作过程或时间的副产品。再比如说王易罡的作品,在它的语汇和画面结构中,有传统山水的视觉元素,有意向表现的因素,也有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东西,于是,他的抽象涉及到一个新的表现方式,就是对语言的重新编码。通过对语言的解构、重新的组织,自然会改变作品的叙事逻辑。但总体的审美趣味,却又是向东方的回归。
最后,我希望谈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中国的抽象还有多少可能性?即使认为观念性是抽象的出路,那么,怎样才能为作品注入观念。同时,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观念表达的有效性?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如何将作品纳入艺术史的逻辑是十分关键的。前面我们讨论过格林伯格所说的情况,就是按照西方的自我批判,一幅空白的画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幅抽象作品。我再举两个例子。这是邱志杰1993年的作品《书写1000遍兰亭序》。事实上,当他书写到1000遍的时候,最后的作品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件抽象?或者看作是观念性的抽象?同时,不禁会问,这个作品生效的逻辑不就是源于传统的书写性经验吗?再比如说杨诘苍的《千层墨》,最后完成的“千层墨”与早期抽象艺术范畴所看到的抽象画是否有本质区别?很显然,看上去都是抽象,但艺术家从一开始,其创作的方法,及其背后形式运作的逻辑却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差异,就源于观念上的不同。
今天的抽象艺术,正是由于存在中西两个不同的谱系,尤其是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参照系,所以,对艺术家的要求是很高的。我认为,其未来的出路之一就是走向观念的抽象。惟其如此,才能摆脱现代主义意义的形式与风格,在方法与观念的变革中,衍化为一种知识性生产。到那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表象上的内容,或表面的抽象形式,而是生成这幅画的逻辑和话语是什么。到这个阶段,就我个人而言,说明了中国的抽象开始进入到一个“后抽象”时期。
注释:
[1] 2016年11月,上海民生美术馆举办了《中国抽象艺术研究展》和展览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周宪、王端廷、李晓峰、马钦忠等学者参加,本文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2]参见Harold Rosenberg:“The American Action Painters”,Reading Abstract Expression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3]参见Diego Rivera and Andre Breton:“Manifesto: Towards a Free Revolutionary Art ,”Partisan Review, Fall 1938.尽管这篇文章是以迭哥·里维拉和安德烈·布雷东的署名发表的,但实际是托洛茨基完成的。参见:创造自由的革命艺术宣言[J].世界美术.1991(4).
[4]参见Michael Fried:“Art and Objecthood”,Art and Objecthood-Eassays and Review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沈语冰先生已翻译该文,由江苏美术出版社于2013年出了中文版。
[5]〔美〕乔纳森·费恩伯格.1940年以来的艺术——艺术生存的策略[M].王春辰、丁亚蕾译,易英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88.
[6]罗莎琳·克劳斯.前卫的原创性及其他现代主义神话[M].周文姬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6.
[7]何桂彦.奥里瓦的“偏见”[J].东方艺术.2010(4).
[8]参见何桂彦.走向后抽象[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