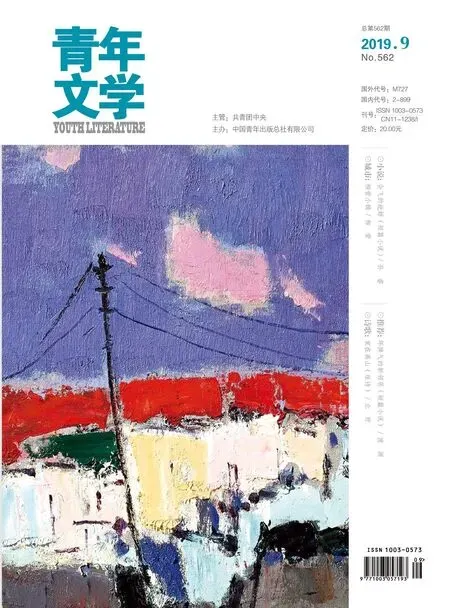旋转的木马
文/柳 营
我八岁那年,她走了。
从此,我和父亲相依为命。
二十多年后,父亲去世。
父亲去世没几个月,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那晚,我在办公室加班,她就那样自然而然地走了进来,像是出门散了会儿步,忘了家里的钥匙,跑来找我取钥匙似的。
她站在我面前,笑嘻嘻的,叫着我的名。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我以为她早就死了。她离开太久,没有任何消息。我真的以为她死了。我曾经非常想念她,夜里也常梦到她。她没给我留下一丁点希望。就像是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不见踪迹。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差不多已经忘掉她了。
如今,她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了,就如当年她离开我和父亲时一样,毫不犹豫,无所顾忌。
第二天一大早,她敲了我的门。
她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没有试探性地招呼一下,就那样堂而皇之地挤了进来。她把我小房间里的电脑、书架统统搬到客厅里。小房间成了她的卧室。
最初,她尝试着要关心关心我。
她给我洗了个苹果。
我从她手里接过苹果时碰到了她湿漉漉的小指头。那瞬间,手与手似乎有了连接和交流,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想,毕竟,我是她生的。我内心一直渴望着能再见到她。
父亲恨她。父亲死了。
我以为从此就如孤儿。
好在,她还活着。
她趴在桌边,看向窗外的街道。她目光停在遥远的某处,发着呆,嘴里机械地咬着苹果。似乎想起什么似的,她转过头来,面对着我问:“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我回。
“工资很高吧?”她又问。
“你知道我住哪儿,知道我在哪儿上班,也应该早知道我的工资有多高。”我回。
她并不在意,继续啃她的苹果。
我希望她能问问自她离开后我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她那个已经死了的男人——我的父亲。
对于这一切,她只字不提。
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对话。
我说东,她说西。
事实上,她对我的生活毫无兴趣。
她住进来后,我以为从此一日三餐可以有热汤暖饭。最初几天,她试着做了几顿淡而无味的晚餐,我提议可以在菜里多放点盐。她见状立马宣布,她最讨厌进厨房。她不仅不喜欢进厨房,也不喜欢多吃饭,她要保持身材。她甚至连我给她买的早餐都懒得吃。
她精心打扮,提着粉色小包,早出晚归。谁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忙些什么。我问过两次,她全当没听到。
她唯一感兴趣的是一次次询问我是否有男朋友。她反复说,女人事业再好,也得嫁得好。嫁人最重要,不能等。女人生孩子更重要。男人七十还可以有孩子,女人不行。她说得非常认真:“我生你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等我懂的时候,我孩子已经独立了。”她笑起来。
她没心没肺似的,当着我的面,一再说:“你应该叫我姐姐。”
每次我在家接完一个电话,她都会神经兮兮地问:“谁呀?”
或问:“这又是谁呀?”
有时直接问:“男的还是女的?”
之后,她会立马告诉我,年轻时快谈恋爱,工作再努力,又有什么用。结婚这件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当大事对待。
我说:“我足够独立,有房有工作,结不结婚,有那么重要吗?”
她搬张凳子坐在我面前:“怎么就不重要了,你难道不想在年轻的时候生个孩子?”
我说:“我早已冻了卵子,不急。”
她大为惊讶:“干吗冻卵子?”
我轻描淡写道:“如果找不到喜欢的男人,年龄又大了,万一那个时候又特别想要孩子,也不至于全然没有办法。反正年轻时,努力工作,多赚点钱才是重要的。有事业才有未来,不然靠谁?靠山山会倒,靠船船会翻。”
她张大嘴巴,脸红通通的,一副干着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有一天,大学男同学从外地来我的城市出差,约着一起吃饭,顺道进家里坐了坐。她刚好在家。她热情地给男生切西瓜,陪他聊天,问东问西。然后告诉他:“我家女儿,心善,喜欢孩子,温柔,会做饭,你看,屋子整理得多干净。谁娶了她,谁的福报。”
男同学看看我,尴尬地笑。
我对她其实一无所知。
多年前的一天。放学回家时,爸爸对我咬牙切齿地说:“那个不要脸的婊子,跟别人跑了!”
我看着父亲,听不太懂他说的话,但知道,她不在屋里,也不知道她何时会再回来。看父亲那凶狠又沮丧的样子,她似乎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心里空荡荡的,突然觉得害怕。父亲满脸阴沉。我不敢哭。父亲不喜欢孩子哭,他会一巴掌重重地甩过来,让人晕头转向,眼冒金星。
晚上睡觉时想她,非常想她。我在被窝里紧紧抱住木马,我的双手湿漉漉的,因为紧张和不安。木马是她在小镇上的一个手艺人那里买的,两块钱,木头刻的。木马只有巴掌那么大,刻得很粗糙,但我喜欢。
她说:“以后带你去骑真的木马。”
有一次她领着我去看电影,电影里出现一个游乐园,小孩子们骑在木马的背上,旋转,旋转,飞快地旋转。他们的笑声那么响亮,衣服那么漂亮。一圈又一圈地转,他们扬扬得意地朝蓝天白云挥手,多么的欢畅,让人羡慕向往。
她说:“以后带你去骑木马。”
小孩子们的笑声,一浪又一浪,那么欢乐。
她走后,父亲几乎不怎么管我。他沉浸在巨大的忧伤里,像木马一样,每天在他沉重的世界里旋转。有那么些日子,他甚至都想不起家里有个女儿。每天放学回家,独自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天渐渐黑下来,我无数次地抬头等着开门声,那门像封住了似的,没人推开它。我自个儿在屋里找吃的,有时实在找不到吃的,就早早捧着木马上床,躲在被窝里哭,哭累了,在寂静得让人惊恐的黑暗中一点点沉进梦里。
总有一片乌云悬挂在她离开之后的生活之上。无论我醒着还是睡着,那片乌云总是浮在头顶。无论我走在哪里,都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噢,她是那个女人的孩子?
嗯,与人私奔!不要脸!没良心!抛夫弃子!
我知道我是被弃的人。是多余的人。
在学校里,我活得像老鼠。同学们不喜欢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远离有娘生没娘教的孩子。娘种不好,孩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的世界没有出口。处处被堵,阴气弥漫。
我如生活在洞穴里,一直野狗般独来独往。
我知道,必须好好读书。每次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大声报出我的成绩的时刻,我知道,我的血液滚烫,我的心脏鲜红。我一回家就做作业,然后洗衣服做饭,打扫房子。我习惯了孤独,习惯了承受,习惯了闲言碎语。
读完小学读初中,考上高中,进了大学。我离过去越来越远,生活在新的城市里,新的空间里,缓缓呈现出另一种景象。
大学毕业,我进了外企。
我比谁都拼命工作。我比谁都热爱学习。我比谁都习惯与孤独相处。
工作后的第六年,父亲去世。
我仍旧一个人生活。没什么特别亲密的朋友,也没有男朋友。交往过几个,虎头蛇尾,就连为什么分手都还没弄明白,便已形同陌路,但我始终相信,有一天,我会遇上真正对的人。
遇不上也是命。
我生活简朴,空闲时喜欢待在屋子里看书看电影。我几乎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彩票倒是必买的。赢家,有时需要的仅仅只是运气。
我得靠自个儿努力撑着全部的现实世界。一个人开门,一个人关门。唯有彩票,可以赌运气。说实话,我从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我的头上,但照买不误。
赢是运,不赢是命。
这话是父亲说的。
自她走后,父亲下班基本不直接回家。他怕回家。他说家里阴气太重。待久了会让他发狂。他得去茶馆泡着,养着虚弱的心气。时常会给我端碗热饭吃的邻居劝他:“她走归她走,女儿是你生的,总得管呀。”
他憨笑,回道:“这屋里,待不得人哪,满屋都是她的影子,晃得我心堵、气喘,若不去茶馆,我早没命了。”
他逃去茶馆,沉溺其中。
他在茶馆不喝茶,只喝酒。茶馆里有说书人。说的内容古色古香。说书人爱用一些奇妙的词汇,“吱吱”“啊呀呀”“托托”。
说书人很老了。以前在上海某个书场门口补鞋子,一字不识,听了一辈子的故事,故事在他的脑子里生了根发了芽,活了起来。老了,回到小镇,在茶馆里当起了真正的说书人。
如今说书人早已去世,茶馆也塌了,在旧址上建了百货大楼。说书人常挂嘴边的话,我却一直记得:人生如戏,不得较真。
正是因为不较真她曾经的抛弃,我才留她同住。
夏天开始不久,她经常夜不归宿了。
最初,我并不知道。住的地方离公司远,我通常早上六点半出门赶公司的班车,而她还在睡觉。
有次加班,我回来已深夜一点。她的房门开着,床上没人。第二天早上出门时,她的房门仍开着,床上还是没人。
也是奇怪,她的夜不归宿,竟然让我暗自松了口气。她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去处,这也许是件好事。
夏天结束时,她恢复了正常。
依旧早出晚归。偶尔在周末会带些熟食和酒回来,邀我一起吃喝。她总是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那个位置以前是父亲的位置。父亲活着时的最后一年,我将他接来与我一起生活。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房东移民,准备出售房子。我贷款买下了这套二居室。
她跷着腿,悠闲地剥花生、啃鸡爪,大口喝啤酒。
她似乎突然有了好胃口,也不怕胖了。两个人待在客厅里,并无话可说。她边啃鸡爪边自言自语道:“有些男人不喜欢女人太瘦,有肉,性感。”
我无话回答。她并不理会,自顾自吃。再后来,我抱着电脑躲进房间。她不太介意我的态度。她常视我为无物,在我的屋子里悠然自得。
有段时间,她白天闭门不出。睡懒觉,做面膜,修指甲。傍晚时打扮精当,下楼散步。她天生善于和陌生人搭腔。没多久,就和小区里的人熟络得像交往了半辈子似的。
冬天的时候,她带回了一个男人。
起初只是来喝喝茶,双方都有规有矩的样子。
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我家来去自如。男人坐在父亲曾经的位置上,她坐我的位置,聊天,喝酒,嘻嘻哈哈。他们打开电视,永远停留在娱乐档,音量从不节制。
她整个人活跃了起来。天天变着花样穿衣服。走路说话,媚态十足。他们在客厅里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她绝不会来打扰我,她当我不在。
她全然不理会我的感受,独自没心没肺地快乐起来。周末,之前从不下厨的她,早早梳理整齐头发,穿上漂亮衣服,钻进厨房几个小时不出来。厨房里飘荡着熬汤和炒菜的浓香。
厨房浓厚的气味让人心生恍惚。多少年了,我生活里极少有这般热烈的气味。我甚至产生幻觉,感觉生活从此可以火热起来。
饭菜准备好的时候,她的男人准时来敲我家的门。三人围着桌子坐下。男人坐我父亲的位置,她坐我的位置,我只好靠厨房这边坐着。这样一来,我进出厨房就很方便。她指示我拿调料、换碗碟、倒开水。她和他像是做了几辈子夫妻般亲亲热热。他老是偷偷掐她的腿。她的娇态和媚眼,她的做作,还有他的厚脸皮,让我无处可躲。
我暗自尴尬。我几次想提醒她别矫揉造作。想想还是忍住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在她面前,在这个生了我的女人面前,有些话,我始终不好意思说出口。
男人开始留宿我家。
“你们有什么打算?”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
“没打算。需要有打算吗?”她奇怪地看着我。
我有心悸的毛病。
我从小就担心有一天我会窒息而死。
小时候,父亲常常喝醉酒,半夜跌跌撞撞地回来,蹲在客厅里号啕大哭。哭得像个不知所措的被人遗弃的小孩。最初听他呜呜大哭时,我躲在房间里,吓得要死,心脏悸痛,全身发冷。长大后,遇到紧张的事,我仍会本能地心悸。
自从那个男人住进来以后,我心悸的毛病又犯了。
我时常因心悸而大口喘气,像一头得了肺病的老牛。我害怕回家,下班后要么待在办公室,要么待在咖啡馆。吃简单的套餐,处理工作或看书,我要拖到很晚才慢腾腾地起身回家。进门,快速洗漱完便躲进房间睡觉,醒来后收拾好后立马离开。我尽量不与他们碰面,眼不见心不烦。
她其实相当不年轻了,甚至可以说老了。她却不自知,化妆品遮不住她脸上的蜡黄和四处溢开的皱纹。她不甘心,把妆化得很重,做出一副在老去的岁月前宁死不屈的样子,这不屈的倔强里渗漏出一大片惨败之气。
自男人住进我家后,她常会趁我上班时,偷偷溜进我房间,用我的化妆品,穿我的衣服,然后和他一起出门,招摇过市。回家后,她脱下衣服重新挂回我的衣柜内。第二天,我穿上她穿了一天、变了形的、有异味的衣服,还怀疑自己是否哪天穿过后忘记洗了。她的不节制所造成的众多细节上的混乱,时常让我生出种种错觉。
她越陷越深,除了偷穿我的衣服和鞋子,还偷拿我放在衣柜底下的钱。最初只是偶尔少几张,后来就越来越大胆,有次竟然少了一大半。
我想说,但不敢说。我倒不是怕她尴尬,而是怕自己难为情。
我替她难过。
我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给她,家里的开销也不用她付,可她似乎仍不够用。
那个来路不明的男人。我对他,一无所知。
“你究竟要在这儿住到什么时候?”那天晚上,推门进屋时,我在过道上遇到他,忍不住问。
他什么也没说,飞快地逃进了她的房间。他逃跑的样子,像只老鼠。
我躺床上翻了几页书,关灯睡觉。
就在迷迷糊糊快要靠近梦境边缘之际,我听到了一阵拍门声。响声很大。我惊醒过来,起初以为听错了。拍门声继续,急哄哄,像死了人似的。
我被拍门声吓得不轻,全身发抖,心脏悸痛。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急忙从床上翻身起来,飞跑过去开门。看她站在门口,披头散发,脸色发青。
我奇怪地问:“怎么啦?”
“你什么意思?”她恶狠狠的。她竟然用这样的口气与我说话。我的脑袋乱糟糟的,整个人恍惚得要命,对眼前所有的一切。
“什么什么意思?”我反问。
“他说你让他搬走,你不给他好脸色看,他明早就搬走,你是不是看我有了男人,心里嫉妒,成心不让我好过?你独立,你不想嫁,你很威风,你想成为老姑娘,我可不想。”她突然蹲下身去,哭了起来。
“不就是问了问他有什么打算?一个大老爷们儿,住别人家里,连问都不能问?”我反问。
“是我邀请他来的,与他无关,有什么事,冲我来!”她哭天抹泪,世界末日似的。
她的行为如此怪异,超出我的想象。
她哭得那么伤心,像真死了什么亲人似的。我不懂如何去劝她。她越哭越伤心,索性瘫软在地上继续哭。
他在她的房间里,始终没出来。
我是不是该向他道歉,替她求他留下来?
绝不!
他吃人家的住人家的,难不成全家还得看他脸色活,还得哄着他,得像土地公公一样天天烧香供着?
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实在没必要。我之前一直避,早出晚归,尽量不在他们面前出现,可这屋子是我买的,按揭是我在还。这个女人离开了我二十多年,父亲因她郁郁而死,她突然出现,打乱了我的生活,这些我都忍了,因为她说她生了我。可如今,她带个男人回家,为一句正常话,倒在我的房门前哭天喊地,这算怎么回事?
我想了想,关上门,躺回到床上试着继续睡觉。
她就瘫坐在门外面,长长短短地哭,哭得停不下来。
她总是如此荒谬。
因为头天晚上没睡好,头痛得难受,第二天一下班我就回家了。推开门,看见他和她坐在客厅里喝茶。男人将腿挂在桌边,见我进去,他愣了一下,将桌子上的那条腿收回,放下。
她看了我一眼,冷淡的。冷淡里夹着一股还不曾消散的怒气。
我清楚,他不会走。
她肯定会以为,她用彻夜的哭泣,抚留下了金贵的他。
她在找男人的问题上,眼力有问题。她看不太清楚方向。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是这样。她有了我父亲,父亲实诚,不会取悦她。镇上某个轻佻的年轻男子,明里暗里勾搭她。她以为是爱,没几下就决定跟着他跑。她扔下了我,就像没生过我一样。她给外婆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就当她死了。她在外面混了没几年,就被年轻男子抛弃了。她便如苍蝇般乱飞,都只是绕着男人飞。她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飞过。她那柔软的身子里,从来没有真正长出骨头来。她一个人站不住。她飞来飞去,不知撞了多少堵墙。老了,也许累了。她想起来世上还有个女儿。她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地闯进了我的生活。她的执念还在,肉身也没有真正老透,还对男人抱有少女般盲目的幻想……
她确实曾给我买过木马。
小小的,木刻的,粗糙的。
我一直将那木马带在身边。之前一直以为有一天这小小的木马会旋转起来,像真正的大木马,迎着光,迎着风,旋转,旋转,旋转,那么欢畅和喜乐,像她陪我看过的电影。
我进屋后,先去了趟洗手间,然后去厨房拿了个草果。这个草果便是我今晚的晚餐了。我一边咬草果一边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正当我进了房间准备要关门时,她在背后喊住了我。我回头,看见她快速地瞟了他一眼,然后清晰地道:“想和你商量个事。”
“好。”我转过身来看着她,右手扶着门框。
“你找个地方,搬出去住,这样大家都方便些。”她直视着我的眼睛,那么坦荡自然直接。
我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担心她的神经有否出了什么问题。
这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我身子瞬间发凉,心脏疼痛。我看着她,本能地反问:“你说什么?”
“你最好找个地方,搬出去住,这样大家生活起来都方便。”她看着我,目不转睛。
我已经清醒过来,完全被她的话激怒了。我的愤怒比正常该来的缓慢很多,但仍旧感觉全身的血往头上涌。
他们竟然想要赶我走。该搬出去的应该是他们。我之前想过,无论他们搬去哪里,我可能不会时常去看她,但仍旧会给她寄些生活费,以女儿的身份。
真是太要命了。心悸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扶着门,安静地看着她,看着这个生了我、大晚上还不卸妆的陌生女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太多的话卡在喉咙里,我确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不想吵架。
“你说话呀。”她竟然紧逼不放。
“好,过些日子吧。”我嘴唇发颤,干巴巴地回。
我一直想要一个妈妈。
一直期盼着能与妈妈坐一次旋转木马。我一直活在对妈妈的想象里。就像她永远活在对男人的幻念之中。
二十多年后,她终于回来了,但她不是妈妈。她就好像是别人留给我的遗物。我原本准备将她好好供起来,就像我随身带着的木马。
我将房子挂在了中介,去公证处做了委托,委托我最信任的大学同学帮我处理房子出售之事。公司早决定外派我去美国,这次我利索地接受了。
那天,我拖着小小的行李箱,天没亮就从家里悄然离开了。她不知道我要去美国。她从不关心我要去哪里。临上飞机前,我想了想,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我想告诉她,多多保重。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热烈的《小苹果》的音乐:“听不清楚你说在什么,我们在跳舞。”她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多年过后,我在纽约遇见了对的人,能量相当,彼此尊重。相识五年后,我们在旧金山附近的某个小镇安居下来,共同经营着一家公司,养了一堆孩子,有我们自己生的,也有领养的。我们在时间里学习如何包容,学习如何持续地相爱。我们在自家的后院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儿童乐园。在乐园东边角,我先生给孩子们装了几匹会旋转的木马。
除了信用卡每月自动会给一个叫王秋梅的中国女人转一次账外,我不再与过往有任何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