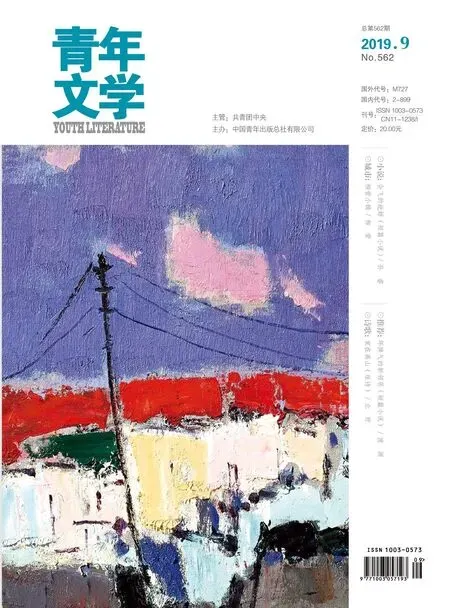被群蚁吞噬的犀牛
文/柳 营
她终于听到了敲门声。
现在几点?不知道。长久呆坐在阴沉的屋子里,孤独和单调夺走了可妈对时间的感觉。
她起身开灯,开门。女儿可晴站在门口。精致的黑丝绸中裙,水头极好的翡翠项链,大大的黑眼圈。
“他又好几天没回家了。”可晴一脸忧色。
“离,坚决离。”可妈想起他那张可憎的脸,下意识地收紧身子,手握成拳状。
“说起来都简单。”可晴道。
“越拖越受罪,早听我,就不会有今日,这次一定要速战速决。”可妈的发间闪着大片的银色,但脸部棱角依旧分明,当年是个美人。
“真希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晴瘦弱,更显可欺。
“他是个浑蛋。”可妈低声呵斥道,“你真傻,到现在还对他抱有幻想。”可妈满脸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可晴怨艾:“我之前不嫁他,他割腕。他为了得到我,曾经连死都不怕。”
“你是糊涂蛋、可怜虫,到现在还看不清楚,还不死心。”可妈愤愤的。
“我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可怜虫就可怜虫吧。”可晴收了收身子,看起来更瘦了。
“没什么可失去的?你还有一条命。你来世上一趟,容易吗?就这样纠缠下去?又不是养不活自己,何苦受他折磨?”可妈语气比刚才柔软了些。
“再等等,总会有结果的。”可晴道。
“你不是小脚老太,你得自个儿活出个味道来。”可妈提了声音。
“我先回了。”可晴低声告辞。
“今天别回了,住妈这儿,陪陪妈,娘俩说说话,好否?”可妈近似于恳求。
“还是回去吧,万一他晚上回来,我找机会与他谈谈。”可晴道。
可妈心里凉,起身,送她出门。
女儿出了门,下了楼梯,可妈一直竖耳听着,直到女儿的脚步声一点点消失在远处。可妈关了门,回到客厅。
电视里正在播《动物世界》。一头巨大的犀牛,被一群蚂蚁吞食。可妈觉得那犀牛就是女儿,女儿正在被某种奇怪的东西一点点吃掉,越来越瘦,越来越小。
她随手关了电视。坐回到椅子上,独自发呆。
南北窗都关着,屋子里闷热。可妈懒得起来开窗。汗出如浆,纽扣解开,蓝绸短袖已经湿透。
颈椎腰椎都有毛病,开不得空调,找来一把麦秆扇,慢慢摇。摇呀摇,脑袋转呀转。想起亡夫弱女,细节铺开,一点点呈现,一节节旋升。往日光景,眼前孤寂。
天气渐暗。
就要落雨了。
有滚热的潮气从窗缝中卷进来。可妈起身,倒了杯凉水喝。厨房里还有中午的剩饭,盛了一小碗,用开水烫一烫,就着剩菜,胡乱吃。
雨点响起,越来越大。
吃完,又出一身汗。
雨也是烫的。风像蟒蛇缠身,裹得死紧,透不过气来。
进客厅,沙发上坐下,继续发呆。
肉身呆坐,心全在别处。女儿脸庞上新添的皱纹,眼睛里溢着的晶莹泪珠。眼看女儿掉进水里,使劲拖,就是拖不上来。她赖在水里,被水泡着,不知深浅……
梅雨如注,又是一身汗。
挂钟的声音,嘀嗒嘀嗒,嘀嘀嗒嗒,重复着渗到可妈的耳里。脑子乱哄哄的,意识虚空起来,肉身却又是重的,一直往下沉,沉进无底的水潭中。几近窒息,天旋地转……
伸出手去,在沙发旁的小柜子里,胡乱抓,抓出一瓶药。
手抖,抖得厉害。努力拧开瓶盖,倒了几片。扔进嘴里。吞下去。
大口喘息。
房间太小,呼吸声加重。
她安慰自己,没事,没事,清醒,清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世界缓慢地清晰起来。
雨声变小,空气凉爽。可妈浑身湿透,全身绵软,扶着沙发手,慢起,摸进浴间。
用棉布洗了把脸,擦了擦身子。
早早上床。
雨虽小,依旧在落,无休无止。
一夜挨一夜,漫长无期。
亡夫在时,喜欢在枕边给她讲故事。还是原来的床,夜夜躺下。人不在枕边,故事还在耳边。
寂寥的夜里,故事里的人,全都被可妈一一忆起。鲜活的人和事,从暗处闪现,带着亮光,滑过来。
声音涌起来,在耳边翻滚。
翻滚着的,是亡夫的声音。
睁眼,淡薄的夜。
亡夫就在床前站着。
可妈从床上坐起来:“阿国,回来啦?”
不见阿国开口。声音仍在耳边滚来滚去,故事往前,继续,人物一个接一个活过来,各自说话。
声音越过她的肩膀和脖子往耳朵里钻,轻声轻气,嗡嗡嗡的。声音黏得那么近,像细细的一层皮肤。可妈能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气味,那气味热乎乎的,直逼她而来。与她身上的气息缠在一起,变得滚烫。它们热腾腾的,贴着可妈的颈脖,钻进可妈寂寂的胸膛,干瘪的小腹,它们盘旋着,留息在那处。可妈粗粗地喘气,喘得脸红。
真是阿国回来了。是实实在在的气味,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粗糙浓烈,带着他特有的热量,无声无息地堆叠。他像是雾,一片朦胧,只有影子在移动。是他的汗气,还有他两腋的暖流。他仍旧强壮有力,他的头发间冒出汗来,热融融的。气流在被窝里弥漫,覆盖住可妈阴凉的身体……
到处都是缠绵的摩擦声。
风吹窗帘……
雨还在落。房间漆黑,窗外有汽车声。幻觉消失,可妈翻转身,叹口气。
房间沉于寂静。
可妈在黑暗里呆着,止不住泣。幽幽的,低低的。
窸窸窣窣,拖过枕巾,揩了满脸的眼泪。
心想,明天给他上支香。
“昨晚,他打了我。”可晴一大早在电话那边呜咽。
“离开他。”一股闷气逼来,可妈觉得难受。
“也是我不好,又和他吵,把他吵烦了。”可晴幽幽自责。
“弄来弄去,要拖到什么时候?”可妈烦乱。
“我想去学插花,先静静心,最近就不能常过去看你了。”可晴转了话题。
可妈不作声,心里有气,这女儿怎么这么不随她,做事不果决。“早离早消停,要拖到什么时候?”可妈问。
“我想好了,不去管他,不吵,不闹,随他吧。”可晴补了句。
可妈心口痛。
“再说,他不提离,我也不提。”可晴自言自语,却有哭腔。
“你自个儿要活成那样,别人管不了。”可妈心里气。
“离了,又能怎样?”可晴问。
“一个人清清爽爽的,有什么不好?”可妈觉得嘴唇干燥。
“再清爽又能怎样?离了再找一个男人,有那么容易吗?”可晴哭出声来。
“没男人,你就不活了?这样瞎缠,一辈子就缠完了。”可妈有气无力。
“他总会老的,要歇的,我等着。”可晴不甘心。
“你还没老,就要等人老?”可妈手脚发麻。
“反正都要老的,老了就折腾不动了。”可晴吞吞吐吐。
“白活,瞎活。你正在被你自己一口口吞掉。”可妈挂断电话。
难得有日头,可妈出门去买菜。
买了小葱、豆腐、鱼头、一小块肉、几棵肥青菜。
晚上做了豆腐鱼头、红烧肉、炒青菜。摆在桌上,好看好吃。开了瓶黄酒,自个儿慢慢品,细细消磨时光。一个人过日子,也得过得像模像样。
吃了鱼头、红烧肉,喝了老酒,身子热,脑袋涨。
听到敲门声,一下,又一下。侧耳再听,又是一下。身体燥热,赤脚,去开门。开了门,屏了呼吸,门道里极静,没人,有风。
似乎又要下雨了。
回桌前坐下,菜已凉,酒还有一半。倒满,又喝了一杯。有敲门声,这次,真真切切。趿拉着鞋,走过去,打条门缝。可妈扶门掩身。
看到门口那人的凉鞋,细脚踝,黄裙子到膝盖,粗腰身,大胸,浑圆的肩膀。是一肥胖的女子。女子开口说:“抄煤气的。”
可妈侧身,门开大了些。
女子进来,笔直往厨房里钻。拿了小凳,打开橱柜里的煤气表。也就半分钟,女子离开。门重新关上,锁舌嗒一响,混在女人离去的脚步声里。
女子身上爽身粉和洗发水的味道还留在厨房和大门之间的过道里,与桌子上的菜味,厨房里的油烟味,角落里的污垢之气夹杂在一起,被锁进过道的灰暗之中,一片寂寥。
脸烫,全身烫。
满屋的孤寂。
可妈拖着鞋子移回桌前,收拾碗筷,洗涮干净。回到客厅,开了电视,转了几个台,对着电视呆坐了几分钟,拿起遥控器,换了几个台,又呆了半小时,瞌睡上来,关了电视。
房间沉于黑暗。
亡夫在的时候,这个时辰,两人该从运河边回来了。
可妈喜欢和他在饭后去河边散步,两个人并肩走。河里有运煤运沙石的汽船,岸边有唱戏练琴的人。河水的气味,植物的气味,柴油的气味,隐隐约约夹有花儿的清香。
两个人走半个钟头,到了拱宸桥,在桥头的青石板上坐坐,吹吹风,说说话。牵着手下桥,在桥头的铺子门前买串热乎乎的臭豆腐,一路咬着,你一小口我一小口。
现在,可妈连出门散步都觉得烦。一个人缩在屋子里,懒得动。
阿国弥留之前,拉着可妈的手,细声细气道:“别怨我走在你前头,我晓得留下你一人很苦,会孤单,但一定要开心,别让我担心,要开心。”
可妈眼泪一颗颗滚落。不接话。手紧紧握着阿国的胳臂,怕稍一松开,阿国就会消失。
阿国继续道:“答应我,多出门走走,找找老朋友,喝茶打牌。”
可妈点头。喉咙呜呜响。
阿国顿了顿,又开口:“真要遇上脾气好的,可以一起过。”
可妈摇头,泪珠雨一样地落。落到阿国的胳臂上,顺着他的胳膊往下淌。
阿国的脸越来越黄,先变灰,继而变暗。曾经那般强悍威武的阿国,变得越来越薄。可妈拼命抓着他,可他一直薄淡下去,薄成了一张黄草纸。
也有之前认识的孤身男人,对可妈有好感,说想照顾可妈,想和她一起过。可妈根本不答应,就让他别讲。
她说,我一个人在屋里待顺了,再进来一个,不习惯。
又落雨了?
细听,是屋子里的钟声,嘀嘀嗒嗒,像雨声。
女儿多少天没来了?
屋子空荡荡的,没人气。
这夜,可妈躲在被窝里,想着亡夫生前对她的好,又难掩心里起伏,寂里有悲。听了很久的钟声,念了无数遍阿弥陀佛,差不多后半夜了,才迷糊了一会儿。
“妈,他最近天天回来。”这天晚上,可晴来电话。
可妈拿着电话不作声。
“他说,他只是贪玩,心里有家的。”可晴笑嘻嘻。
“我听着刺耳。”可妈觉得小肚子隐痛。
“他最近工作不顺,想出门度个假,放松放松。”可晴道。
“好呀。”可妈拿起报纸,翻了翻。
“让我陪着一起去马尔代夫。”可晴说。
“噢。”可妈被报纸上的奸杀案、贪污案、植物园里的郁金花展所吸引。
“这几日身体还好吧?”可晴问。
“好。”可妈又翻了一页报纸,注意到一则新闻,说是乘客错过了站,生气,抢公交司机的方向盘,车子翻倒在了绿化带。万一翻到江里,那可怎么了得呀。可妈心想。
“度完假去看你。”可晴说。
“嗯。”可妈挂了电话,继续翻报纸。
晚上梦到女儿和女婿吵架,吵得天翻地覆,打耳光,扯头发,哭闹。又梦到女儿被女婿打死,她赤身躺在地上,变成一头巨大的犀牛,被时间和蚂蚁一点点吞掉。可妈心里急,看着女儿,想拿苍蝇拍打蚂蚁,可这蚂蚁真多呀,铺天盖地而来,没有尽头。
雷声划破一切,震天响。天要裂开了似的。
可妈被天裂开的声响惊醒,听声音,是楼上传来的。
楼上住着一对吵架成性的夫妻。可妈经常睡到半夜,被楼上的声响吵醒。椅子倒地,杯子摔碎,怒骂,歇斯底里哭泣,没完没了,沸反盈天。
楼上女人的哀怨一声接一声,起初哭天喊地,之后沉沉起起,随后越来越细,细到无声无息,线一般,吧嗒一声,彻底断了,然后像死了一样……
一直下着雨,淅淅沥沥,连绵不绝。
屋子冷清,钟摆声,嘀嗒嘀嗒,嘀嘀嗒嗒,嘀嗒嘀嗒。
窗外楼房,一边层层叠叠,暗灰,分不出界限,一直往西绵延,最后化为墨黑,缩成黑夜。另一边,面对着山,山那边是西湖。
可妈想,这有男有女的温暖被窝,缠缠绵绵,细细碎碎,有爱造爱,交颈而眠,有什么不好。可不知为何,这同睡一张床的人,常将被子抛起,温暖的被窝和睡眠全不再重要,吵架却成了半夜必做之事,各自浑身发抖,扯开嗓门,互相诅咒。这家男人身体软脾气硬。女人身体冷脾气倔。没有爱又不懂如何去爱这个世界的女人,从内而外,都是凉薄的。可妈每每在楼道里遇见她,都觉她满脸寒气,如自家的女儿。男人暖不起女人,又打又吵,女人少了真正的心气,想挣扎,却犹犹豫豫,缩在阴影里,照不见日头,日复一日,就这样枯黄了。这生活,潮湿湿阴惨惨,像是地窖。可妈倒是喜欢他们家的儿子,圆乎乎的脑袋,每次见了她,都会脆脆地唤声“可奶奶”。如今这圆乎乎的脑袋早已出远门读书去了,为父为母的半夜的鬼叫声,仍川流不息。
就又想起在马尔代夫的女儿,心里发酸。无能为力。添堵而已。
又想,生得了她的身,保不了她的世。
人各有命。
说是人各有命,想起来心里还是烦的,躁的。想多了,胸口闷得慌,头又眩晕起来。身子变得滚烫,哪处着火了似的。
火烧火缭的,热焰四窜。
可妈紧锁眉头,闭着眼,忍着。等着猛劲儿过去。
又觉得冷。骨头里的冷。
脑袋似乎变得越来越大,要爆炸了似的。太阳穴刺痛,像有人在耳边敲鼓,鼓声长久不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直敲。敲得人想吐。
骨头是冷的,肉身是滚烫的,该是发烧了。
屋里先是死静,随后有了些声响。倾耳听,来了,是阿国来了。可妈听他开门,穿过客厅,进了卧室,站在床头,伏身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又站了片刻,脱了衣服,光着身子滑进被窝,贴着她,依着她,将嘴对着她的耳,讲起了故事……
那么多的往事,那么多的好风景。
她咚咚咚响个不停的脑袋里有了奇妙的声响,阿国的声音低柔轻缓,真真切切。
可妈挣扎着想转过身去,却动弹不了。想睁开眼,眼皮却沉重得要命。她就那么僵硬着,感知贴在她后背的阿国,如以往一样,赤裸的,强健的。
被窝里有了不一样的暖意,耳后根有了热腾腾的气息,可妈有了些安慰,疼痛似乎缓和了不少。
她知道阿国在陪着她。他的故事讲得断断续续,听不太真切。
可妈的意识也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脑袋还在疼,身体还在燃烧,她被折磨累了,想睡了。半醒半梦之间,她似乎感觉到阿国帮她转过身去,搂进怀里,他的脸贴着她的脸,他的微笑如爱抚,两人四目相交,可妈突觉松快,心火渐宁。
他抱她如抱婴儿,用近乎爱昵的声音在可妈耳边呢喃:别担心,慢慢来,我等着你……
可妈松下心,迎着他的声音,踩过满地的蚂蚁,往前走。
闹钟突然响起,当的一下。
响声划破厚实的寂静。又当的一下,随后重归孤寂。
这孤寂里,仍有嘀嗒嘀嗒声,像雨声,又像钟声。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电话铃响。
一下,二下,三下……八九下。
无人接。
隔了二天,电话铃又响。
一下,二下,三下……
没人接。
雨连绵不绝。
路灯灰暗。
保塔山脚下的老社区,像西湖的湖面,雾蒙蒙一片。
一位穿着得体满脸憔悴的女子,绕过一楼的走廊,穿过灰暗的楼道,高跟鞋响到三楼,停下,敲门。
妈……
妈……
妈……
里面没有声响。
掏出小包里的备用钥匙,开门。
推门进去,一股潮霉的恶气扑面而来。女子扫了眼靠窗的小饭桌,半碗霉干菜扣肉,半碗剩饭,都已长霉。
又叫了几声。妈,妈,妈。
边叫边直奔卧室。
一声惊叫,几丝啼哭,又细又长,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