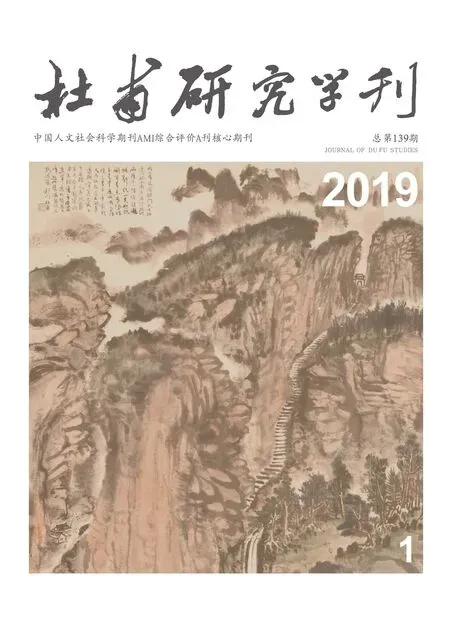杜诗异文传播中的本色保存与文化增殖
阮丽萍
作者:阮丽萍,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400031。
从文化学的视角考察杜诗异文,主要的是对异文文化传播功能的关注。异文是原始文本的衍生形态,与文本一起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表征着文化。任何一种经典文本的译解、释读和接受的过程,都承载着传统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异文是读者在经典接受过程中与经典作家意义输出的符号互动,对文化历时演进进程中的“差异”进行符号表征,是“有意味的差池”。因此,异文的文化传播功能比之原始文本更加明晰。
对经典文本的每一次释读,都是以阐释并增殖原始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为目的的。历代杜诗释读行为,都可归结为从各个不同侧面对杜诗原始文本价值与意义的追索。伴随着杜诗文化传播过程,“原始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出现扩大和增殖现象。传播学理论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其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文化增殖现象。文化增殖是一种文化放大现象,当一种文化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出新的价值或意义,或一种文化的传布面增加从而使受传体文化相对于传体文化有了某种增殖放大,这就是文化的增殖现象。
一、杜诗异文考订与原始文本的本色保存
古籍异文是原始文本的衍生形态,异文考辨中注家按断“当作……”之语,省却的主语为“原始文本”。众所周知,杜诗原始文本(或言第一文本)已不可寻,但是这一“虚拟的存在”对于杜诗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围绕杜诗展开的著录辑佚、注释笺证、考订辨伪、圈点评藻等传播活动中,杜诗原始文本始终是阐释的起点、又是批评的最终归宿。从异文的生产机制看,异文是对第一文本(或原始文本)“本来面目”的历史追寻。杜诗文本参与者对杜诗“原本”用字的推求,虽说是一种想像性的建构,但也体现出对杜诗“历史面貌”本色保存的心理需求。注家的这种心理需求与杜诗异文的考订过程相始终,可以以杜诗几则文本参与程度较高的异文为例说明问题。异文参与程度高,是个相对的概念,意即某句杜诗的某处异文,相对于其他异文而言,参与讨论的人数多、受观注的程度高。杜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句,“没”字出现异文“波”。“波”字来由,苏轼《东坡题跋》有明确记载,系北宋文士宋敏求所改。宋敏求为何改“没”为“波”,原因在于“鸥不解没”: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淹没灭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诗改此两字(另指陶潜《饮酒》诗改见为望,笔者按)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也就是说,老杜“没”字用法与宋敏求的阅读期待视野不相一致,于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原始文本”用字“没”进行“选择性理解”,认为是老杜此处用错,或是版本有误,遂以改字的形式消解主客观间认识上的“差池”,异文“波”由此而生。异文一旦产生,就像一块具有巨大聚合作用的“磁铁”,吸引同一时代或处于异代的杜诗研习者将目光集于一点,在反复的讨论争鸣中,异文原有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得以增殖和繁衍。宋敏求的改字,引起了苏东坡的不满,认为宋氏是“以意改书”,判为非;至南宋,吴曾又不同意苏东坡的判断,认为宋敏求改字有据,他说:
东坡以杜诗“白鸥波浩荡”,波乃没字,谓出没于浩荡间耳。然予观鲍照诗有“翻浪扬白鸥”,唐李颀诗有“沧浪双白鸥”,二公言白鸥而继以波浪,此又何耶?
吴曾认为此处异文作“波”字有理据,与吴曾同时代的南宋学者王楙亦持相同见解,他不赞同苏东坡的判断,认为宋敏求改字有理,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九“白鸥波浩荡”条云:
仆谓善为诗者,但形容浑涵气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鸥波浩荡”之语,有以见沧浪不尽之意。且沧浪之中见一白鸥,其浩荡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没耶?改此一字,反觉意局,更与识者参之。或者又引鸥好没为证,仆案《禽经》:“凫好没,鸥好浮。”
以上诸说,两种版本各执一词,作“波”作“没”各有理由,遽难断其是非,终究以“两存”的形式保留异文。自宋以后,对于这则异文的讨论并未结束,明千家注本作“没”,于句下注曰:“‘没’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语,势当是‘没’字相应。”明末《杜臆》亦不同意宋敏求的改字,从诗作行布的内容分析角度断“没”为是;至清代,前人于此句杜诗异文著录的文献,“原样”地传承到清代杜诗注家手中,除此之外,亦别有创见。以仇注为例,仇氏原文著录了鲍照诗句,兼之赵次公、苏东坡、吴曾、王嗣奭等人对此句的讨论所引用文献;在“原样”传承之外,仇注又有新的发明,他引用《易林》“凫游江海,没行千里”句,指出杜诗“没”字所本,体现出文化传承中立足本色、忠于传统的特点。
又如杜诗“欲往城南忘南(一作望城)北”(《哀江头》)句,是杜诗异文中最典型、文本参与程度最高的例子之一。《全唐诗》于此处异文的标注方法过于简省,有异文失收之嫌。笔者检诸宋本,发现此句用字与异文当有三个版本:忘南北、忘城北、望城北。“北”为本诗的韵脚字,不容轻易改动。围绕“忘南”“忘城”“望城”孰者最为接近杜诗“原始文本”庐山真面目的问题,先后有十余家治杜诗者参与了讨论。现以时代为序,研究这组异文的历时传播释读情况。
宋本释读。二王本作“忘南北”,白文无注;宋百家本、宋千家本、宋分门本皆作“忘南北”,无异文;蔡笺本作“忘南北”,同时出注异文“一作‘望城北’”。北宋王荆公集句作“望城北”,未言所据;赵次公用荆公集句版本,作“望城北”;郭知达宋九家本另作“忘城北”。草堂本采用的是传统的异文辨析方法,根据诗句上下文语境来进行语词分析,找到最有可能贴切杜诗原意的表达,《草堂诗笺》云:
忘南北,一作望城北,非是。甫朝哀江头,暮又闻吐番入寇,欲往城南省家,仓皇之际,心曲错乱,忘南而走北也。甫家居城南,当时为之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宋玉《九辩》篇:“中瞀乱兮迷惑。”王逸注:“思念烦惑,忘南北也。”
至南宋,陆游也加入了这组异文的讨论,《老学庵笔记》云: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陆游是从诗意语境的角度判断异文,训“望”为“向”,指出作“望城北”是。至明代集千家注批点本,刘辰翁对前人对于这组异文的批评皆不引用,径作“忘南北”,刘氏极有可能认为前人对此处异文的释读皆不尽人意,不足以令人信服,故弃而不用。明末王嗣奭《杜臆》于异文处的阐释也相当模糊,语焉不详。胡震亨《唐音癸签》中对这组异文有详细讨论,胡氏据地理文献《两京新记》考证曲江的确切位置在都城东南,地理特点是“其地最高,四望宽敞”。据此,他认为,“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因此,胡氏按断此处异文当作“望城北”,因为曲江一带四望宽敞,适合老杜伫望城北的官军。

杜诗异文中还有一例“知名度”颇高:“不闻夏殷(当作殷周)衰,中自诛褒妲”(《北征》)。这是《全唐诗》出注的异文,实际上还有改下句的版本异文“中自诛妹妲”,《全唐诗》失收。本句之所以出注异文,原因在于诗句若如字面解则不通,于是历代注杜诗者致力于“弥合修补”。弥合之间,表现为众人对此句杜诗原始文本用字“猜迷射覆”过程,有四种处理意见值得关注:一种观点认为老杜误记、讹混历史史实,用典时出错;兼之“命语痛快”,涉笔成误,所以不必追究。宋代赵次公、清代叶燮、浦起龙持此观点:





二、杜集异文传播与杜诗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增殖
历代杜诗文本参与者是杜诗的异代传播者,文化传播的理想状态是保持传播对象的本色,“原样”地将传播对象呈现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体现出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从这一点来看,杜诗传播过程中异文的出现,异文出注者主观上并非以“变形”杜诗原始文本为旨归,相反地,改字(句)的本意在于“还原”,而不在于“存异”。也就是说,不论实际情形如何,异文出注者的本意在于消除杜诗释读中的误读误解、廓清迷雾,客观准确地传递第一文本的原初状态。可见,杜诗异文现象,体现的是杜诗历时文化传播中“本色保存”的主观愿望与“变形走样”的客观效果的实际悖离,异文消蚀着原始文本的意义和形态,同时又承载着杜诗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增殖。
第一例中,“没—波”这组异文的产生,起点是由杜诗接受者(宋敏求)的释读期待视野与文本提供的信息不一致,由此先后吸引了十余家治杜诗之行家里手参与异文讨论,这还是有文献记载的书面讨论,还有大量的口头讨论或不见经传的书面意见都不包括在内。通过异文传播,杜诗“白鸥没浩荡”句原本的内涵与意蕴不断被发掘出来,成为传播的客体;与此同时,对此句杜诗“没”字或然性的理解与释读——不管是否“乖违”杜诗原意,在客观上都实现了在杜诗原始文本意义基础上的文化意义的增殖。
第二例异文的历时讨论,逐渐超越杜诗文字符号表层的文化信息而进行深层发掘,至少实现三个方面的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增殖。(一)对异文诗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诗意的深度讨论阐释,以异文为研究起点,从诗句思想内涵的角度“发散性”地多角度释读异文句,实现了在杜诗所要表达的原始意义之上的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增殖。(二)对杜诗本句“忘南北”“望城北”的互文性的考证。异文讨论参与者着力于对两种表达分别找到用语根据,因为他们相信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主张用“忘南北”者,引宋玉《九辩》成句及王逸注(草堂诗笺)、又引曹植《吁嗟篇》成句佐证(仇注);主张用“望南北”者,引《逸周书·武儆》及唐传奇、《敦煌变文》成例(郭在贻),均指出杜诗用字语出有典。(三)考据方面。胡震亨为了弄清这则异文的真相,专门考证了曲江的历史地貌,证明作“望南北”的合理性;陆游《老学庵笔记》对“望”字进行了考释,证明“望城北”是;今人郭在贻训“望”为“忘”,通过对大量的古书辞例的考证,指出两字为通假字关系,兼引唐时文献佐证。在这组异文的阐释与流变中,可以寻见文化的本色保存与价值增殖的过程。
第三组异文中,如果赵次公、浦起龙的判断为真,那么另外三种处理意见均是杜诗原句意义与价值的增殖;如果顾炎武的解释切合了杜甫本意,那么剩下的三种说法亦可视为异文传播中价值与意义的增殖。不管原始文本真相如何,围绕着这则异文而进行的讨论,产生了远远高于原始文本本身的文化信息,实现了原始文本意义与价值的增殖。
杜诗中参与度较高的异文,除以上三例外,尚余多例。如“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一作白白)江鱼入馔来”(《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一作服)虔”(《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五云高太甲(一作太乙),六月旷抟扶”(《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子云清自守,今日(一作令尹)起为官”(《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等等。这些诗句中的异文,伴随杜诗文本的传播过程,无一例外地吸引了十家以上杜诗注家、学者参与异文的讨论。这一过程中,异文本身既像一块蕴含巨大能量的“放射物”,向不同时代的异文文本接触者提供与他们原有的阅读期待视野或一致或乖违的文化信息,与受众期待视野相一致的文化信息会被“本色保存”;反之,受众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其进行“选择性理解”,实现原始文本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增殖;同时,异文又像一块具有巨大聚合作用的“磁铁”,吸引历代杜诗文本参与者始终将目光集中到某则异文身上,在众人的参与讨论中,异文在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基础上实现了文化意义的增殖和繁衍。
三、异文传播的文化增殖机制
异文传播,可视为中国文化传播史上以杜诗为中心的一种文化辐射现象,通过经典作家的意义输出,读者受众围绕文本(包括异文)历时符号互动,衍生出新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异文传播的文化增殖功能,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者。传播主体对某种文化的传播,是对该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与确定,通过传受活动,实现共通意义空间的共享。宋代“千家注杜”的文化现象,本身也是宋代士人对杜甫与杜诗的文化价值的估价与确定,通过对杜诗价值与杜甫的文化意义的发掘,树立了宋人作诗的典范,催生出成熟的宋调。注杜“千家”皆为杜诗传播者,从现存宋代124种杜集文献来看,不少以“刊定”“校定”“新定”“改定”“正宗”等语辞命名,皆以杜诗本色保存为旨归。上述“波—没”这组异文,苏东坡、王楙、王嗣奭、仇兆鳌等人对“没”字的坚持,皆立足于杜诗的本色传播。然而,在该异文的历时讨论中,“没”字的意义空间被重新发现乃至扩大,以清代“集大成”之仇注为例,仇氏于异文处著录了前代宋敏求、赵次公、苏东坡、吴曾、王嗣奭等人对此句讨论所引用的文献,在“原样”传承的基础上,更引鲍照、《易林》中的句子以证“没”字出语典,是为在客观传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实现了意义共享与价值增殖。
(二)受传者。受传者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文化信息进行“选择性理解”,从而衍生出许多生成的意义。宋人以学问为诗,以才学论杜,当杜诗文本用字与自己的阅读期待视野不相一致时,便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对“原始文本”用字进行“选择性理解”,必要时臆改杜诗。上述宋敏求之“波”字便是以意改字;第二则异文中,蔡梦弼臆改“望城北”的痕迹尤为明显;第三例异文中,对异文的四种处理方式,代表十余家注解杜诗者对异文“选择性的理解”意见,各执所见,从不同角度衍生出新的意义,恐是老杜始料未及的。一般来说,文本经典化程度越高,受众面越大,选择性理解的可能越大,文本聚合的能量越大,文化增殖的空间就越大。


异文就像一个既定且未完待续的“议题”与“谜语”,承载着文化传承与价值增殖的使命。某则异文受关注的程度越高,越能吸引较高层次的注家学者参与讨论;反之亦然。特别是一些杜诗研究大家的意见参与更有“广告效应”,对异文的历史走向、异文诗的传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逐步实现了杜诗部分篇章的经典化。
注释
:①岳广鹏:《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②(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据津逮秘书本影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③(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页。
④(宋)王楙著,郑明、王义耀点校:《野客丛书》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⑤(宋)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卷一,明嘉靖已丑八年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本,第24页。

⑦(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杜诗卷九,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0页。
⑧(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
⑨胡震亨《癸签》卷二十二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讫无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东南。《两京新记》云:“其地最高,四望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他诗:“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即此意。若用“忘”字,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义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