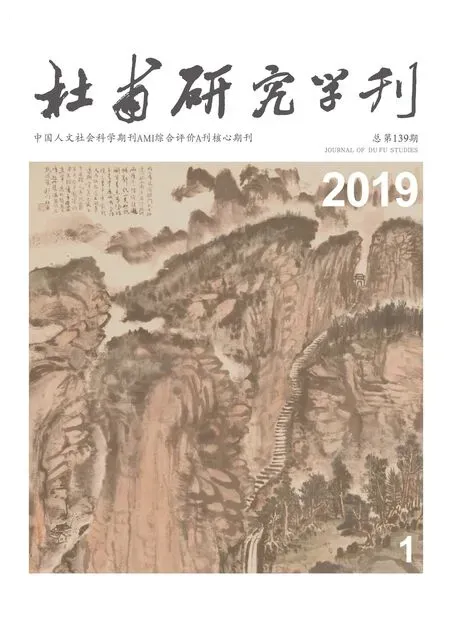杜甫与唐玄宗、肃宗、代宗
魏耕原
作者:魏耕原,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教授,710025。
杜甫身历三朝,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裂变时期。他无时不关注国家社会,是政治感极强的诗人。对所经历的玄宗及子孙三代军国大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有大量时政评论之作,从中考察他对皇权的态度,可以纠正“一饭未尝忘君”的传统而牢固的定位,从而理清对君权至上原本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一、对唐玄宗肯定与讽刺的悖论
当开元二十三年,李林甫任中书令,“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琎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次年,“监察御史周子谅言(牛)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所引,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李林甫又谗杀玄宗三子,玄宗自林甫为相,因其出于宗室,“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袵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而耽宠固权,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阴计中伤之”。妒贤嫉能,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韦坚、李适之、李邕、裴敦复均遭其迫害。为了固位,更张开元前期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以蕃人为将,利其不识文字,无由入相,安禄山缘此得大将之任而坐大。直至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病死,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乱。继任相位之杨国忠,其人“禀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枭首覆宗,莫救艰步”。大唐帝国自此进入多事之秋,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一直到灭亡。
向来认为大唐由盛转衰以张九龄罢相为分水岭,也是玄宗时盛唐的转折点,这说法大致不错。然玄宗好大喜功,奢侈之风自开元中期逐渐兴起。张说虽在推行开元初期开明政治以及擢拔文士、提携诗人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但他“志在粉饰盛时”,则与玄宗志得意满不无关系。为中书令时首建封禅之义,奉迎玄宗,当时就遭到源乾矅的反对。开元十三年封禅,“车驾发东都、百官、四夷酋长从行。每置顿,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还有祠睢,上谒五陵等粉饰,均属劳民伤财之举。
开元元年,高力士升为右监门将军,开了宦官掌权之恶例,大唐三大毒肿之一便首先由此滋长。附会者希风望影,竭肝披胆以求吹嘘。诸如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通过此渠道入将拜相,“其余职不可胜纪”。导致宦官后来发展到口含天宪,恣意废立,大唐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还有天宝后期从上至下,奢侈淫靡之风盛行。在外似繁华升平的天宝时代,耗费之数巨增。即使在天宝年间军费开支已增长惊人:“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固苦矣。”
明了以上这些,我们看杜甫诗如何对待玄宗的态度,就会更有深刻的了解。
天宝十三载《渼陂行》写一日之游,忽阴忽晴,始则天地昏黯,恶风白浪堪忧,既而月出天朗,氛挨忽散。未了忽复天地苍茫,云飞水立,仙灵幽渺,说得天摇地动,忧乐无端,此诗似非单纯为赋游景,隐约之间有些异样的预感:豪华的大唐似乎将要面临“咫尺但愁雷雨至”的大变,只是“苍茫不晓神灵意”罢了。因隐忧在怀,哀乐无端,只是未明说出来,这并非空穴来风。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只看两年前所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即可知此言之非妄。同登之高适、岑参、储光羲诗写景均天朗气清,全与平日游览之诗无异。只有杜甫却“登兹翻百忧”,看到的却是:“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的忧虑,皇州将面临一种大乱。故哀痛“惜哉瑶也饮,日晏昆仑丘”,有了如此预感的隐痛,而渼陂景色的变幻或许即此心忧的折射。所谓“知我者谓之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即此之谓也。
就在作《渼陂行》同年秋季,霖雨两月不止,严重遭灾,杨国忠取禾之善者蒙蔽玄宗说“雨虽多,不害稼也”。杜甫《秋雨叹三首》其二说“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自上年到此,关中水旱相继,人多乏食。回看《渼陂行》就更非泛写游景了。
至于作于天宝十载的《兵车行》,直斥“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对玄宗无异是戟手痛责。“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已就玄宗肆意开边造成的经济凋弊,忧心至极!《丽人行》就衣食两端铺叙诸杨姊妹的骄奢无度、苟且淫佚,实际上也是对唐玄宗后期昏妄的尖锐讽刺,这从“黄门飞控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灼然可见。作于与《兵车行》相先后的《前出塞九首》,其一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其六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都是对唐玄宗轻启边衅、开边拓士的谴责,这也是军费开支巨增、导致国困民弊的原因。
安史之乱前的杜甫对唐玄宗态度,集中反映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年杜甫44岁,在长安困守十年,对政治中心长安与玄宗的政局有了全面深入了解。经骊山时听到皇家音乐震天,推想赐浴、分帛、听歌看舞,由此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慨谴责。经渭河时看到群冰西下,而感到“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预感到一场巨灾大祸将要发生,此与“焉能辨皇州”的预感是一致的。《渼陂行》的隐忧于此时得到证实,不幸而言中。就在杜甫担心“天柱折”的同时,安史已在渔阳起兵。
对于玄宗在马嵬兵变被迫处死杨贵妃,杜甫《北征》认为:“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这是从寄希望于肃宗政权的角度,谓玄宗犹如亡国之君,而肃宗当能中兴。此前在至德二载的《哀江头》里有感于国破家亡的悲痛,指出昔日玄宗与诸杨骄奢淫侈,彼此互为因果,其中也包涵着对玄宗播迁的同情。合观二诗,而有愤其荒淫与哀其不幸的复杂感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历四年(768)的《千秋节有感二首》,这是专为玄宗而发的最后一组诗。千秋节是以玄宗八月五日生日为名的节日。其一说“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其二说:“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谓玄宗极乐于当年,恣情尊贵,却以骄盈召祸,实开乱端。有感于玄宗昔日之乐召来后世的无尽之悲。
综上可见,杜甫对玄宗前期开创的开元盛世是称赞的,但更多的是对后期奢侈荒淫给予尖锐的鞭挞与谴责。这在唐代诗人,恐怕只有李白差可比肩,其他则可以不论。由于旧时的注者和论者,过分强调了“忠君”一面,而讳言讽君的一面,甚或遇及后者之作,极意曲解杜诗的用意。因而对于讽君的一面直到现在或多或少有所忽视。杜甫对唐玄宗以及后之肃宗与代宗的谴责,都是以儒家特别是从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出发,故批判之激烈,远远超过“葵藿倾太阳”的一面。杜甫与当时人民吃够了唐玄宗所造成恶果的苦头,所以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忘记他负有罪责的一面。
二、杜甫与肃宗
肃宗李亨扮演曾祖太宗与乃父玄宗的逆取皇位角色,稍有不同的是,是借着安史之乱机会采用了“抢班夺权”的手段,虽然都是以“禅让”或众心所归名义登上大宝。此年已45岁了,他怎能不着急呢?

至德二载(757)五月杜甫从沦陷的长安,冒着生命危险奔往凤翔即肃宗行在。当时唐玄宗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杜甫也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肃宗。在《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说“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其三又说“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把肃宗看成大唐中兴之主,这也是当时人们的唯一的共同愿望。当时百废待兴,肃宗政府正是人材乏缺之时。杜甫所任左拾遗为从八品,有直接参预国家大政的权利,可以在朝廷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见。可是立足朝廷半月之间,他赶上了肃宗清洗玄宗旧臣。此年三月罢免韦见素、裴冕知政事,八月贬放崔涣为余杭太守。韦、崔与房琯均为玄宗由蜀派往灵武册立新君,此前五月借故已罢房琯相位。房琯罢相,一来是随从玄宗奔蜀至普安郡提出诸王分镇之议注,削弱了当时还属于太子的势力;二来是上年即至德元载十月,房琯自请将兵,收复京都,结果连续在陈陶斜与青坂败绩。当时安史已陷长安,兵势方炽,“然房琯所将本非精兵且意欲持重伺敌,而中使邢延恩督战,遂至仓皇失据;则其败也,犹之哥舒翰潼关之败也。琯之败,肃宗待之如初,可见其咎不在琯。肃宗不因败绩而借门客受贿罢免房琯,正是隐忍阴挚心理所致。三来肃宗视房琯为旧臣党魁,但素有重名,言时事慷慨,以天下为己任,但用兵并非所长,加上自己派宦官督战,遂及于败,房琯请罪,所以肃宗只好隐忍,“待之如初”。四是贺兰进明向肃宗进谗,谓房琯请玄宗命诸王分镇,“以枝庶悉领大蕃,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旧唐书·房琯传》)。综上诸因,肃宗意在清洗玄宗旧臣,对房琯惨败隐忍半年,遂在五月以细故罢免房琯。至德三载贾至坐房琯党被逐出守汝州,他又是普安郡诏的起草者。又于同年(758)略后即“乾元元年(758)罢免崔圆中书令为太子少师,留守东都。于是上皇所置宰相无在者”(《新唐书》本传)。至此唐玄宗派往册立代表团的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贾至,或罢相或贬放,清洗一空。杜甫联名推荐的岑参,在任右补阙时的《寄左省杜拾遗》说“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暗示杜甫不要多事,也在乾元二年(759)贬放虢州长史。严武因房琯荐为给事中,在乾元元年贬为巴州刺史,房琯贬邠州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贬房琯诏书里说:“崇党近名”,“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肃宗对他宿怒全都发泄出来。所谓“房党”实际上是被肃宗视为太上皇党,属于新君与父党之间矛盾。

疏救房琯对杜甫是件政治大事,因自此被视为“房党”中人,而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机会。他原本对授左拾遗并不惬意,再加上成为多余而且有碍的人,把半月前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的激动便冲刷了许多。他以切肤之痛体会到肃宗的心胸狭窄。于是只好告假探家,省得肃宗对他感到那么地不舒心。抵家后作《北征》,如果说在安史乱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确如前人所说的是“心迹论”,那么此篇就是谏疏或奏议。把这次疏救房琯的波折,说是“虽乏谏诤恣,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真是不知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
此诗对军国大政,提出以下几点:一是不主张借兵回纥,以为“此辈少为贵”。可是“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帝心期望回纥,群议为之沮丧。“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此两句“曲尽夷情,所以却之难,而禁之不易”(王嗣奭语)。后来克复洛阳后,回纥则大肆掠夺,遗祸无穷。二是不主张先收复二京,这和不借兵回纥,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次年四月郭子仪在长安西清渠官军一战大败。接着肃宗急欲收复长安,必然要借兵回纥。杜甫不主张借兵,自然反对这时收复长安。《北征》所说的“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深入非指收复两京,因凤翔距长安在咫尺之间。何况希望先开青徐,再略取恒碣老巢,然后收复两京即可伸手而得。可惜自古以来对此误解,以为杜甫主张先收二京,再回收复河北,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
此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所杀,叛军处于败势。当时李泌建议不欲速复二京,先守太原,取冯翊,则叛军不敢离开范阳与长安,分割其兵力,使之北守范阳,西救长安,疲于奔命不逾年而弊,然后以扶风、太原、朔方军围取范阳,巢穴一失,敌自可覆灭。最后收复二京易如反掌。这是论当时用兵之形势,本当如此。杜甫这六句的见解与李泌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建议如出一辙。然而肃宗却要先收复两京,并非不明大势,而是因此年李璘起兵虽被平息,而为了巩固已到手之帝位,如果先复两京大功在手,其他诸王就不得不拱手臣服,也不会再有像永王李璘起兵的事件发生。所以,宁愿使安史之乱延续,却执意以收京为务,这也是肃宗阴暗心理所致。杜甫这一主张向来湮没不彰,这也是他后来弃官赴陇的重要原因。
三是肯定了马嵬诛除诸杨之举,认为是“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由此也似乎透露出马嵬兵谏的掌控者是肃宗。四是希望能恢复“煌煌太宗业”。
次年即乾元元年(758)年杜甫出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有《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他把去年投奔行在与今年贬逐又出此门,在长题中寓愤慨于冷热的对比中。其中说去年从沦陷之长安投归行在,“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实是说心之热;“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这是贬官带来的心冷,也是对肃宗的讥刺。

在华州的《立秋后作》的“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杜甫已下决心弃掷派给的司功参军,也见出对肃宗的不满。在秦州的《遣兴三首》其二的:“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由于肃宗担心郭子仪、李光弼等功高难制,故派九节度使围攻邺城而不设统帅。致使次年惨败。事后又闲置郭子仪,后又置李光弼于临淮,所崇信者却不能成事。《秦州杂诗》其二十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已见对所谓的“中兴主”肃宗已彻底失去了希望,这也是他弃官的主要原因。又说“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决心要和所倾之“太阳”告别。其六说“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邺城惨败全由肃宗不设统帅造成,酿成平叛最大的损失。若破邺城早灭安史叛军,则士卒不须以防河北。其八说“一望幽州隔,何时郡国开”,邺城惨败,叛军之势复张,至九月东都洛阳再次沦陷,河北亦复沦陷,而平息叛乱天下安定又待何时。其十一的“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邺城之败使幽燕之克复推宕,而且吐蕃又骚扰,形势陷入恶化。其五说:“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邺城惨败,以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召子仪还京闲置。所以《其十九》说:“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台。”希望子仪复起。当初,郭子仪克复两京,肃宗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疑忌平叛后功高难制,邺城之围,故不设子仪为统帅,而败后即解除兵权,杜甫即对此而发。所以其二十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实则正言若反,对肃宗表示出极为不满。
宝应元年(761)为了削减玄宗蜀郡势力,肃宗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南都,太原府为北都。对此,杜甫《建都十二韵》说:“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议在云台上,谁扶黄屋尊?建都分魏阙,下诏辟荆门。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当时东有史思明,西有吐蕃陷边州,“半乾坤”尚处于骚扰,天下苍生在丧乱中还未喘过气来,又劳民动众,以建江陵为南都,废蜀郡之南京,意在汲汲于解除玄宗之影响,实非平叛之急务,而失东西天下人心。时局艰难当思洗雪国耻,建都大计此时岂应轻论。肃宗即位已五年,政权稳固,但叛兵祸根犹存,万国尚不安宁。此诗末了说:“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是说衣冠瞎忙乎,关辅之难无救,天子当把心思用在河北平叛大事上,不应有汲汲建都之举!

三、杜甫与代宗
犹如对安史之乱的预料,杜甫在《忆昔》对代宗的警诫,亦不幸而言中。代宗为太子时,对李辅国的专横看不过眼。虽借助他的力量而嗣位,又因其方握禁兵,忍而尊礼之称“尚父”而不名。辅国持政益横,便削减其权,因其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密遣人刺杀。可见出代宗之阴狠。后来宦官程元振代辅国专制禁兵,诬陷名将来瑱以坐诛,又构陷元勋裴冕而外贬。二人皆与其人原有私憾或不依违,天下方镇因此而寒心。代宗又听信他的谗言,夺郭子仪兵权,致使岐雍兵力单薄,而失去御敌实力。在代宗即位次年即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自缢,属下部将李怀仙携其首来降,延长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总算结束。杜甫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抒庆祝。然好景不长,时局不久又起恶化。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恐安史一旦平息而宠衰,故奏安史降将分帅河北,自为党援,代宗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只好同意。河北藩镇自此蹶张强傲,不可复制。
上年回纥协助围攻克复洛阳。“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月不灭”(《通鉴》宝应元年)。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来犯,程元振匿而不报,及至咸阳,代宗仓皇出奔陕州,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长安再次沦陷。当时代宗下诏征兵,诸道兵马无有至者,皆惧程元振谗构,众怨所归,代宗方罢元振官,长流溱州。
代宗即位两年间以程元振取代李辅国,犹如以豺代狼,结果造成长安再度沦陷,虽然已被闲置的郭子仪很快收复,这毕竟是大失人心的事。所以,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一后半说:“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其先代宗听信程元振谗言,夺子仪兵权,所引起的恶果,即“百官跣足随天王”。长安府库闾舍,也被焚掠一空。
对于长安再陷,杜甫在阆州《伤春五首》追记其事。其一说:“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蒙尘清露急,御宿且谁供?”这是说奔陕之狼狈。其二说:“牢落官军速,萧条万事危”,即指长安被兵,援军不赴,情势危急。其三言:“烟尘昏御道,耆旧把天衣。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言代宗出奔,父老牵衣挽留。而诸镇畏程元振谗构,莫肯奔命。末言“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希望进贤去奸,是为当时切务,也是杜甫之“愤词”(吴瞻泰语)。其五说:“闻说初东幸,孤儿却走多。难分太仓粟,竞弃鲁阳戈。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代宗逃亡之时,听说“孤儿”即禁军溃散。奔至华州,官吏奔散,无复供给,护从将士冻馁,竞相逃散。事见《通鉴》代宗广德元年。吐蕃攻进长安,王公奔窜。最后唯有希望君臣修德共济,收拾人心,挽回根本。代宗继位一年多而致大乱,均由信用宦官造成,郭子仪、李泌、来瑱不见重用,或馋死或闲置或隐居,故诗中以“贤多隐屠钓”“犹多老大臣”“得无中夜舞”反复致意,这是对代宗的希望,其中也蕴涵对代宗的讽刺。

后来杜甫已知收京后代宗不治程元振死罪,有感于代宗迷途尚不知返,作《释闷》忧心国事:“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前四句谓时局愈来愈不堪,代宗奔陕,国势愈见衰败。天子逃跑得也够累了,也该与群公考虑如何平息战乱,然而仍旧加重赋敛不改覆辙,而且没有诛杀罪魁程元振,犹因其有拥立之功而放归田里,这真是出人意料。这时杜甫已对代宗失去了希望,这从末二句的反语可见。

大历三年(768)漂泊岳州所作《岁晏行》,深叹时政徵敛繁重,小民不得其生,这是痛恨代宗钱政的愤慨语。现在丧乱仍旧遍及全国,不知何时方能结束。这是杜甫代民呼吁,也是对代宗败政予以全面揭露与指斥。

注释
:
②③④⑥刘昫等撰:《旧唐书·李林甫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37页、第3238页、第3255页、第4757-4758页。
⑧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本文所引杜诗圴引自本书,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⑨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见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