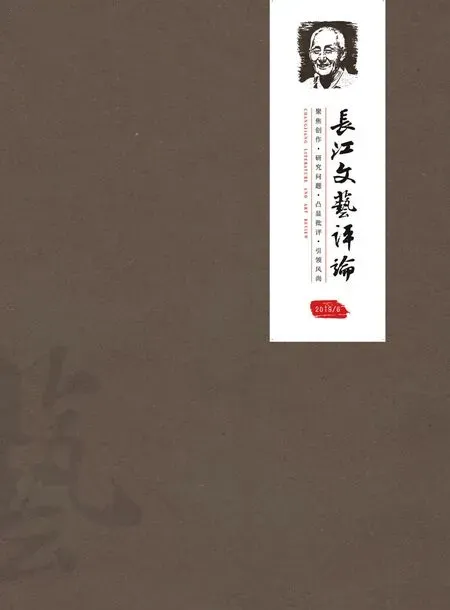且说“拔高阐释”
◆段崇轩
一
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的文学批评已然有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但当下却存在着普遍“拔高阐释”的现象,因而备受文坛内外的质疑和訾议。近段时间,围绕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部作品于201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是作者的第16部长篇小说。出版社的广告词称:“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间秘史,一部描绘秦岭的百科全书。”同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长篇小说年度金榜”和《收获》举办的“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中,这部作品都名列前茅。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也喷涌而出。搜索中国知网,2018年关于《山本》的专题评论文章就有六十多篇,一开始绝大部分是叫好声,半年之后出现了批评声。其实对一个高产作家来说,我们不能要求他每部作品都是精品力作。时高时低、有好有坏,应是正常现象,均应以平常心待之。但出版界、评论界却抱着自己的目的,把名作家的新作都要“打造”成“巅峰之作”。
先看正面评价:“二十世纪的拉美文学因一部《百年孤独》为世所瞩目,贾平凹的新作《山本》由人而史,实为一部中国近代之《百年孤独》。它无百年之长,却显百年之忧。”“读《山本》以《水浒传》为参照,可以看出《山本》在精神认识上完全超越《水浒传》,从而达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与批判。”再看负面评价:“细读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会发现数量虽多,质量却普遍不高。这在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中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价值观、情感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等方面,《山本》都有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山本》的思想主题混乱,艺术上也很粗糙,远非一部优秀之作。而且它在叙事模式和不少细节描写上还较多沿袭了贾平凹之前的作品,并映射出时代文学潮流的较大影响,缺乏足够的创新。”上述的评论者,都是圈里的“领军者”“实力派”,但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却天壤之别、冰火两极。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山本》的思想艺术价值,也不去探讨贾平凹创作的长处短处。我敬重贾平凹在那片古老土地上的不懈耕耘,赞赏他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但对于评论界对他以及作品的一味恭维、叫好,却不敢苟同。从对《山本》的负面评论中,倒是看到了另外一些问题:当下的文学批评界存在圈子化、江湖化等不良倾向,一些批评家把“拔高阐释”当作了自己的得力工具。现在文坛上表现出的观念混乱、良莠不分,批评家和作家人格矮化、形象不佳等现象,都与这种拔高阐释风潮密切相关。
“拔高阐释”源自西方阐释学理论中的“过度阐释”概念。阐释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人文理论,它着力研究文本本身的理解和阐释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到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众多学科,但对文学理论与批评有着更直接、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代表性理论家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阐释学引进中国,对中国的文学评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作家安贝托·艾柯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圣经》的阐释时说:“一个文本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文本,在其阅读的过程中就可能不断受到质疑,因而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过度阐释”由此成为阐释学中的一个概念。对一个读者或批评家来说,理解和阐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但都是有限的。把一说成二或三,脱离文本的真实而随意夸大、借题发挥,就是一种过度阐释。拔高阐释也是过度阐释中的一种,它指的是有意无意抬高作家作品,作出超出和脱离文本阐释的一种方式。那种有意贬低文本和片面解释文本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过度阐释,这里且不去说它。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历史中,拔高阐释现象可谓根深蒂固。譬如“十七年”时期,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某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竭力鼓吹。譬如20世纪90年代后的多元化文学时期,为了圈子的、个人的利益对一些作品的夸大评价。文学批评不再遵循学术标准和规则,被外在力量所支配,拔高阐释批评就势在必然了。
在文坛上,拔高阐释的现象随处可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文章和著作中的表现。如今,文学评论报刊大量增加,出版学术著作的门路多。这对文学评论的发展自然是好事,但需求的扩张也会带来文学评论质量的下滑。批评家特别是知名批评家的写作,都变得身不由己。作家出书会主动奉上、请你指教和评论,报刊和出版社会向你约稿、专为某作家作品撰文。批评家被缠绕在一种圈子和网络中,不得不写一些违心文章。既然受人之托,甚而提前支付了报酬,写文章自然是要说好话、唱赞歌的,因此,把一般作品说成优秀作品,把优秀作品拔高到杰出作品;好处要说得到位,坏处要回避和隐去;发掘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抬高作品在当下和文学史中的位置和意义。这些都成为文学批评的写作惯例。至于著名作家新作出版,一般不会给批评家奉寄样书,但人在江湖,早已形成了一个个圈子、门派,每个著名作家的身边都会有一群拥趸者,都会及时撰稿发表。基调上是肯定为主,评价上要层层加码。二是在首发式和研讨会上的表现。现在,文坛上会海如潮,官方的、市场的、个人的,源源不断。对于体制来说,是出政绩的需要;对于作家来说,是满足名利欲的需要。当然,严肃的、艺术的研讨会也是有的。但不管是作品首发式还是创作研讨会,请批评家有偿参会,就是要捧场、说好的,你不能违背这个游戏规则。于是,把一般作家说成优秀作家,把优秀作家抬高到文学大家,而文学新秀出于扶助的目的也需“拔苗助长”。在这样的会议上,问题、缺点往往是忽略不计的,即便要提,也是蜻蜓点水。会议发言要整理出来,发在微信群、报刊上。比之文章和著作,文学研讨会上的拔高阐释显得更为突出。三是在文学评奖中的表现。不管哪个级别、哪种类型的文学评奖,获奖作品总有一段“授奖词”,这同样是一种作品阐释、一种更凝练、更高度的评价。打开这些授奖词,有些概括精准,但不少言过其实,不管是实至名归的,还是勉强上位的,都是“上天言好事”。而它真正的获奖理由、思想艺术价值,往往语焉不详、大而化之,这是一种最显眼的拔高阐释。
二
在当下,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作用,这些本是常识性的问题,却变得模糊、复杂起来。评论几近变成了表扬、宣传的代名词。其实文学批评的内涵,有评论、评判、分析、阐释、批评,指出局限、错误并提出意见、建议等多重意思。文学批评自然需要肯定、赞扬,但更需要批评、引导,后者本是它的重心所在。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两栖”文体,它具有主观性、艺术性,同时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前者是它的形,后者是它的魂。古今中外的作家、评论家,对它的特征作出了精辟论述。俄国作家普希金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中国评论家童庆炳说:“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入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我们需要重温这些基本理念,恪守文学批评的本质和精神。
由于对文学批评本质特征的淡忘,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心理期望,出现了严重错位。作家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往往期望批评家能道出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点,总结出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和写法,并把他推到理想的文学位置上去。而批评家的心理期望复杂一些,他自然希望能准确把握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让作家和读者满意;也希望能坦率地指出创作问题,引起作家和读者的注意。而肯定、表扬是没有风险的,否定、批评则是不讨好的。因此“聪明”的批评家,就把文学批评变成了过度拔高的文学表扬。我们油然想到鲁迅对批评家的态度和期望:“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他最不满的是批评界的“捧杀”和“棒杀”,他殷切期望那种判断准确、是非分明的批评家出现。今天似乎又回到了鲁迅的时代,但我们却丢失了鲁迅那样的胸怀、雅量。
拔高阐释现象的盛行,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转型期。整个社会告别“革命”、转身市场,摆脱传统、投向现代,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作为精神文化形态的文学滑向了社会边缘地带,商业文化、大众文学如潮涌起。首先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的侵蚀。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文学始终是关乎国家、社会、民众的大事,而到市场化时代,文学逐渐卸去了部分历史重负,慢慢变成了个人的事业、兴趣,或是博取名利的工具。既然是个人的事情,就可以用来谋求个人利益,达到私人目的,抒发小我情怀。作家写作通俗的、低俗的作品,或写作迎合的、“歌德”的作品,以此赚取稿酬、名利,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捷径。批评家写作“遵命”的、应景的、人情的评论文字,比坐冷板凳更有效益。而跟踪名作家、一律唱赞歌,更是最易成功的事情。其次是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学是探索社会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艰苦的、曲折的。而在世俗化社会中,文学的本质、价值也在变化。它可以“兴观群怨”,更可以逢迎、娱乐、消遣。作家编造传奇、戏说历史、娱乐人生、张扬自我,都可以写出广受欢迎的作品。而批评家在文章中迎合潮流、捧场名家,只说成就、不谈问题,同样可以赢得各方欢心。文学娱乐化、批评颂扬化,似乎成为90年代之后文学不可逆转的大潮。最后是拔高式批评的简单易成。真正的、学理的文学批评,是需要下苦功的力气活,甚至是冒风险的。而拔高式批评不仅得来容易,且四面讨好。这种批评,不需要细读作品、研究作家,只把握作品、作家大概,然后放置在当下创作、文学发展中,给出一个放大的、宏观的判断和评价。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分析,也很简单,复述故事情节、评价人物形象、发掘社会内涵、概述表现方法和语言。而文本的思想意蕴,要努力上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生命、人性的层面,去理解、阐释,才算大功告成。此外,中国特色的文学体制,在组织作家队伍,建构国家文学,扶植各类创作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它重当下、重面子、重宣传、重政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拔高阐释、表扬批评的滋长。这种批评方法已经形成一种模式,是传统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升级版,颇受一般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的青睐,因此在各种文学评论报刊中满目皆是。
作家需要赞扬式评论,批评家习惯于拔高式阐释,于是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密切而暧昧起来,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个有形无形的文学圈子、江湖。评论家丁帆在一篇文章中痛切地说:“反思自己的批评生涯,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了‘挣工分’做过不少无端和无聊吹捧自己作家朋友的不齿评论,当我意识到这种批评行为近于无耻时,也至多只能做到认为作家朋友作品不好就缄默无语,不发言论,甚至拒绝一切约稿。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对自己认为不好的作品进行批判性的批评,成了鲁迅‘林中响箭’声中的退却者,成了别林斯基皮袍下的萎靡小人。”他道出了众多批评家内心的隐痛。当下文坛,表面热热闹闹其乐融融,但其实作家心中有不安,批评家心中有纠结。在拔高阐释的风潮中,作家的形象变得模糊、扭曲,难以站立起来,批评家的形象显得可疑、懦弱,难以引导文学。文学没有标准,鱼龙混杂,越来越远离现实和民众,远离艺术和真理。当文学出现无序、泡沫状态时,就失去了应有的品质、力量。
三
文学批评如何理解和阐释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等,在一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中,已讲得明白、到位。而真正在文学批评上有真知灼见的,是阐释学学派。中国引进阐释学已有三十余年,并有了自己的理论建树,但在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上,却成效不大。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阐释学是一门丰富而精深的思想理论,我们不必深究,但它的基本思路和一些概念,对文学批评颇有启迪意义。
阐释学文论研究的中心是作家作品与读者、批评家的关系。围绕这一关系,形成了三个重要概念。一是“成见”,即批评家的先入为主之见。一个批评家在解读文本时,总是带着他的全部感情、思想、经验、修养等走进作品的。这就必然给他的解读带来主观性、个体性。因此,作家期望批评家猜透并阐释他的感情和思想,并拔擢到一定高度,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批评家总是用自己的成见去观照、解读对象的。而拔高阐释往往是违心的、敷衍的。伽达默尔说:“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成见,它实实在在地构成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成见即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二是“阐释的循环”,批评家解读作家作品,既要守住自己的成见,又要打破自己的成见,在两种声音、两个世界的反复交流、碰撞中,努力把握批评对象,改变和丰富自己的理解、认识。狄尔泰说:“一部作品的整体要通过局部来了解,局部又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了解”,这就是一种“阐释的循环”。因此,拔高的批评、贬低的批评,都是有违批评规律的。三是“视界融合”,批评家面对作家作品,不是主观武断地要把自己的感情思想替代作品的感情思想,也不是俯首帖耳地用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替代批评家自己的审美判断,而是两个主体构成一种交流、对话关系,在激发和互补中合二为一。正如理论家张首映所说:“视界融合就是文本的视界与读者的视界的融合,或文本的视界与解释者的视界的融合。理解就是把这两种视界‘融合’在一起,产生两者都超越了自身的新的视界,组成一个共同的新的视界。”可以说,批评的权力是无限的,更是有限的。他受制于对象也受制于自己,他要把两个世界融合之后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真正的批评是艰难的,也是神圣的。
阐释学理论最终会派生出“批评对话”。对话批评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理论和学说,而是一种批评立场和方法。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小说中,发现了文本中版块与版块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构成了一个“大型”的、“复调”的对话世界,从这种对话中,洞悉了文本的全部内涵与奥妙,形成了巴赫金式的对话理论。法国评论家托多洛夫,在巴赫金等众多理论家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对话批评理论。如前所述,那种唯名作家是从,把他们所有的作品都尊称为成功之作,有问题的作品也不敢批评,乃是一种仰视式的“捧杀”批评。而那种自以为是,对批评对象“鸡蛋里面挑骨头”,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贬损式批评,则是一种俯视式的“棒杀”批评。这两种批评都是不足取的。托多洛夫倡导一种平视式的对话批评,他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文学与批评无所谓优越,都在寻找真理。”在对话批评中,作家与作品构成一种主体,尽管作家并不在场,他的作品构成了一个世界;而批评家构成了另一个主体,同样是一个世界。两个主体隔“书”而坐,共同探索文本呈现的社会、人生和审美内涵,乃至作品中的真理。批评家最终在文章中阐述的世界以及理性阐释和判断,是二者融合、共造的结晶。其中需要肯定、赞赏,但更需要分析、批评、建议。在严谨的、学理的批评中,作品和作家的形象是客观的、清晰的,批评家的形象是真诚的、可亲的、可信的。
现在,我们很少谈论批评家的主体建构了。其实,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体制化的社会中,批评家的主体建构是格外紧要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建构。於可训教授在《且说文艺批评的异化》中,论述了文艺批评“经历了由克服政治性的异化到出现市场化的异化的复杂变化”。或许还应加上“人情化”的异化。我们在一个“大变局”的社会环境中,能否经得起各种力量的左右和各种名利的诱惑,能否始终坚持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公正性和学术性,确是衡量一个批评家人格境界的严苛标尺。批评家能否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并有所建树,人格建构是决定性因素。二是学养建构。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文学,对批评家的知识结构、人文学养、思想观念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扎实、丰富、鲜活的学术功底,就很难阐释当下的作家作品;没有开放、多样、现代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就很难破译当下的文学文本。因此,筑实批评家的知识、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成就一位批评家的前提和基础。人格与学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注释:
[1]【意】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页。
[2]【俄】普希金:《论批评》,齐邦媛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3页。
[3]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
[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4页。
[5]丁帆:《我的自白——文学批评最难的是什么》,《文学报》,2019年2月28日,第18版。
[6][7][8]引自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240页,249页。
[9][10]【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5页,94页。
[11]於可训:《文学批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