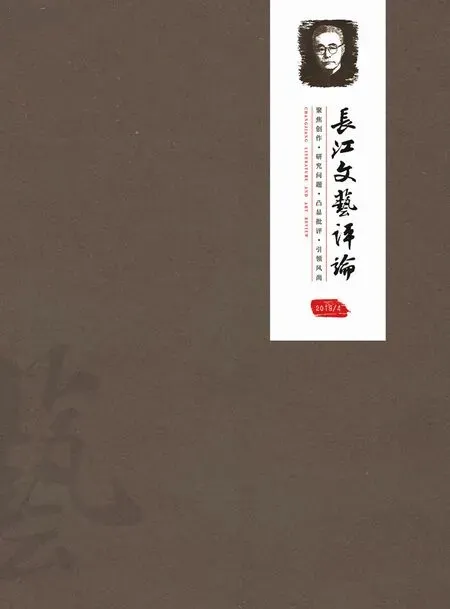弥合城市与诗歌之间的隔膜
◆李鲁平
当从文学样式上审视,把诗歌跟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品产生的影响方面,诗歌对城市的书写都明显逊色于关于乡村的书写。当走进一条街道、一家饭馆,或住进一家宾馆时,当面对一扇窗、一栋楼、一座桥、一盏路灯、一辆公交车、一个工厂或者厂房内的一个车床时,当代诗人似乎犹豫了,甚至迟钝了,而在面对乡村事物、自然山水时,他们曾经是无比地娴熟和练达。这种茫然和不知所措,折射出诗歌与城市之间的隔膜。
新时期以来,从“朦胧诗”到当下的诗歌,并非没有触及都市,事实上很多诗歌都写了城市意象。比如1979年查干的《北京,你好!》:“耕种者关注的是新出的禾苗/哦,我的北京古老而年轻/时时警惕着天旱水涝/云横海啸……”在这里,诗歌并非告诉读者具体的城市生活,而是把一座大都市隐喻为机关、单位,把对是否风调雨顺、天下平安的牵挂与一个城市的名称联系在一起。作品在本质上是以城市符号延伸展开的宏大叙事。又比如,1984年商子秦以都市末班车为题材的《深夜,延点车……》,这首诗分四个章节,由“司机”“乘客甲”“乘客乙”“乘客丁”四个角色的自我倾诉组成。在末班车上,深夜从黑暗中出发的司机“从没有行人的街道上开过/从没有灯光的大楼下开过/从都市的梦境开过/收容着守候在孤零零的站牌下/和我一样孤独的晚行者”,当公交车经过零点这个标志性时刻,司机突然发现“离黎明还有一段长长的路/我们依然是孤独的/但我们毕竟最早行驶进今天的王国”。这是一首典型的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介入了都市社会最基本的服务体系——公共交通,以及不同身份的“乘客”所映照的都市生活。虽然诗歌中充满了都市符号,但仔细品味后不难感受到,诗歌所表达的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对时间、对光明、对未来的思考和歌颂。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的诗歌对城市的书写大致都属于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它们并非严格的城市叙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关于城市的集中书写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对人口流动的放开,一些背井离乡的打工青年写了大量以街道、工厂、机器等城市元素为背景的诗歌。这些作品因为深入具体的城市生活以及个人命运,在一段时间成为农民工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活现状的代言。这些作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身份确认的书写和对精神归宿寻找的书写。
早期郑小琼的诗歌创作是这一类诗歌写作的代表之一。“我说,烧尽这些纸上诗句,这内心的激情/我,只愿把自己熔进铸铁中/既不思考也不怀念的铁/抛弃一个流浪者的乡愁、回忆和奔波的宿命/但是那块淬火的铁掉在地上,又被浇上冷水/细小而绝望的声音”。诗人在这首叫《炉火》的诗作里,决心摈弃内心深处关于自我、身份、故乡等种种执念,面对熊熊大火,她要把“乡愁”“回忆”“奔波”连同自己融化。事实上,在千万人奔赴南方的那些年,他们的人生已经与南方的繁荣熔铸在一起了,包括他们的乡愁、回忆。但即使如此,诗人也要抛弃,并且诗人的坚决在于不仅仅要抛弃乡愁与回忆,还要抛弃不断奔波的命运。如何才能真正告别不断奔波?只有在法律和身份上成为南方这个城市的市民,才可能最终安居乐业,流浪和颠沛才可能不是宿命。郑小琼触及了当代诗人书写城市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即身份问题。在这些诗歌中,充满着对“城市是谁的城市”,“我”是否属于城市等等的不断追问和思考。
精神归宿的困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书写城市的另一个主题。如果说郑小琼更多的是向内,拷问因为身份而带来的命运不确定性,郭金牛则更多的是向外,反思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与对立。郭金牛的《662大巴车》写一辆公交与一个打工青年之间的车祸。“662大巴车不是起点也不终点/它经过罗租工业区,石岩镇,和高尔夫球场/就像我经过小学初中和大学……662大巴车没有装载水稻/662大巴车也没运载高粱/662大巴车丢下了十几人,开走了”。在诗人看来,这辆公汽并不行驶在深圳,而行驶在他的家乡。这并非诗人个人的感受,而是大多数打工青年的感受。无数打工青年都会乘坐城市里的公共交通工具,但他们往往恍如穿行在故乡,在他们的精神中,公汽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并没有肌理上的联系。在《662大巴车》里,诗人并不是以一个深圳市民的身份经历了662大巴与打工少年的相撞,而是作为一个异乡客恰巧撞见了这场车祸。在作品中,诗人不断强化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断强化对自己精神归宿的指向。“站台上,一个离乡少年/被662大巴车撞倒,塑料桶滚出老远/天,突然黑下来。金子,撒了一地,无人来捡/662大巴车没有受伤……我好像一个受伤的穷人,刚刚苏醒,真叫人心烦”。天黑下来,既是对自然天象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是被撞少年人生际遇的象征,被撞少年的人生坍塌了。夕阳洒下的碎光,无人注意,也象征少年的命运无人关切。诗人对水稻和高粱这两个事物的敬重,对大巴车扔下乘客一走了之的鄙视,强烈地凸显出乡村与城市的尖锐冲突。在这类作品中,诗人从视线所及的每一个城市元素都会本能地延伸到家乡和乡村。如郑小琼的《黄昏》:“卖苹果的河南人在黄昏的光线中微笑,五金厂的铁砧声/制衣厂绸质的丝巾光芒闪烁、跳动,像女工光鲜明亮的青春/她们的美丽挽起了黄麻岭的忧伤和眺望/我站在窗台上看见风中舞动的树叶,一只滑向远方的鸟。我体内的潮水涌动。我想/这时候,在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将与我相爱/他此刻也站在楼台,和我一同倾听黄昏”。诗人在窗台看见的不是都市,她看见的是跟自己一样从中原来到南方的谋生者,她看见的是远离都市的故乡黄麻岭。诗人眺望的也不是眼前的都市,而是远方,是未来,是爱情。这些作品借助都市符号,书写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对立、矛盾,实质上触及了当代诗歌书写城市的另一个核心,即精神归宿问题。
以上两个特征,身份确认的困难、精神归宿确立的困惑,是当代诗歌书写城市的主要指向。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是紧密相连的,正是身份的尴尬、模糊、不确定,导致在城市世界精神无所归依,而对精神归宿的寻找反过来会扩大人与城市的隔膜。在大多数以城市为背景的诗歌中,我们都可以或明或暗地感觉到,诗人本质上仍然是把城市当作对立的世界来书写,即城市既不是诗人法律上的身份属性,也不是诗人情感上的栖息地,更不是命运的归宿地。他们不断在诗歌中辨别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是不是此座城市的市民;他们也不断确认自己与城市的关系,这座城市究竟是谁的城市。但结论往往令人失望。如同诗人所说:“它的繁华是别人的,它的工厂、街道、服装商铺是别人的/它的春天是别人的,只有消瘦的影子是自己的”(郑小琼《疼痛》)。对于许多打工者,不仅城市是他人的城市,繁华是他人的繁华,而且命运也无所寄托,“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郑小琼《铁》)。
户籍制度,自由迁徙的限制,使得很多人从一出生就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归宿。很多80年代初从乡村走进校园,然后定居城市的创作者,尽管都获得了城市户口以及户口背后的制度性安排,但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在精神和灵魂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对于他们,只是生活在城市,以城市为谋生之地。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出生之初所认定的身份属性和精神故乡,这一印记并未因为他们的身份获得了法律上、制度上的认可而磨灭,他们永远有家乡,有乡村,他们书写的也往往是乡村和故乡。对真正栖身城市的更多写作者而言,一方面要追求从法律上完成身份的转变,要被城市体制所接受,另一方面,要从情感和精神上完成与城市的血肉相融。这当然就是诗人面对城市时的困惑以及艰难,这些困难也塑造了当代诗歌城市书写的面貌。
以城市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显然不能停留于此,因此,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城市书写。在这种意义上,城市不是法律上与自我相对的城市。在这种意义上,谁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样、同等的城市人。在这个意义上,街道、路灯、公园、住宅区等与乡村的田埂、池塘、竹林等一样亲切,城市也即是家乡和归宿之地。一句话,城市是属我的城市,“我”是属城市的“我”。
许多欧美诗人关于城市的创作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尽管他们写的不是中国的城市。智利诗人罗贝托·波拉尼奥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诗歌大多数都从城市的街头出发,抵达城市生活的核心,咖啡馆、小旅馆、廉价餐馆、电影院、公寓、街道……这些城市符号在他的诗歌中,如同草木、乡村、山丘在我们的大多数诗歌中一样亲切、自然、深情、抒情,让人毫无察觉。面对这样的诗歌,读者不会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这是写都市的”“这不是写乡村的”。“雪落下时/但那是什么时候?/你不记得,那时候你在街上/雪落在你的警察制服上/但你还是能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跨上/黑摩托车/在街道尽头”(《巴塞罗那街道》)。这里没有任何乡村的元素,但我们感受到的城市物象,就如我们曾经感受到的乡村的农田、河流、树木一样,自然而然。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突然警觉“这是城市”。一个女孩跨上摩托车消失在街道的另一头,就如我们在另外一些诗歌中读到的,一个女孩和她的背篓或者羊群消失在村口、山梁。
本雅明曾经写过著名的《拱廊计划》,他穿梭在巴黎拱廊建筑之中,观察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试图通过都市空间构造与都市生活纹理梳理现代经济、商品世界、消费主义对人的幻觉和乌托邦的养成。波拉尼奥的诗歌中也有自己的“拱廊”,他试图通过“窗户”揭示美洲都市生活世界的纹理。“窗户”是美洲生活方式中有独特价值的空间形式之一,它不仅仅是房屋建筑和结构的一部分,更是城市精神和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波拉尼奥的诗歌充分挖掘和反复书写的一部分。如,“我在等待下雨/喝着咖啡望着窗外的美景”(《天亮》),“当你靠在公寓窗边/穿着背心,观看墨西哥的/黄昏”(《给埃夫拉因》),“那对警察穿过/文具店的橱窗然后/是餐馆和仓库/接下来另一家餐馆的大窗户还有服装店/和钟表店直到消失/在纯蓝的地平线”(《读霍华德·弗兰克尔》),“那时我终于能笑起来/打开窗户/让假发进来/让颜色进来”(《巴塞罗那的假发》)……这些不断出现的“窗口”“窗户”并非贴上去的标签,而是城市的细胞和血液。波拉尼奥写的不是词语“窗户”,不是都市符号“窗户”,他写的是都市生活深层结构的纹理。源于文化的不同,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坐在窗户边观看都市的风景,坐在窗户边喝咖啡,等等,都是少见的景象。在我们的城市,窗户更多的是为了通风、采光,而不是生活场所,因此窗户不是被防盗网封锁,就是被窗帘遮蔽。大多数人的室内活动必须远离窗子。
显然,在波拉尼奥等欧美诗人的诗歌中,城市不是自己身份的对立物,也不是自己精神的对立世界,城市就是他们生命和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们诗歌中的城市就如我们诗歌中的乡村,诗歌与城市之间没有隔膜,没有冲突。这并非说欧美诗歌就不对城市文明持有批判态度,无论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都会有生存困惑或生活困难,但他们的城市之中不会有根源于户口的迷茫感和漂泊感,他们的困惑在于如何让都市人生更加美好,实现作为人的目的的全面发展。他们无需反问自己,自己向何处去,灵魂安放在哪里,是回到乡村还是栖息在城市。他们无疑也面对住房、教育、空气、交通等种种城市问题,但当他们批判城市时,他们不是以乡村和打工者的身份来批判,当他们热爱城市时,也不是以乡村和打工者的身份来爱,他们的身份和精神归宿地始终是统一的。当然,如何对待城市和现代化,是另外一个问题。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的加速推进,未来将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将成为大多数人不可逃离之地,诗歌如何书写城市将成为诗人创作的重大课题。在经历了以城市符号表达启蒙话语,以城市符号表达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困惑和精神归宿问题之后,新时代的诗歌理所当然要直面都市社会,自觉深入城市的日常生活世界,把城市作为身份之地和命运归宿之地来书写,把城市当作精神故乡来书写,如此,需要不断弥合当代诗歌与时代、与人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与隔膜,呈现新时代诗歌的新气象、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