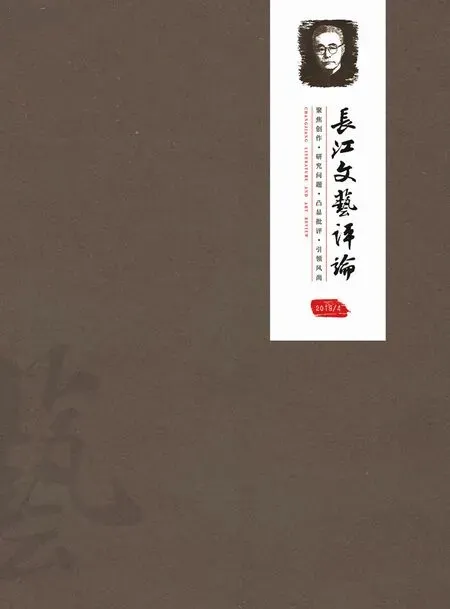论李洱小说中的动物形象
——以《应物兄》为例
◆龚映月
自先秦两汉时期开始,动物叙事便作为一种叙事类型参与到整体叙事的建构中。“五四”以后,动物叙事从古典题材领域逐渐过渡至叙事学意义上的现代文体领域,在鲁迅、许地山、沈从文、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姿态各异的动物形象。新时期以来,动物叙事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创作现象,如沈石溪、叶广芩、贾平凹、莫言、张炜等人的小说关涉到众多的动物内容,通过动物形象表达对伦理道德、社会现状的诉求与思考,并将动物叙事视作一种表现策略以凸显创作个性。
李洱并不是以动物叙事而引起关注的作家,但自创作初始,动物形象便密集地充斥于他的作品中,如《福音》《国道》中的蝙蝠,《喑哑的声音》中的乌鸦,《退了鳞的鱼》中的鱼,在《林妹妹》《你在哪》《重现个人身份》《遗忘》等多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狗,《花腔》《鬼子进村》等作品中多次被提及的毛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鹦鹉、鹅、狼狗等。这些动物形象,或作为小说的叙事主角,或与人物共同承担叙事主体,或作为人物的从属,或作为象征物参与到叙事中去,成为李洱小说叙事中的稳定构成要素,几乎涵盖了动物叙事的所有类型。李洱曾谈到《石榴树上结樱桃》电影改编的遗憾之处:“电影减少了很多动物,还把狼狗改成了猪,喜剧化效果就有所减弱。”可见动物形象在实现李洱作品表达效果中起关键作用。
2018年底,李洱费时十三年完成的长篇巨作《应物兄》得以问世。故事围绕济州大学引进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以及筹建儒学研究院的中心情节展开,人物涉及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古希腊哲学专家何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以及这些大师的众多门生和亲友,涵盖学、政、商、媒体、宗教等不同领域的诸多社会群体,尽显众生百态。小说中,李洱延续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知识生产的状态、学商官之间的关系、现代知识人的精神出路等都作出了深刻思考。
在这部长达八十五万字的作品中,动物形象之密集或许称得上李洱作品之最,野鸡、狗、猫、济哥、白马、驴、蚁狮、鼠、寒鸦、杜鹃、林蛙、土蜂、猩猩等动物纷纷登场,总数目多达百余种。这些动物形象的存在,增加了作品的文本厚度,对故事叙述以及表达效果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动物叙事入手,围绕动物形象的文化功能、动物形象与人物形象的相互映射、动物行为对情节发展的反讽与喻示等三个方面,分析《应物兄》中的动物形象于小说叙述的意义,并通过与其它动物叙事作品对比,探讨《应物兄》中动物形象的独特性。
一、动物形象的文化功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动物叙事都停留在“寓言表述”的维度上,“动物形象的塑造成为一种潜隐的‘象征符号’,承担了某些伦理化、意象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认知功能”。赋予动物形象以象征功能,使之成为一类工具性的“文化符号”仍然是新时期小说动物叙事惯用的伎俩,如莫言小说《蛙》中暗含生殖崇拜原始内涵的“蛙”,以及张炜《九月寓言》中意味着自由、流浪宿命的“鯅鲅”等,这些动物形象以其特有的文化寓意成为贯穿全文文化意象,并通过对这些动物原型的内核进行抽象化的延伸,以实现文化功能的增殖。
不同于动物形象“寓言化”,李洱选择将动物与“知识”和“经验”联系在一起。有论者将《应物兄》视作“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应物兄》堪称浩繁的文化容量。小说中,李洱通过对话、讲演、自语、讨论、专著等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引用的古今中外典籍、诗文、名著多达百余种,包括《诗经》《易经》《论语》《礼记》《史记》《十戒》《理想国》《诗学》《国富论》《江村经济》《偶然、反讽与团结》等等,涵盖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充分彰显作者知识储备之广博。《应物兄》中所引用的动物形象,并非具有某种特定的文化寓意,更多的是作为知识的载体而存在,更为具象化、多样化。小说中,动物作为知识载体频繁登场,或将其视作文字释义的对象予以解读:在“济哥”一节中,程济世对甲骨文中“螽”的字形结构与内在寓意进行了详细说明,应物兄与费鸣围绕着“犬”与“狗”两字含义借用《说文解字》与《尔雅》中的说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或作为典故被征引:乔木先生在评价程先生时,借《论语·八佾》中的说法,认为“程先生不算狮子,最多算一条狗,丧家之狗,也不是马,最多算一只羊,告朔之饩羊”,在黄兴将带来的宠物由驴换成白马之后,应物兄以《论语》中公西赤出使齐国“肥马轻裘”的典故予以解释。此外,动物还作为哲学思想的凝聚物而出现。文德斯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理念论》中的一段话,向应物兄解释黑猫与柏拉图之间的联系:“柏拉图的学说里也有某些有着重大意义的东西是不能推源于前人的,那就是‘理念’论或者说‘形式’论……如果‘猫’这个字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就不是这只猫或那只猫,而是某种普遍的猫性。”在何为看来,“猫”就是“理念”。在文中,动物形象还借史学、考古学、生物学、饮食文化、宗教学、医学等多种知识形式被提及。
李洱曾说:“我感到与重新审视已有的经验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审视并表达那些未经命名的经验,尤其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相互作用下的现代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工作便是命名,是赋予那些混沌糊涂的生活以一个清晰的形式。《应物兄》中,除了直接引用,李洱还借动物对一些新生经验进行命名,动物形象由此作为李洱创造知识的重要工具参与到文本叙述中去,作为“戏仿历史”的一个写作分支体现于《应物兄》中。小颜从“归化植物”中获取灵感,创造出“归化鸟类”这一术语,并借此类比海外定居,并传播本族文化的人;华学明接手了寻找济哥的任务,并整理出了一份煞有其事的“济哥”研究资料,对济哥的古称、习性、演变过程以及生态学意义进行了详细说明;“套五宝”作为文中一道名菜,是李洱在“套四宝”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菜品,相较于套四宝,在最外层多了一只鸿雁,而这只鸿雁,或许就是程济世的化身。李洱结合新的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对以往的知识、经验进行调整、充实,对新的社会现象进行“命名”,使之连接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使之具有崭新的现实寓意。借助动物形象,李洱再次展现了自己在《花腔》中戏仿历史、编造典故、混淆认知的能力。
在李洱看来,“掉书袋”的目的在于“增加小说的互文性,以便站在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多种知识展开对话”,并将其视作“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对话关系的一种手段”。由此看来,李洱的野心绝不止于引用与创造,而是试图将动物形象置于广阔的知识视阈中,以此为中介与已有的知识对话,以此为契机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发生联系,从而让传统文化产生新的文化话语,在贯通中窥见流变,并赋予对象多重意义,使故事拥有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由此看出,李洱并不着意于塑造某个贯穿全文的固定的动物性文化意象,而是试图在变动中探索真相。
诚如《应物兄》中所言,“人类的知识,在某一个关键的驿站总会相逢,就像一切诚念终会相遇”。小说中的动物形象便可视作一项重要的中介物,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联结辐射了书本与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知识,拓展了小说的文化含量与知识广度,并产生新的知识话语,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文化意蕴,使读者在新的文化界面上与世界对话,由此生发出对世界的崭新观感。
二、动物与人物形象
陈佳翼认为:“所谓的‘动物叙事’,并不意味动物在‘叙事’,而是隐藏其后的作家在展开‘叙事’与讲述,实则指向了人的向度,是关乎人的情感、思想与伦理等多个维度的诉求表达……是对人的自身生命伦理价值的体认,更将关系到民族思想生活与人类思想生活的大局。”动物叙事的中心仍然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文化语境的变迁,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历经多次变革,文学作品中动物叙事的自然意识、生态意识、反思意识显著增强,或将动物置于人的反面予以观照,或打破人与动物的界线,通过人的异化实现对现代文明的反思,逐渐成为动物叙事的主要特征。比如,贾平凹在《废都》中将牛塑造成为哲学家的形象,作为人类世界的旁观者思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认为只有动物的野性才能拯救被文明异化了的人类及世界;在《怀念狼》中,通过人狼互化的神秘叙事暗示了生态失衡给人类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同样,莫言在《生死疲劳》《幽默与趣味》等多篇作品中亦通过人与动物的身份转换,对现代社会变革、文明发展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在这些动物叙事中,动物性为延续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重振人类文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与此不同的是,《应物兄》的动物并不具备精神力量上的优势与生物性上的拯救功能,而是与人类处于平等互补的地位,以对人物的生物性特征进行还原,并作为人物的衍生物与附属品为人物性格的完善作出补充。
李洱喜欢将人以动物作比,《应物兄》中与人物相关的动物性描绘,有对人物外貌的刻画:双林院士“脸上的皱纹都纤毫毕现,乍看就像八爪鱼的触须在四处蔓延。脑袋上汗津津的,又像是一头刚浮出水面的海豹”;有对人物的整体比喻:“他突然觉得,她就像是一只鹤。她像鹤一般移动着轻盈的身体,如将飞而未翔”;也有对人物知觉的形容:“那真是奇痒难耐,好像养了一窝跳蚤。搔破之后,问题更复杂了,好像除了养跳蚤,还顺带养了一窝蝎子”,“在去见董松龄的路上,这个问题就像一只鸟,栖落在我们应物兄的肩头……那只鸟还不时地啄一下他的脑门,使他感到一阵又一阵尖锐的疼痛”。李洱注重人身上的动物性本质,并习惯结合动物形象进行联觉想象彰显出来。
除了直接对人物进行动物性描写之外,《应物兄》中的人物几乎都有宠物。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甚至不同专业的人饲养的宠物各有区别,饲养宠物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乔木收养了一条杂种京巴,姚鼐在二里头养野鸡和土蜂,何为养了一只黑猫,葛道宏在办公室放了几只蚁狮,程济世幼时养了一只济哥而后对其念念不忘……每个人的宠物都有其主人特别的精神属性。作为《应物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小说涉及狗的品种多达上十种,乔木的杂种京巴、铁梳子的纯种金毛和蒙古细犬、季宗慈的黑背和藏獒、雷山巴的昆明犬、贵妇的吉娃娃,以方便作者对主人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提示和补充,以体现了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经济实力的人的特征以及对宠物的不同需求。这些动物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物,从侧面对人物形象进行补充,作为社会活动的衍生品对主人的特性予以旁证。
除此之外,这些宠物还暗含着作者对人物的认知隐喻,它们或是人物形象人格的外化,如葛道宏的养的蚁狮,和他一样是“天生的阴谋家,天生的杀手”,季宗慈时不时流露出来的那股傲慢劲儿,除了资本力量在作怪,或许还受到了黑背和藏獒的影响;或是某种思想信念的物化,如吴为的宠物黑猫,于她而言,就是一个永恒的理念,看到黑猫,就像看到了柏拉图;或是人物某种存在状态的具象载体,如栾庭玉家里的那两只鹦鹉,将他常说的口头禅挂在嘴上,正是对他日常生活状态的侧面佐证,程济世和敬修己常居海外,在异国他乡传播儒学,正如同“归化鸟类”,北岛以丧家犬自嘲,同样是对海外生活经历的总结。动物形象身上所寄寓的深切用意,在黄兴身上得以充分体现。黄兴在小说里也被称作“子贡”,是一位商人,但也对程济世执弟子礼,这让人联想到子贡和孔子的关系。黄兴最初养驴,他将驴视作他的“广告”,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暗示自己金钱、文化的特权,同时又代表了一种中庸哲学:人家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后养了一头白马,开拓宠物产品市场,将动物穿戴赋予区别身份、表达信仰、遮蔽弱点、突出个性的社会需求。黄兴的宠物,既对他的身份地位提供了佐证,也彰显了多种文化集中作用的混杂状态,同时也折射出官、学、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应物兄》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动物品种。
在其它动物叙事相关的作品中,极少出现有像《应物兄》中如此普遍的宠物饲养现象,李洱敏锐地注意到了当今社会宠物饲养的热潮,窥探到该现象形成背后复杂的文化、心理、社会运行机制,并以动物性对人性进行佐证与对照,从而深化对人性的理解与表现。
三、动物行为与故事情节
梁鸿说,李洱的小说中“解构与建构,陈述与思辨,肯定与否定是同时发生的,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反讽修辞学……这既是对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的书写,同时也形成一种新的语言风格,各种充满悖论的意义不断包裹着往前走,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意义空间”。对于这一点,李洱如是解释:“我感觉这倒是我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奇迹性的发现。知识分子生活好像时刻处于一种‘正反合’的状态,各种话语完全搅和在一起的,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剪断了也还是理不清。”
正如莫言习惯以大量动物为手段塑造魔幻语境,以获取“狂欢化”语言效果,在《应物兄》中,李洱也同样借助动物这一道具,多次运用这一“反讽修辞学”,以凸显知识分子话语生活中的矛盾。在程济世看来,《螽斯》于《诗经》的重要性在于“螽斯”是借虫子写人,虽然妻妾成群,但是彼此之间不嫉妒,相处和谐融洽,写出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和伦理观,体现了儒家对于人类社会的祝愿。由此,螽斯也被程济世视为和谐共处之楷模。然而在后文中,为迎接程济世特意从河北易县和湖北荆门弄来的蝈蝈一夜之间尽数死亡,动物学家华学明给出的解释是互相撕咬致死,其惨烈的死状与《螽斯》中所描写的和谐画面完全相异:“有两个咬在一起的,还有三四个咬在一起的。地上到处是折断的腿、翅膀、须子。有的剩下了半个头,有的则干脆没有了头。应物兄捡起了一只半蝈蝈:一只和半只在一起的蝈蝈。它们的眼睛依然像晶体那样闪亮,似乎还在对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动物学专家华学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济哥重出于世,却意外得知济哥尚未灭绝,在多重打击下最终疯癫,从中也可以看出李洱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反思。程济世多次提到对寒鸦怀有特殊的感情,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分不清寒鸦与灰喜鹊,也认不出寒鸦的骸骨。知识分子的认知混沌在对珍妮的论文《儒驴》的讨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珍妮看来,驴子的诸多习性使它成为动物中的儒家,并撰写了《儒驴》一文。在对这篇论文的讨论中,应物兄的一众弟子围绕着《黔之驴》进行了文本分析,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生搬硬套将驴子视为智者,并将其与知识分子进行类比。费鸣和范郁夫则作为解构者插科打诨,从旁讥讽,从而实现了对驴子本质认识的建构与解构的双线展开,众声喧嚣中反讽于无形。《应物兄》中的动物作为沟通知识与现实的媒介,还原知识产生的过程,并作为暗线参与文本建构,伏在文本里伺机而待,不动声色地予以反讽,揭露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将动物表现作为作品的隐性结构与故事情节互相映照,是动物叙事中的常用技巧。贾平凹在《古堡》中,便将麝与张老大的命运紧密对应,以麝的遭遇预示张老大的现实境况。这一叙事手段在《应物兄》中得以沿用,并生发出新的特质:《应物兄》中多次借动物画面以预示故事情节走向,并与之形成对照。芍园宾馆院子里的那几条狗的状态,隐晦暗示了日后众人相处的场景;医院旁水泥路上在雨中“选择了情欲”的那两只猫,正是季宗慈和丁宁举动的预告;铁梳子的蒙古细犬,分列于黄兴白马的两侧,在麦田里相伴而行,提醒着众人两人接下来在商业上会有紧密合作。在乔木的建议下,为改掉多嘴多舌的毛病,应物兄无奈习得腹诽之法,与之对应的是小狗木瓜也在乔木先生决定下最终被阉割,知识分子失语之后正如被阉割的动物,不再具有知识繁衍的能力。与众不同的是,《应物兄》中的动物行为与人物情节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只是作为故事的隐藏暗线,随着故事的发展自然展开,动物行为与情节之间的联系由此被弱化。
动物与人物情节的并列发展,为观察人类行为的生物学意义提供了便利,由此还原了人类行为背后的动物性本质,从而加强叙事的自省力度与剖析深度。而动物行为与情节之间如有若无的联系,也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咀嚼空间。
王鸿生将《应物兄》叙事动力的来源比作一阵风:“风是随机的,也是无形的。一个粗线条的故事框架,无数难以预期的情境,一经‘风’的吹拂、感染、点化、席卷,便散枝开叶,舞动起来,一切眼见的、耳听的、心想的,都纷纷涌入,旋转,世界在自我绽放,自行吐露,随风而来的人、事、物,挤挤嚷嚷,相互裹挟,小说的重点便落在对它们的捕捉上。”动物形象,便可视为这股风中的一些定点。它们“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和人、事一起,构成了万物共生的状态,并将“当下”与跨时空、跨领域的文化和现实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勾连起来,在这个场域中,这些动物形象都具备了某种文化意义。借助这些动物形象,李洱呈现了知识分子在应对纷繁世事时的千种姿态,透射出儒家文化在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多重困难,在实现文本意义的增殖的同时,强化了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并使得故事情节具有多重寓意,极大扩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应物兄》中的动物叙事,突破了动物形象与文本要素之间稳定的建构关系,彰显出李洱动物叙事的独特个性。
注释:
[1][3][7]陈佳翼:《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72页,6页。
[2]李洱访谈,来源于http://news.163.com/13/0406/01/8RO9SKCU00014AED.html。
[4]李洱、魏天真:《倾听世界的心跳——李洱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4期。
[5]李洱:《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6]王宏图:《李洱论》,《文艺争鸣》,2009年第 4期。
[8][9]李洱、梁鸿:《“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建构》,《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0]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2018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