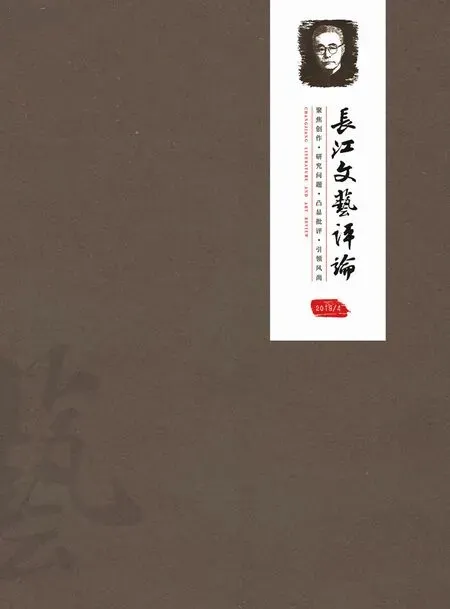纪录片创作中的“作者”意识
——张以庆纪录片研究
◆司徒兆敦
在中国纪录片创作群体中,张以庆导演是值得研究的一位。我们对有特色的纪录片作者及其作品进行研究,不是要树立一种风格和创作方法,而是要研究多种纪录片创作风格及创作方法,推动中国纪录片多样化的发展。在一次纪录片讨论会上,有观众问:在纪录片创作中究竟客观性重要还是主观性重要?张以庆毫不犹豫地说:既然是作品,当然是作者最重要的,纪录片是纪录片作者的记录,自然会有他的态度和他的立场。
我的纪录片课通常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就比较慎重,因为纪录片包括了“对现实的描述”和“有创意性的安排”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强调作品的非虚构和客观性,是创作的前提,后一部分是纪录片作者“创意性的安排”的自由,这两部分既矛盾又统一在纪录片作品中。我们很难说,纪录片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究竟哪个更重要。
在《舟舟的世界》的发奖会上,碰巧是我为张以庆导演颁奖,下来以后张以庆告诉我,当年我曾经教过他,我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提到了一部叫《失去平衡的生活》的影片,那是1983年美国导演高夫瑞·雷吉奥的纪录片,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但是把导演对当代世界面临的所有危机和他的思虑表现得清清楚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通过视听语言课进行电影的普及工作,这部纪录片是我的教学参考片中重要的一部,我没有想到它对张以庆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这次和张导演“对上号”以后,他就成为了我很好的老师,他用他的纪录片告诉我,纪录片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纪录片不能仅仅停留在“纪录”和“纪实”这个简单的表述层面上,它还应当在表达作者思想和美学观方面影响观众。在我的印象中,张以庆导演是非常重视影像的质量和效果的,记得我曾经认真地向他推荐过日本本桥成一导演的《纳迪雅的村庄》,那是一部拍摄了许多年,表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地区留守村民生活的纪录片。张以庆导演看了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他说像质太差,不看了。我觉得他并不理解中国纪录片人找到好片源的艰难。后来看到他在多处表达:创作者要“有点理想主义”,要追求“有价值的东西”,他自己“一生追求美”,联想到他对制作精致的《失去平衡的生活》的酷爱,我多少理解了这位制作纪录片超级认真的导演了。他要把自己认识到的、经过筛选的、有含义的、优质的影像呈现给观众,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观众的尊重。我把他视为纪录片的“作者意识”的代表性人物。
我的根据是:一、他的纪录片选题是非常慎重的,从长片《舟舟的世界》《英与白》《幼儿园》到《君紫檀》,包括短片《前世今生》和《听禅》,都是经过他认真选择的题材和拍摄的对象,这些作品和他的经历、他的心境、他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不是在拍摄别人,他也是在拍摄他人的同时记录着自己。或者他是要借助别人来表达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他用镜头“书写”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展示个人内心世界。我在看他的作品时,就像在读一本书,一本解读和剖析张以庆的书。由此,我相信他是孤独的,他无声地坐在摄像机后面,长时间拍摄,无尽头拍摄,再拍摄……没完没了,他熬人也熬自己;在后期的剪辑阶段,他又是默无声息地坐在那些拍摄素材前面,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审看,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张以庆导演的工作现场,这只是我的猜测。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每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周期会如此的漫长。我的合理解释是:他是在和现实存在的拍摄对象,和留在影像上的拍摄对象,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和沟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是最幸福的。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常常是不被理解的,有时甚至会受到莫名的伤害。张以庆在残疾人艺术团体验生活,自筹了五百万资金,另有八十万还要用作为《千手观音》的团队再编排一个《青衣》的舞蹈,并准备为艺术团拍摄一部纪录片,奉献给中国残疾人艺术事业。剧本已经写出来了,名字叫《观音》,蕴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应“静观世音”这四个字;二是因为舞者大都听力不好,甚至没有听力,比如领舞邰丽华就只能观看世界,听不到声音。那时残疾人艺术团的《千手观音》已经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以庆希望用一部中国传统戏曲载歌载舞的节目为残疾人艺术再添一把火,在片子表达方面,他也颇费了心思和功夫,想把“听觉”拍出来。但遗憾的是他的真诚却被误解了,有人怀疑他想利用残疾人艺术团的声望来抬高自己。我参加了那次在上海的谈判,我目睹了张以庆对残疾人艺术的热忱,但是历史的流毒或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对有的人甚至是不能改变的。那时就有人对我说:“怎么会白送你八十万,还搭上一台节目,自己能不捞好处的?”听到这话我很伤心,我希望再做一些努力,让张以庆实现他的愿望,但是他表现得非常平静,只说了一句“不必了”,就离开了,我可以想象他离开这个非常热爱的艺术团时的伤心。直到十多年后,我看到他的《君紫檀》,看到其间插入的那些谁也不明白的中国戏曲片段时,我激动了,我知道他爆发了,他积压的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情,终于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作品中爆发了。
二、“作者电影”,是坚持作者立场的电影,因为“坚持”,它又常常是不被人理解的,故事片如此,纪录片亦如此。记得在上世纪田壮壮导演的一句话:“我的电影是为下世纪观众拍的”,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好了,他说的“下世纪”已过了十多年,当然,嘲笑之声少了,思考的多了。我对张以庆纪录片没有使用“作者电影”,而只是把他作为“作者意识”的代表,是因为他一贯的“作者意识”追求,坚持影视作品的作者尊严和作品的文化思想追求。他明确指出,纪录片不仅仅是资讯,更不能是“纯娱乐”的产物。他要求纪录片要有内容,要言之有物,要有感而发,纪录片作品视听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要有一致性,他追求作品的理想与人文关怀,同时要在影像和声音构成方面传递相应的审美诉求。张以庆的“作者意识”在创作中顽强地坚持着,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赵倩称之为“纪录观”,我也是非常认同的。《舟舟的世界》是孤独的张以庆和同样孤独的舟舟的一次沟通尝试,舟舟是面对音乐,张以庆是面对影像,这种交流让他们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在这部由张以庆亲自撰写解说词的纪录片中,解说词是大受欢迎的,我想这和电视传播应当是有关的。张以庆似乎也发现了,这种语言交流的直接性的优点,但也带来过于表面化问题,因此到了《英与白》的创作阶段,张以庆抛弃了利用旁白和解说词的“捷径”,完成了心对心的直接交流。这在纪录片创作中无疑是一次突破,难怪审查人员看片以后会长时间地沉默。我看到一次采访中,张以庆真诚地表达他的感谢之情,感谢电视台领导在反复审看《英与白》之后给与的宽容,这对认真创作的纪录片作者又是多么大的温暖啊。的确,我们不应当以我们“懂不懂”或者“喜欢不喜欢”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志,我们应当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去对待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作品。文艺领导对创作者的宽容和理解造就了张以庆,这是“作者意识”的纪录片成长的重要条件。
印象中的《英与白》简单而枯燥,一个杂技团,一间饲养房,一只雄性熊猫(英),一位女驯兽员(白),一个邻家女孩(娟),一台电视机,一台录放机……单调的生活,没有激烈的外部动作,这就是通常电影创作中说的“不好看的电影题材”。但是,张以庆正是认为在这样单纯的设置中,可以实践他对电影语言的探索。他说过:“孤独、情绪、苦闷、挣扎、茫然……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可以用影像去表达,但不是按原来的手法、方式、语言样式去纪录、去表达了。”他说得直接而明白,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为了实现创作意图,纪录片作者是可以对拍摄进行设计和安排的。
我始终怀疑饲养房中的那台电视机和录放机,还有邻家那个小女孩“娟”,都是作者为了表达思想,处心积虑的设计和安排。张以庆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但是他清楚文字语言和电影语言是不同的语言表述体系,尽管它们在其中一些部分会有交集,但大的方面是不同的。例如,在声音描写方面,我们形容安静,用“万籁俱寂”“死一样的寂静”“阒然无声”……,但是电影不可能用完全无声来表现“安静”,因此我在教授电影《视听语言》课程时,引用电影前辈的片例时说:电影是只能用有声来表现无声的。
《英与白》在视听语言方面的探索是超前的,在纪录片创作上应该是一个突破。在影像方面,它运用了“主观镜头”,甚至出现了熊猫的“主观镜头”,从影片开始就出现了倒置的人或物的镜像,很多镜头是以“栅栏”为前景拍摄的,慢慢地我们发现了这种我们不习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舒服的镜像是带有暗示性和隐喻性的。张以庆希望通过这种强制性的镜头让我们和他一起观看,一起感受,一起思考。纪录片和专题片最大的区别就是:纪录片只提供图像与声音,它要把作品的阐释权交给观众。纪录片的这种创作特点,也体现了纪录片作者对观众认知能力的信任和尊重。需要说明的是,张以庆为观众提供的影像和声音不是随意的,它是经过认真选择和排序后提供给观众的,就这一点,的确会引起不同的意见。我承认:只要是有价值、有含义的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一定是创作者精巧的设置与安排的结果,“作者电影”更是这样。
对此,张以庆曾经对我说过:把自己都不明白的、未加整理和编辑的素材交给观众,是不负责任的。艺术创作是严肃的,甚至是神圣的。我们从《英与白》的声画构成中可以感觉到作者与“英”、与“白”(还包括窗外的那个小女孩),都是同样的孤独,同样渴求交流与关注的。张以庆希望通过电视机和录放机来打开这个封闭的空间,希望保持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但结果恰恰相反,孤独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孤独。于是我们发现了,那些透过栅栏相互观望的镜头原来是带有象征含义的。我们不禁要问:原本应当是属于大自然的自由自在的熊猫,为什么要关押在笼子里,甚至要变成人类的“玩物”?究竟是谁更加地不自由?我们的确可以通过这些镜像进行长时间的思考。是的,张以庆的纪录片,可以让我们透过作品直达作者和观众的内心,甚至是拍摄对象的内心。《英与白》中的“白”在看完片子后给张以庆写信:“我一直以为只有我父亲了解我,可看了片子,我发现您走进了我的内心。”纪录片是可以通过观看带给观众思考的,这是张以庆纪录片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他不允许自己的纪录片进展过快,他要给观众留下思考的时间。《幼儿园》这部纪录片更加极端地把成年人和幼儿平等地摆在同一张板凳上思考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的说教,但是非常严峻。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思考的纪录片”,是观众和纪录片作者一同思考的影片。
三、《君紫檀》是张以庆导演构筑纪录片的“声画交响曲”的大胆尝试。我记得在《前世今生》创作之后,他对我说过“以后不拍纪录长片了”这样的话,他没有说原因,我感到很惋惜,可能是纪录长片创作太过消耗他的精力了。果然,他到佛山拍摄了纪录短片《听禅》,制作非常精致,我隐隐感觉到他是通过作品和历史,和自己的内心在对话,当然,也是无声的对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消失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几年过去,他到青岛讲学时对我说,他正在拍摄一部长纪录片,是关于传统紫檀家具制作工艺的。他兴趣盎然,我却很难想象家具制作会有多大的趣味。
然而《君紫檀》出来后,不同凡响。影片放映之后,张以庆导演的第一句话是“希望大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部作品”,由此可见他的忐忑。我看到纪录片学者宋素丽的一篇评论文章《可见君心即我心》,这是对《君紫檀》的审美追求与文化自信的有说服力、有专业水平的分析文章,我非常认同她的观点。
宋素丽的论文中提到,2008年她和张以庆合作过一篇文章《我还可以那样做》,如今看了《君紫檀》,“他又一次用作品证明:他还可以这样做”。宋素丽用“一贯主题:尊严和尊重”“表达形式:天马行空和诗意现实”“文化自信:传承与创新”来概括张以庆纪录片作品的终极追求。在文中,她引述了张以庆在《君紫檀》的导演阐述中的话:“纪录片中的上乘之作,是把人和事作为载体,传达生命观、价值观的东西,我将苦苦寻找独特的影像语言,来探寻我们这个民族劳心劳力者的心像,和立于世界之林独有的文化哲学。”这足以证明张以庆在《君紫檀》中赋予了他的“作者意识”多么大的期待。
张以庆导演在这里强调了“独特的影像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记得他还说过:“纪录片故事性太强,本身就违背真实”,这也是和当下纪录片创作要求“也要讲故事”背道而驰的。美国纪录片导演伯纳德的专著《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在中国影响很大,纪录片创作领导和投资人抓住“也要讲故事”,变成了“必须讲故事”,甚至要求纪录片作者在上交题材申报材料时要附上故事大纲,这让纪录片作者无所适从。我在纪录片创作课程上是不强调“讲故事”的,我只是承认生活中“有故事性因素”,纪录片的“故事”是隐性的,是带有观众想象参与的,不是一个显性的,明白无误的“故事”。纪录片要求“也要讲故事”或“必须讲故事”有可能违背纪录片规律,这是必须慎重对待的。
张以庆从《舟舟的世界》的努力要讲故事,到《君紫檀》的完全放弃讲故事的自由境界,是他完全放弃了“讨好观众”,追求崇高的一步。他所关注的人物及其心理状态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非常可喜的。无论舟舟、女驯兽员“白”都是无穷孤独的,都在寻求交流、沟通和宣泄的机会。到了《君紫檀》,张以庆关注的是以顾永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紫檀家具工匠的“工匠精神”,作品长时间地、非常仔细地表现工匠们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打磨家具的每一道工序。这让我联想到伊文思在拍摄玻璃工匠时的情景,他从一遍又一遍吹玻璃的简单动作中,思考到生活中被忽略了的人文关怀。张以庆看到的工匠动作,仿佛是用手在触摸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把艺术家的情感融化在可视可听的具体影像中,张以庆在拍摄中感受到生命的伟力,它不再是孤独的哀怨者,他是生命的歌者。我始终相信,纪录片创作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经历、相互感染和共同成长的艺术。张以庆通过《君紫檀》在实践他的纪录片声画交响曲,这里有对电影先辈们的致敬,有类似库里肖夫的实验,有爱森斯坦的“杂耍”,把现实的与历史的交织在一起,让我们从紫檀家具的制造过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工匠们的“工匠精神”的伟大。正因此,当片尾字幕升起时,张建、刘建、梅小兵、李祥……十几个普通工匠的名字出现的时候,那是张以庆带着我们向他们真诚的致敬。我们常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特别是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人们只是“一群人”,把他们的名字像明星一样纪录在案,是张以庆历史观的鲜明表现。
张以庆说他“不会讲故事”,“喜欢文学,有点理想主义”,“不读哲学,但总是在做有哲学追求的片子”,“文学潜移默化造就了我”,他总结自己的创作时很有感触地说:“进行艺术创作,一定要在生活中留出很多空白。哪怕就是你无聊,也是一种准备,就是留白。”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要给自己“留白”,不把自己的创作说得太“满”,太完美,尽管他“追求美”,但是他理想的美常常是遥不可及的。
我认识张以庆导演很多年了,我也是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他的,他如此强调纪录片创作中的“导演意识”最初也是让我怀疑,甚至是反对的。但是他坚持了,通过创作实践引起了纪录片人的思考和争论,这对纪录片创作应当是一件好事。在表像真实和本质真实,在再现现实和表现现实之间,我们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的,只要我们坚持纪录片创作在非虚构前提和在表现的主要内容必须有事实的依据下,我们是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的。张以庆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是:纪录片也可以是这样的!
创作之路应当是纪录片人在创作实践中开辟的,不是根据某个权威的定义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