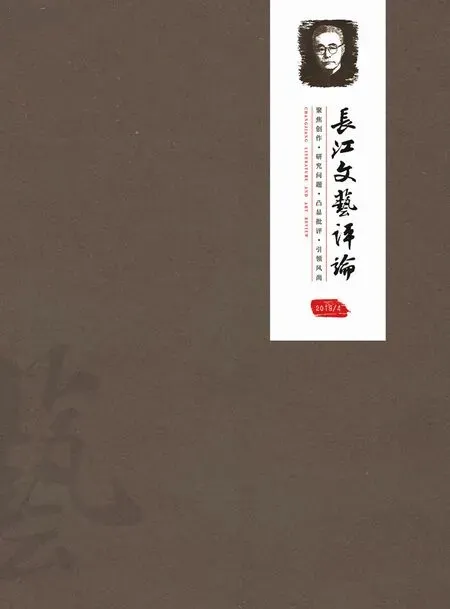平庸化写作的伦理黑洞
———文学现场迹象谈
◆王朝军
“哇,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是真的好!!!”好久没听到如此这般发自心底的声音了。大概率的表情是颔首或故作思索状,让对方摸不着头脑。那就成,目的达到了。对得住别人的沉默,总比对不住自己的张口看起来柔软,不伤人。
我一般是不愿意伤人的,尤其是面对作者的眼神。这眼神里有期待。尽管他可能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庄严宣誓:评不评是你的事,你说好不好关我屁事。但他仍藏不住“被赞许”的心火。不信你试试,说他写得不好,哪里不好,为什么不好——后果是严重的,你首先得掂量一下你的承受度。
他在文学现场摸爬滚打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经历了很多事,读了很多书,认识了很多人。按理说,我应向他走过的历史致敬,同时也应向他的作品和他本人致敬。可我刁钻得不识时务。作品不好,他攒下的历史经验对文本的意义何在?他本人之于文本的伦理价值又从何而来?这些看起来吹毛求疵的“编排”,却有可能让我们深入小说写作的底部,揪出几棵陷作者于平庸的“毒草”。
当下的小说在拿来“正确”方面毫不费力,因为正确就摆在那儿,是人人都可以见到的。小说家只要给正确描出形状,涂上炫目而复杂的情节,便成了一个自足的结构,无须再去追问哈姆雷特式的生死疑难。因为在小说中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人从诞生起就面对的可能性被贬逐到了文本之外,你无从选择也不必选择,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什么时候该发生,什么时候该凸显,什么时候该曲折,什么时候该激越,什么时候达到高潮……都在可预知的疆界,只要你心中有座灯塔,就不要怕迷失航向。这座灯塔不是作者建的,他仅仅是向你指了指,你就立刻明白,哦,在那里。
正确,是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提纯出来的“合理”,是行为指向的最大公约数,可它却是小说家面对的最“伪善”的敌人,因为人的行为和他的肉身一样真实,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并不是必然的想象,而是无数个偶然构成的现实。这也是小说家时刻面对的“现实”。现实因为有了各种可能的脸孔,而给小说家提供了建造博尔赫斯笔下迷宫般魅力的可能。遗憾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在许多小说家的记忆中被有意无意地删除了。他们懒得去形而上地“挖空心思”,也就将形而下的叙事搞成了争相“正确”的赛跑。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写作,也是必然导致平庸的症结所在。因为没有“不正确”“不应该”“不规则”,因为它所提供的永远跳不出现实和理性的区域。它的生命已然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死掉了,剩下的那些已尽失文字的尊严。
当然,我们不必怀疑它结构的紧致、语言的顺溜、细节处理的老到、人物的纯粹……总之,它不缺的就是叙事元素,精致得就像一只无任何杂色的玉杯,或老年画上那个抱着金元宝的娃娃。美则美矣,可又能怎么样呢?它们是无生命的,死气沉沉的,它们越是完美得无可挑剔,就越是暴露出它们“不食人间烟火”。鲁迅说《三国》把诸葛亮写成了妖精,是因为他也看不惯孔明先生被放在“典型”的烤架上,随意任罗贯中拨弄。“妖”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它原是一个无灵魂的物,在洞中修炼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阴性十足,可以呼风唤雨,幻化人形,就是说成“精”了。它的“精”里面满是“精打细算”——精确的预测、精明的算计、精细的考量,甚至它的肉体也是经过精炼而成的,要不孔明怎么会娶个黄发黑肤的丑媳妇呢?周公之礼免了,妖精要什么老婆!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是聘一个吧,那就聘个最丑的,让“孔明妖”在妖道上走得更远。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鄙夷罗贯中,这不是他的错,他实践了中国古典小说在当时能够达到的宏大叙事的应有高度,他为“历史人物”向“历史英雄”的文学探险提供了范本。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小说在经过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的精神启蒙后,在欧风美雨一百年来的不断洗礼下,我们的小说家竟然杀了个回马枪,转向自给自足的小农写作区域,说好的开放呢,说好的胸怀呢,说好的兼收并蓄呢……我说这话,一定会有人骂我刻薄,这种紧致的结构、流畅的语言、老到的细节、纯粹的人物,哪一样不是得自西方?是的,如果你坚持这种“表象崇拜”,我只能闭嘴。然后,根据我的判断,你可能更愿意听一个故事来缓解双方的尴尬。那就让我投其所好,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篇小说是这样的——请恕我不写出它的名号和东家,因为我也不知看到过多少篇类似的小说,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让我的大脑无地自容,我就像神功附体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一句话,看这样的小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大脑。
故事发生在一个荒蛮之地,阴森中透着寒厉,或者还有难以捉摸的僵持。恰好是冬天,极冷,冰把湖面封住了。这样,孩子们在冰面上嬉戏就成为可能。其中一个孩子,发现一条鱼冻在冰层里,他执着地朝冰面哈气,试图帮鱼脱离困境。他当然不会成功,他的煞有介事是为了引出突然闯入的两个成年男人。一场惊心动魄的沉默战就此上演。如同古龙小说的改编剧,一个硬汉拔枪指着另一个弱小者的头颅。现在我们知道,硬汉是个军阀,弱小者是个郎中。为什么?你心中充满问号。作者恰好开腔了,他告诉你:一切都因为一个女人。她危在旦夕……
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啊!是这样吗?后来呢,后来呢……抱歉,你的追问是合理的,但不是有效的。虽然“她危在旦夕”不是文本的物理结尾,却在心理意义上已经结束了。只要你墨守“合理”的想象疆域,按图索骥,就一定会找到省略号后面飞奔的马来。这就像贾平凹在《废都》里设置的那一个个方框,它们会直接撩起你的肉欲。如此直接,无须过渡和展开。恰恰在这里——恰恰是“她危在旦夕”引起的这种动物性的应激反应,剥夺了你的兴趣,也让文本的意义空间一笔勾销。
那么,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给你剧透了——“马”上有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追逐着她穿过历史的恩怨,最终和解。不消说,开头那把愤怒的枪,倾斜了,犹疑了,摇摇晃晃起来,丢了魂似的将子弹射在冰面上。
我们把这种装置性写作,叫做套路。它是大棚蔬菜,长在哪个大棚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应该长在大棚里,应该有严格的作息、相同的规制,并符合种植者的成本预期。它们个个饱满,样样鲜艳,但独独缺了些味道。那是一种不期而遇的风雨乃至旱涝才会冲刷出来的味道,是通向深邃的意义洞穴的味道。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它的身上遭遇了各种莫测的可能性,即便它不美,不精致,不规则,但它依然故我。总之,它具有无比丰富的可塑空间,它在文学的疆场纵马驰骋,参与和见证着各种冒险,接连不断的偶然助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味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气味”。
好吧,如果你有洁癖,对这种“气味”不感冒,或从来就不知小说的“气味”为何物,那么我敢断定,你会像丢失钥匙一样丢失小说创作的最基本伦理,你的写作也永远称不上是创作。是的,你有一块自耕田,你日复一日地在它里面刨食,但你对它的感情只限于价值的交换,你从未想过哪一天爆发出某种生命的冲动和力量,将它几乎是无限的剩余价值开发出来。在生活的土壤上,你缺乏资本家的“贪婪”,更缺乏对它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的起码尊重。你的平庸不是源于这片土壤的无意义,而是源于你在丰富的意义土壤上让本应旺盛的叙事本能无限期搁置。
老实说,我不愿意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此小说与彼小说摩肩接踵,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它们叫嚷着,推搡着,挤兑着,都试图把自己形塑成中心和主体。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堵石墙面前(《地下室手记》),却没有一个能鼓起撞击的勇气——看看即使是粉身碎骨,这“粉身碎骨”里有多少鲜活的成色。它们左顾右盼,集体性地歇斯底里,骂骂咧咧,又不约而同地退了回去。它们说这是符合逻辑的,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本能反应。可问题是,当它们对“理所当然”产生认同感的时候,就是认同了自己的麻木和冷漠,认同了自己的“习以为常”,平庸化这个幽深而舒适的黑洞,迟早会将它们身上残存的一点叫做意义的东西全部吞没。文学的诗意品格消失了,真相世界关上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