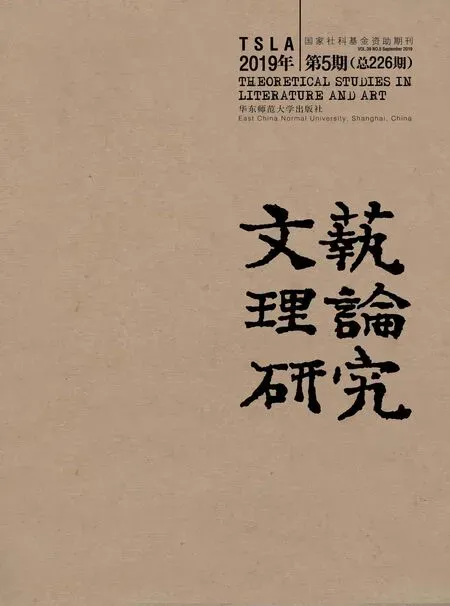论同光体诗人对同光体诗歌特性的理论构建
张晓伟
“同光体”一名,出自陈衍和郑孝胥的谈论。同光体内部又可分为两个或三个小派,但既然有“同光体”之名,它在诗论家心目中,就自然有相对统一的特性。对同光体的特性进行理论构建,其最大功臣是同光体中的理论家陈衍。沈曾植与郑孝胥的诗论,数量虽不及陈衍,在某些问题上的理论深度则有以过之。陈三立的诗论风格较为独特,他也有意无意地涉及到了同光体特性的问题。比他们更晚的诗论家,关心此问题的,当以汪辟疆和钱仲联为代表。他们在民国时期的相关论述都受陈衍影响,又形成自己的偏向和特色。
同光体曾被冠以复古、保守的评价。从政治观点来看,他们或许是比“诗界革命”派更保守一些。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从艺术角度去审视当时的诗歌,却会发现“诗界革命”派的艺术大都是古典型、唐型的诗歌。从道咸时代宋诗运动萌生出的同光体,在艺术上则蕴涵了中国传统诗歌内部的一种深刻的革新力量。即便就对新时代的感受而论,他们也有很多不可磨灭之处。他们的感受,以负面的居多,但谁说负面的感受就是不深刻的呢?
要了解同光体在艺术上的这种革新力量,我们需要回到陈衍、沈曾植、郑孝胥那代人对同光体或者说对自身创作的认识上去。
一、 对前人诗学中诗歌“正体”的主动反拨
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诗论家,利用了很多组二元对立的诗学概念来阐述同光体的诗歌创作。比如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风”诗与“雅”诗,“清切”与“僻涩”,“广易”与“艰深”等。同光体在这几组对立概念中,大抵都属于后一种。整理他们的这些概念,进行重新组合,大致可梳理出他们心中的同光体特性。稍加阐释,便可成为我们今天对同光体特性的新思考。
同光体诗人用到的诗学概念很多,单独分析会不免破碎。要综合理解他们的诗论,首先要对前人特别是明代以来的人形成的诗歌“正体”观念,有个了解。从而就能发现,他们动用了多种诗学概念,却将自己定义为前人所谓“正体”的反面,进而建立自己新的诗学。前人的诗学,大体以唐诗为正体,以宋诗特别是江西派的诗为变体。其背后的理由,是唐诗富于音乐性、抒情性,文学体制上圆美流转。这个观念在明代以后尤为突出,明代的前后七子和杨慎、胡震亨、王夫之等人,都参与了相关的理论构建。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是始于宋代以来的人对宋诗的批评。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48),是著名的论断。所谓“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就是说宋诗缺乏唐诗的音乐性和抒情性。刘克庄说江西派“锻炼精而情性远”(26),则是直接以传统性情说的立场来反对江西派的。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近时学其诗者或未得其妙处[……]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丁福保182)李梦阳《缶音序》:“其词艰涩,不色香流动。”(《空同集》卷五十二477)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宋诗不入弦歌。”(丁福保1146—47)都是一脉相承的说法。
清代以来的神韵派和性灵派,不论他们具体的诗论有多少变古之处,也都处在这个诗学“正体”的脉络之中。神韵派标举的是盛唐王维、孟浩然等人,对“拗捩”“艰涩”风格的诗歌,自然不会太感兴趣。性灵派所说的“性灵”,许多时候与“性情”相同,而性情说是始于儒家诗学的传统命题。历史上凡是主张性情、性灵的诗派,一般都以直抒胸臆、语言清浅通俗为特征,与上述诗论中的宋诗特征,是相反的。
这个诗歌“正体”观念,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一个民族的诗歌在其初始阶段,一般都脱胎于歌谣乐章,还具有歌词的特性,因此富于抒情性、音乐性,体制流美而不艰涩,是很自然的。只有书面化的诗歌发展到相当阶段,才会出现重视学问、风格艰涩的诗。严羽说宋诗注重学问和议论,陈岩肖和李梦阳说宋诗“拗捩”“艰涩”,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论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批评的这些宋代诗人,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诗是远离性情、拗捩艰涩的。如果去看黄庭坚和陈师道的诗论,会发现他们的诗论比诗歌创作“保守”很多,是比较传统的儒家诗论面貌。
只有到了晚清的宋诗派,尤其是同光体那里,他们才对始于宋诗、被后人以贬义色彩提出的这些诗学特质,重新审视并明确用以描述自己的诗歌,又继续进行理论发展。这个从被动的批评到主动的构建,是宋型诗学极为重要的历史变化。
首先他们明确把自己看作神韵派和性灵派的反动。陈衍《近代诗钞》祁寯藻下的评述中,说道咸间宗宋诸家“不规规于王文简(引者注: 王士禛)之标举神韵”(《陈衍诗论合集》879)。祁寯藻是道咸宋诗运动中的重要成员。《石遗室诗话》卷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诸老始喜言宋诗。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李莼客诸公稍为翁覃溪,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18)“张船山、黄仲则之风”即乾嘉性灵派诗风。陈衍是“同光体”一词的发明者之一,他说:“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18)苏堪是郑孝胥。实际上不仅是不“专宗”,陈衍内心未必以盛唐诗为诗中最高。这体现出对他明代以来唐诗学的一种反动。
神韵派的王士禛和性灵派的袁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推崇钟嵘《诗品》。《诗品》主张“直寄”,要直抒胸臆、明白直接地作诗,就“即目”“所见”作诗,不主张用典。陈衍对《诗品》非常反对,专门作有《诗品平议》来批评《诗品》。他认为钟嵘的诗歌宗旨,只是“批风抹月”之作,“力诋博物,导人以束书不观”(《石遗室诗话续编》476)。他更认为从《诗品》到《沧浪诗话》再到王士禛是一条脉络,他对这条脉络整个都是反对的。他说钟嵘《诗品》“启沧浪‘有别才,非关学’之说”(《石遗室诗话》89),并且后者是前者“流极”的产物(《陈衍诗论合集》940)。他还说:
渔洋于沧浪[……]取“羚羊挂角”之说,盖未尝学杜故也。表圣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已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羚羊挂角”是底言乎?至如禅家所云“两头明,中间暗”及诗家之“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竟是小儿得饼,且将作谜语索隐书而后已乎?(《石遗室诗话》140)
从性情说的角度,《诗品》《沧浪诗话》、性灵派,都是符合诗言性情的原理的。但陈衍这里更多的是反对神韵说而不是性灵说。神韵说的原理,从陈衍的角度看,是推崇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别才”,认为诗的境界不可说、不可道。陈衍非常反对这个神秘的诗歌境界。所以他这里反对“羚羊挂角”之说。又如《石遗室诗话》卷十:“渔洋更有‘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喻,直是梦魇,不止大言不惭也。”(140)晚明竟陵派的《诗归》,点评古诗常用“说不出”“说不得”等语。《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中反对道:“有何说不出?”“何以说不得?”(312—13)。
张之洞作诗能兼取唐宋之长,并非宋诗派的反面,他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但是张之洞的诗学观点非常保守。他斥责江西派的末流是“江西魔派”,主张“清切”之诗。陈衍和郑孝胥,都对张之洞这一点进行了反对。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叙》:
大抵伯严之作[……]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恶能使之尽合;兴之发也匪定,则儵忽无见、惝怳无闻者,恶能责以有说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并世而有作,吾安得谓之非真诗也哉。(郑孝胥1)
这实为近代诗学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蕴涵的近代诗学道理极丰,发古人之未发,与陈衍则相通声气。张之洞主张“清切”,同光派诗人的创作,显然与之相违。郑孝胥便说“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其理由是“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世界太复杂,人的内心活动也太复杂,乃至于“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清切”的诗难以表达这么复杂的内容。这里对诗歌内容的复杂化导致风格不得不艰涩的认识,与后来西方现代主义巨擘艾略特的说法可以说完全相同(见下文)。郑孝胥又说,他主张的诗不但有违清切,而且也“宫商不调”,违背传统诗歌中的音乐性要求。他又明确说陈三立等同光诗人的诗“不期于切”,根本不以传统的清切流转和谐之美为追求。这种自觉的意识,在最初创造这种新型诗歌的韩愈、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论那里,是没有的。
陈衍有过一段类似的话。《石遗室诗话》卷十一:
广雅相国见诗体稍近僻涩者,则归诸西江派,实不十分当意者也。苏堪序伯严诗,言“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过芜湖吊袁沤簃》则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故余近叙友人诗,言大人先生之性情喜广易而恶艰深,于山谷且然,况于东野、后山之伦乎?(156)
这段话的发表时间晚于郑孝胥,又引用了郑孝胥的话,应当是受了郑孝胥说法的影响。或者说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相通声气。这里把张之洞的观点归结于张的“性情”,不及郑孝胥说得透彻。但是陈衍也有更进一步的地方,就是说出了“清切”与“僻涩”、“广易”与“艰深”这两组对立的概念。这里他明确将自己所属的同光派以“僻涩”“艰深”的风格自居,这也是前人所无的事情。他《沈乙盦诗叙》中记载他曾对沈曾植说:“君爱艰深,薄平易”(《陈衍诗论合集》1048),也用了“艰深”“平易”这组概念,对“艰深”宛然是赞赏的语气。
同光体诗人对“风诗”“雅诗”的论述,实为对宋代以来诗歌的这些新变因素,赋予“正”的意义,为新变之诗谋取合法性。因为诗经中的《大雅》等部分,至少在后人看来,语言是艰涩典重、缺乏音乐性的,并有许多铺排和议论的成分,与宋诗派有某种契合。陈衍对诗歌风雅之别的经典论述见于《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
余以为诗歌本分两道,前《诗话》曾言之。旗亭所唱者,《风》类也;诘屈聱牙者,《雅》《颂》类也。在《雅》中“杨柳依依,雨雪霏霏”一类,“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为一类。(491—92)
风诗的特点是“旗亭所唱”,富于流美婉转的音乐性。这里偏要说歌唱性是卖酒的“旗亭”所唱,可能暗含了贬低的意味。雅诗本是古人心目中的庙堂典正之作,这里说它“诘屈聱牙”,想要把“僻涩”“艰深”的同光派诗风标举为诗歌正体的用心,十分明显。所谓“诘屈聱牙”,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审美中,是很难算得上“正体”的。这里搬出雅诗来自我作古,亦类似于诗歌光怪陆离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对自己进行的“古典主义”的“认证”。把“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和“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作对比,是用了《世说新语》的典故。《世说新语·文学》:“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刘义庆278)“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但内容和风格都接近于风诗。“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则是标准的雅诗,不但典重艰深,还带有议论性质。陈衍在《诗学概要》中则说“《雅》《颂》,赋多而比兴少。《风》,比兴多而赋少”,后世“赋”越来越多是因为“比兴有限,而赋无穷”。(《陈衍诗论合集》1029)集中从文学角度论述风和雅颂之别,始于明代唐诗学中的王世贞、许学夷等人。唐前诗多用比兴而宋诗多用赋,不是新鲜的说法。陈衍认为赋越来越多的历史变化是诗歌的进步,则与大部分唐诗派诗人的立场相反。陈衍《瘿唵诗序》反对严羽“不关学也”的说法时,批评汉魏六朝诗“有风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陈衍诗论合集》1057),就是认为汉魏六朝诗不如后来的诗。尽管“赋”越来越多,陈衍也并不认为宋后诗人就都能作雅颂之诗。陈衍《聆风簃诗叙》:“今之诗人,徒取给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名家,虽号称钜子,立派别,收召才俊,免于‘风而不雅’之谯者盖寡。”(《陈衍诗论合集》1033)显然他认为当时的诗人也大都能风不能雅,恢复雅颂正要靠他们这些同光体诗人。
总的来看,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诗论家,对前人诗学中标举的富有抒情性、富有音乐性、风格上圆美流转的诗歌“正体”,进行了自觉的反拨。他们直接标举“乖于清”“艰深”的风格,这在历史上是个新的现象。他们又对自己的这种风格,进行了具有古典主义色彩的解释和理论建设。
二、 “学人之诗”的究竟内涵
同光体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从道咸宋诗派到同光体的诗人们有很多都说过学人之诗,这在学界,是被关注比较多的问题。从“同光体特性”的角度出发,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可供发掘之处。
陈衍在《近代诗钞》祁寯藻下的述评,说道咸间的宋诗派诸家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陈衍诗论合集》879)。陈衍对学人诗的论述,大都以这个“二而一之”为主旨。如《聆风簃诗叙》说:“余平生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陈衍诗论合集》1076)可是对二者的具体关系,“一之”境界具体如何,陈衍缺乏系统的论述。如《李审言诗序》认为“故别才不关学者,言始其事;多读书云云,言终其事。”(《陈衍诗论合集》1073)学人诗才是最终阶段。但是《石遗室诗话》卷十四又说:“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200)似乎认为学人诗要汇入诗人诗的极境。
在学人之诗这个问题上,陈衍诗论尚不足以为我们解开同光体诗歌的秘密。沈曾植的相关诗论,相比之下要深刻得多。钱仲联先生说沈曾植是同光体诗人中“道道地地的学人”(《沈曾植诗学蠡测》102)。这不只体现在他的诗作,他的诗论也是同光体中最地道的学人诗论,尽管他没用“学人之诗”这个名目。首先是沈曾植也喜欢用《世说新语》中“远猷辰告”“杨柳依依”的话头来论诗,他的说法,包含了不少“学人诗”的道理。沈曾植《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
谢傅“远猷辰告”,固是廊庙徽言;车骑“杨柳依依”,何尝非师贞深语。(郭绍虞292)
这里表面上是把雅诗和风诗两种风格并重,实际上是认为后者也是“师贞(用兵正道)深语”,也含有很深的义理。这是用雅诗的观念来统一风雅二者。他心目中的雅诗是含有义理的“深”语,这个深不只是思想的深度,还包含诗笔本身的深度。结合沈曾植的诗歌创作,更能知此意。
沈曾植《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一文也认为雅诗高于风诗。六朝的诗歌只是比风更低一层的“歌谣”,更不足道。在唐诗派的诗学中,唐诗为正体,六朝诗又常被认为是唐诗之前的“正始”,诗歌的怪变是中唐和北宋才发生的事情。这里沈曾植把前人这种诗学翻了个,所用的,就是“雅诗”的理论。这与陈衍的立场相同。与陈衍不同的是,他这里又多出了一层学人诗的意思。他说“涵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刑之事变”(“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下)”177)云云,是他认为上乘诗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当是沈曾植诗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诗歌理论的集中体现:
吾尝谓诗有元佑、元和、元嘉三关[……]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轩轾,此二语便堕齐、梁词人身份。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遍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尤须时时玩味《论语》皇疏(与紫阳注止是时代之异耳),乃能运用康乐,乃能运用颜光禄。[……]其实两晋玄言,两宋理学,看得牛皮穿时,亦只是时节因缘之异,名文身句之异,世间法异。以出世法观之,良无一无异也。就色而言,亦不能无决择,奈何?不用唐后书,何尝非一法门(观刘后村集可反证)。无如目前境事,无唐以前人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伪体。其实非伪,只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郭绍虞291—92)
这篇文章里的“三关说”(元嘉、元和、元佑),和以“意”“笔”“色”论诗的理论,前辈学者已有所阐发。这段话又是沈曾植学人诗理论的集中体现。他的三关说与陈衍“三元说”的最大差异,正在“元嘉”一关。但是他重视的元嘉诗,是不包含鲍照的。他重视谢灵运和颜延之,是因为他们有着东晋及更早的学术作支撑。谢灵运诗的先导是东晋的支遁(支道林),并且和东晋的兰亭诗相通。支遁诗和兰亭诗,都有浓重的东晋玄学背景。沈曾植所重视的玄学,又不在于其老庄源头。他认为东晋玄学、南朝皇侃的《论语》疏、南宋的朱熹,这些学问都只是时代之别,本质并无差异。皇侃的《论语》疏更是可以给人理解运用谢灵运和颜延之两家的作用。这些学问就是“意”“笔”“色”中的“意”,有了“意”才能抉择和运用“色”(诗歌的外境),二者才能综合到“笔”的境界。否则就是伪体。这个“笔”又显示出,沈曾植也认为学问本身不是诗,还是要归入诗的本位。这是沈曾植这里的学人诗理论与乾嘉考据诗的差别。读沈曾植诗集也能知道,他的诗并不寡淡,内在诗性是很强烈的。
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建构中,汉魏诗是个高峰,后来的东晋玄言诗一般被视为诗歌的衰落。到了刘宋,因为乐府复兴、诗歌抒情性复振、山水诗兴起,诗歌才迎来“元嘉三大家”这个高峰。而沈曾植的认识,完全与今天相反。他说刘勰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主张山水诗不如庄老诗,而这是齐梁人的陋见。他认为元嘉诗的好处,正在于有东晋学术和诗歌的基础。他非常推崇东晋支遁(支道林),《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里说:
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支、谢皆禅玄互证[……]谢固犹留意遣物,支公恢恢,与道大适矣。(《海日楼札丛(外一种)》44)
谢灵运还偏向于外在事物一边,而支遁的诗“与道大适”,比谢灵运更高一层。
沈曾植对东晋玄言的这种推崇,是我们理解同光体诗歌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艾略特在把自己的现代主义诗歌认定为“古典主义”的时候,搬出的正是久已淹没的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他用此来反对十八、十九世纪被他认为只是片面抒情的浪漫主义。另外沈曾植这里“意”“色”“笔”三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艾略特的诗论中思想观念、客观事物(即艾略特所谓“客观对应物”)、诗歌感觉三者的关系。这种相似性不应被视为巧合,应被视为同光体诗人与艾略特一代的现代主义诗人,在诗学品质和在诗学史上所处的阶段等方面的相通。
要进一步理解同光体诗人上述两方面的论述,还需要到道咸宋诗派乃至乾隆时代的尊宋诗人那里去,追溯他们的理论渊源。乾隆时代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卷四中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122—23)“实处”“研理日精”等说法,还未脱前人窠臼。“刻抉入里”则抛开了“学问”等诗歌的外部因素,直接就诗歌风格作论。“刻抉入里”的诗,正是从中唐开始的。晚唐陆龟蒙有一段合论孟郊、李贺、李商隐的话,《书李贺小传后》:
吾闻淫畋渔者,谓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状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隐伏,天能不致罚耶?(陆龟蒙260)
“抉擿刻削,露其情状”,便是“刻抉入里”。中晚唐人的“抉擿刻削”,靠的是文学手法。宋诗的“刻抉入里”则像翁方纲所说,是“研理日精”,有意识地把学问和哲理引入诗歌。
陈衍把从道咸到同光的宋派诗分为“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派(《石遗室诗话》21)。翁方纲的“刻抉入里”与同光诗人的“生涩奥衍”,实际只有一间之隔了。到了道咸时代,郑珍有一首《留别程春海先生》,评论他的恩师程恩泽的古体诗是“蟠虬咆熊生蛟螭”,显然不是神韵派推崇的王孟妙境。诗中说诗人对学问要“捣烂经子作醢臡”,包含了学问本身不能成诗,要经过转化的道理。诗中又以“峭者”“拗者”“旷者”“宏肆而奥者”等词语说诗,是陈衍“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个说法的前驱。(郑珍46)这体现出同光体诗学中的“学人之诗”和“生涩奥衍”两个方面,早在郑珍那里就有所结合。晚清人的学人之诗绝非乾隆时代四平八稳的考据诗,而是有明确的风格指向的。
与郑珍同时代的莫友芝,在给郑珍诗集作的序里说道:
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裁别趣、非关书理之论[……]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宗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莫友芝577)
这里对严羽的反对,下启陈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中间包含着“学人之诗”的道理。此序中说郑珍:“静涵以天地时物变化之妙,切证诸事态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涣然于中,乃有确乎不可拔者[……]溢而为诗。”(莫友芝578)学人诗不只在于博闻强识,更能够贯穿“天地时物变化之妙”“事态古今升降之故”,最终要“涣然于中”“溢而为诗”,仍要归结到诗歌这个本体。这可谓是“学人诗”的上乘宗旨,已经接近沈曾植的理论。
清代的宗宋诗人从乾嘉到道咸再到同光的这个学人诗的理论脉络,以沈曾植为最终完成者。而上引郑孝胥的“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不是为学人诗而发,却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不可忽视的另一个侧面。近代的时代环境,实不允许一种像六朝诗、北宋词那样风华靡曼的诗派的出现。王闿运号称学习六朝三唐,但如同沈曾植所说,被时人批评为只会模拟的伪体。甚至王闿运自己也说“余诗尤不可观”(王闿运552)。受王闿运影响的邓辅纶、高心夔等湖湘派诗人,创作都有突出王闿运宗旨之外的地方,与同光体不无声气相通。近代社会环境和诗人内心世界的迅速复杂化,在那代诗人那里,接近是个“无解”的问题。他们又有极深厚的传统学术修养。除了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心思情志和思想内容纳入诗性的“学人之诗”,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如果沈曾植是晚清学人诗内在理路的完成者,郑孝胥的话则揭示了这种诗歌盛行的外部因素、以及与外部因素相对应的诗人心性因素。
三、 诗人论诗所用形容词中体现出的诗歌特性
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特点,是不仅依赖于理论化的概括,还依赖于直感式、审美式的评论。这类评论,突出表现为使用形容词来描述诗歌风格。近代诗论也延续了这个传统。陈衍的这类诗论,最有名的是他把近代宋派诗分为“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派的论述,见于《石遗室诗话》卷三。因为是常见的文本,这里不具引。陈衍擅长“二元”的思维方式,喜欢把事物一分为二并求其综合。然而就陈衍整个中年诗论对同光体的概括而言,“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个词关系并不对等。(本文所说陈衍“中年诗论”以《石遗室诗话》为代表,大体完成于民国四年之前。“晚年诗论”则以《陈石遗先生谈艺录》《石语》为代表。晚年诗论透露出闽派诗人不尚艰涩的一面,本文不作涉及。)他把“清苍幽峭”一派上推到王、孟、韦、柳,这更像一种调和之论。他在上文所引的论述中把同光体诗人都看作与王、孟、韦、柳等唐诗“正体”相反的派别,就是证明。“清苍幽峭”这个词,其美学指向介于盛唐的圆美流转与晚清的“生涩奥衍”之间,正是个中庸调和的描述。结合他《石遗室诗话》中反对张之洞的论述来看,“生涩奥衍”才是同光体诗歌真正具有革新力量的诗学品质。具体去看郑孝胥等闽派诗人的诗歌作品,也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生涩奥衍”的诗,与晚清江西派并不能清晰划分。汪辟疆《近代诗坛与地域》就曾指出:“海藏(郑孝胥)集中亦有近于奥衍一派者,实与东野、宛陵为近。”(26)
陈衍在反对张之洞时用到的“僻涩”“艰深”二词,和他标举雅诗时说《雅》《颂》的“诘屈聱牙”,都是与“生涩奥衍”类似的词语。陈衍诗论中还有多处用到这类形容词,如:“《萚石斋诗》造语盘崛
。”(《石遗室诗话》60)“爽秋诗僻涩苛碎
,不肯作犹人语,然亦多妍秀可喜者。”(157)“爽秋诗根柢鲍、谢,而用意遣词,力求僻涩
,则纯于祧唐祖宋者。(《陈衍诗论合集》899)”“陈之诗甚僻涩
,有似其性情。(引者注: 此略带贬义。)”(《陈衍诗论合集》1087)“散原精舍诗专事生涩
。”(《石遗室诗话续编》704)“海藏支离突兀
之故态。(引者注:“支离突兀”这里是形容郑孝胥的人,但也未必不能看作诗。)”(《陈衍诗论合集》1082)“缶庐造句,力求奇倔
。”(905)“雁南诗兼学坡、谷、荆公,不苦涩
亦不滑易。”(《石遗室诗话》338)“乙庵诗虽多诘屈聱牙
,而俊爽迈往处,正复不少。”(488)加着重号的这些词,全都偏向所谓“生涩奥衍”一派。这里面有同光体浙派的沈曾植、袁昶,也有同光体闽派的郑孝胥。他说乾隆诗人钱载的《萚石斋诗》“造语盘崛”,是值得注意的。陈衍在《近代诗钞》中,认为钱载是整个乾嘉时代唯一可作为宋诗派和同光体先声的诗人。除陈衍外,同光体诗人中最擅长用这类复杂的“组合形容词”论诗的当属陈三立。与陈衍不同,陈三立诗论不很重视艺术形式,而是重视诗人的主观情志,和触发诗心的外在环境。陈三立《蒿庵类稿序》:“跼天蹐地之孤抱无可与语,辄间托诗歌以抒其伊郁烦毒
之思。”(陈三立896)《陈芰潭翁遗诗序》:“盖所接苍茫无端
与块独不自聊之感,荡魂撼魄,更有在于人国兴亡成败盛衰之外矣。”(陈三立912)《俞觚庵诗集序》:“举伊郁烦毒愤痛
毕宣于诗。”(陈三立943)这都是对诗人主观情志的描述。这些形容词,全都不可能指向王维孟浩然那样的唐诗体,最能指向同光体诗。陈三立对诗人遇到的外境的描述,也与此相同。《书善化瞿文慎公手书诗卷后》:“而况际天荒地变、患气充塞、人人莫知死所之今日哉?”(陈三立949)这些说法,再次印证了上文所说近代诗人面对的复杂到“无解”的内在和外在状态,亦即上文多次引用的郑孝胥所说“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一语。这一近代性因素,又正好与道咸以来宋派诗的内在发展理路相合。陈三立有时也用形容词直接论诗歌艺术,如“惨辉妙旨,成嵯峨俶诡
之观”(1137)、“磊砢恢疏
”(1141)、“镵刻瘦硬
”(1148)、“沉博奥邃,陆离斑驳
”(1152)。这些词大都与“生涩奥衍”有关联。其中“沉博奥邃,陆离斑驳”是评沈曾植诗的,可谓恰如其分。陈三立本身是在文章中使用形容词的高手,他这些论诗或者论诗人的形容词非常地丰富多彩。后来的诗论家中,能继承同光诗人这类形容词的,当推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评姚燮:“雕肝镂肾
,戛戛生新
。”(388)评沈曾植:“沈乙庵诗深古排奡
,不作一犹人语。”(205)“乙庵律句,奇辟古奥
。”(206)评范罕:“惨辉妙旨,成嵯峨俶诡
之观。”(260)评范罕诗的这句,是录用陈三立评《无邪诗存》的语句。钱仲联还用到过“奇诡纵肆”“镵削奇倔”“镵刻奇伟”等等形容词。值得注意的是钱仲联偏向的是同光体中的浙派(沈曾植一派),他对“生涩奥衍”是直接主张的,不再有陈衍那种总是要二而一之的调和之论。陈衍评价陈三立“伯严诗避俗避熟,力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评价沈曾植“雅尚险奥,聱牙钩棘处时复清言见骨”。钱仲联在《论同光体》里则不大认可陈衍的这种评价,认为陈衍作为闽派诗人有不尚拗涩的一面,所以才去强调陈三立沈曾植的“文从字顺”“清言见骨”。(《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121)用这样复杂的组合形容词来论诗,就笔者的考察,是始于六朝时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谢朓说的“圆美流转”(《南史》卷二十二609—610)。这样的诗学标准,基本上在唐代一直延续,并且也符合一般民族早期诗歌的特征。同光体诗人用同样的“组合形容词”方式论诗,却完全走向了“圆美流转”这种传统审美的反面。上文说到同光体诗歌艺术是“传统诗歌内部的一种真正的革新力量”,就其直观的审美表现而言,就体现在他们这些形容词中。这些形容词,与他们在“雅诗”和“学人之诗”里把同光体说成诗歌正体的说法,似乎并不一致。他们一用起这些形容词,似乎就放弃了诗歌“正体”的建设。其实这个矛盾,在中国诗学中由来已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
少陵材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为国爱君[……]诗之变,情之正者也。(2)
杜甫“恢张”“纵横”的诗风,有违前代诗歌的古典美,因此是“诗之变”。但他又是最忠君爱国的诗人,所以是“情之正”。中唐的儒学复兴,以韩愈为巨擘,韩愈的诗又是比杜甫变体更甚的怪变之体。宋代江西派的黄庭坚,接着杜韩变体而来,但他的诗论又是儒家传统色彩浓重的论调。这或许可以说是宋型诗学近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内部矛盾。同光体诗人的上述理论建设,未必已完全解决问题,却是传统诗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结果。陈衍已经明说《雅》《颂》就是“诘屈聱牙”的。儒家与佛教、道教相比,其实非常能接纳“不和谐”的状态,和激烈浓重的人生。这或许是这个诗学现象深层的思想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很少会用这一类的形容词。对他来说,这个矛盾已经被他的学人诗理论所解决,他不必再用这些传统上带有负面性质的字眼去描述自己的诗歌。近代诗学内部的许多问题,若说陈衍是问题的提出者,则沈曾植在相当程度上是已完成了自我统一的解答者。
四、 同光体与艾略特的现代主义
同光体诗人的这些诗论,与西方现代主义巨擘艾略特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上文已数次论及。最早把艾略特诗论与中国古代诗论进行类比的,可能是叶公超。他在民国时代写的《再论艾略特的诗》中认为艾略特诗论和中国古人有用典、化用旧句、“文以载道”等方面的相通。
经过上文的梳理,同光体诗论与艾略特的相通,显然要比唐宋人深刻得多。这不只是一种横向比较,还在于同光体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处在诗歌纵向发展的相同节点上。这才是在考察“同光体特性”时为什么必须要关注到这种相通的原因所在。故此,这里只拿艾略特影响最大的早期诗论与同光体对比,他晚年宗教化的理论,与中国的可比性就不大。同光体中陈衍晚年诗论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变化的方向还和艾略特晚年有所相近(比如对诗歌语言通俗性的强调),但这里也只考察陈衍相对早期的诗论。艾略特的第一篇重要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于1919年,仅稍稍晚于上述同光体理论的形成。现在结合上文,具体列出同光体诗论与艾略特的几项相通之处。
一、 思想观念、外部事物、诗歌感觉三者的关系。艾略特认为诗人应该“知道得愈多愈好”。他说:“诗人可能有的兴趣是无限的;智性越强就越好;智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 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化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4)这种诗人学问越大越好的说法,正相当于同光体中对学问和思想的重视。同样与同光体相同的是,学问本身并不是诗,还要“把它们转化为诗”。这个转化,在艾略特诗学中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学问和思想作为观念,要转化为诗歌“感觉”。《玄学派诗人》里就有“将意念转化为感觉”,“将它们的博学融入他们的感受力”的说法(艾略特33、30)。二是“感觉”又要有其“客观对应物”,即外在事物。诗人越有学问和思想,其诗歌感觉便越能融通外在事物。艾略特说:“思想对于邓恩来说是一种经验,它调整了他的感受力,当诗人的心智为创造做好完全的准备后,它不断地聚合各种不同的经验。”(31)这与沈曾植的“目前境事,无唐以前人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是同样的意思。“聚合各种不同的经验”,与沈曾植说的“就色而言,亦不能无决择”极为相似。沈曾植说“打发不开”的结果是“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伪体”,这正相当于艾略特批评的浪漫主义诗歌中思想与感觉的分裂。艾略特的诗歌“感觉”这个概念,在他的某些论述中,可视为诗人主观思想和客观事物的统一。他说:“只要感觉仅仅被感受,它就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韦勒克269)这是一种一眼即辨的辩证法性质的综合。不难看出,沈曾植的“意”“笔”“色”中,意就是诗人的思想,色就是外在事物,笔就是二者的辨证综合。沈曾植不用西哲术语,但是他用印度“空”“假”“中”的“中”这个概念,是十分接近西方术语的。“中”就“笔”所实现的“意”和“色”的综合。
二、 时代的复杂化导致诗歌风格的艰涩。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说:“诗人并不是永远都要对哲学或其它学科感兴趣。他们只能说,就我们文明目前的状况而言,诗人很可能不得不变得艰涩。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细的感受力,必然会产生多样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32)“不得不变得艰涩”,与郑孝胥等人在反对“清切”说时为自己的艰涩诗风所作的辩护,如出一辙。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或许是不如艾略特所处的社会复杂,但是对那一代从传统社会中走来的同光体诗人来说,已经“足够”复杂了。至于“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在张之洞那里,恐怕就是让人难以通晓的“江西魔派”了。陈三立、沈曾植和稍晚的陈曾寿的诗,都绝不像盛唐诗那样文从字顺。他们虽然没有打破语法,也仍然用了艰涩的语言。
三、 对个人化抒情和个人灵感的贬低。艾略特反对个人抒情,这是他众所周知的诗学命题。他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然而,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8)艾略特反对的这种个人抒情,正好是清代性灵派所主张的、同光体所反对的。甚至艾略特对不可捉摸的诗歌灵感,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主张诗人“智性越强就越好”。他指责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反对推理,反对描述;他们间歇性地思考和感受,极不平衡”(32)。而陈衍一再指责严羽和王士禛那种“不可说”“说不出”的“羚羊挂角”“华严楼阁”是痴人说梦的话,也体现出了对理性的一种推重。又如清代宋大樽《诗论》说“有前此后此不能工,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必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说的就是一瞬间的作诗灵感;陈衍反对宋大樽,说他这里是“误于王文简(引者注: 王士禛)模糊惝怳欺人之谈。”(《石遗室诗话》49)。
四、 反对浪漫主义和提倡玄学诗。正是因为主张智性和感受的统一、反对个人化抒情,艾略特在其整个诗学中,都把自己看作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反面。这与同光体诗人把自己看作性灵派、神韵派乃至六朝盛唐派的反面,其道理是相通的。艾略特认为十八世纪以来,诗歌“统一的感受”发生了分裂,诗人们要么只思想,要么只感觉。这正好比同光诗人说的六朝之后风和雅颂的分裂、比兴和赋的分裂。陈衍在《瘿唵诗序》中反对《沧浪诗话》时说:“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陈衍诗论合集》1057)这是初始的未分裂状态。艾略特和同光诗人都以能够弥合这种分裂的重建者自居。
艾略特在反对浪漫主义的同时,推崇早于浪漫主义的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这与沈曾植对早于齐梁缘情诗风的东晋玄言诗的推崇,有一种奇妙的相似。艾略特称赞两个玄学派诗人“学识都极为渊博,而且显然将它们的博学融入他们的感受力”(30)。这里对博学的强调,和认为博学可以转化为诗歌感觉,都与沈曾植推崇东晋玄言诗的理论相同。艾略特认为他自己和玄学派诗人在对“晦涩的词语”的使用上也相似(艾略特30),这让我们想起陈衍和郑孝胥关于“僻涩”“艰深”的那些说法。艾略特认为玄学诗的修辞是“推敲锤炼”“巧用心迹”(26)。很明显,同光体诗人反对前人自然清切、“无迹可求”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也有浓重的人工雕琢色彩。
艾略特说,前人对玄学派的批评,说他们“要么是‘玄学的’或‘机智’的,要么是‘古怪的’或‘晦涩的’”(34)。这不是正等同于中国古人对宋诗的议论化和“拗捩、艰涩”这两个方面的批评吗?艾略特把这些前人批评的东西拿过来自居,又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也与同光体诗人相同。
出于以上这种种理由,尽管东西方诗歌史有巨大的差异,我们还是可以说“同光体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处在诗歌纵向发展的相同节点上”。这也是同光体诗人为什么会建立出这样的一套诗学,和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为什么显示出了传统诗歌的一种革新力量。
结 语
同光体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传统诗学内部的一种强烈的自我革新。出于论题限制,这里无法对同光体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论述,颇感遗憾。日本的吉川幸次郎说陈三立诗“尽管处于传统的诗歌形式中,但稍微夸张些,可以说它和以往的诗有着不同性质”。他举了陈三立五绝“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为例。他在评论陈三立另一首五绝时又说“这已经完全是近代的感觉了”。(吉川幸次郎356—57)这种看法体现出吉川氏的慧眼。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三位同光体的魁杰有过一次五古唱和,每人三首,共九首。这组诗颇能体现同光体的特点。沈曾植的三首题为《简苏堪》,王国维评论这三首诗:“于第一章,见忧时之深。第二章,虽作鬼语,乃类散仙。至第三章,乃云‘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又非孔孟释迦一辈人不能道。以山谷、后山目之,犹皮相也。”(王国维424)他认为沈曾植诗极具精神高度,已非山谷后山的江西诗派所能概括。王国维对宋诗和同光体本是很苛刻的,他能作这样的赞赏,难能可贵。王国维的苛刻是出于他的诗学观念,其赞赏则是出于溢出诗学观念之外的诗歌感受力。甚至他在自沉前一天,写在扇子上的也是闽派诗人陈宝琛的落花诗,中有“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之句(刘永翔 徐全胜1)。只要怀着同样真诚的心去阅读同光体的诗作和诗论,就能发现其中激动人心的诗学革新力量,和其至今未息的对将来诗学的生发作用。
注释[Notes]
① 汪辟疆与钱仲联时代晚于同光体诗人,但在民国时代都深受同光体诗学影响,所以本文对它们民国时代的诗论稍作涉及。但本文仍以同光体诗人为主要考察对象。
② 此诗的第三句以黄庭坚(双井)来称赞袁昶(袁沤簃),可见第一句说的“江西魔派”是江西派末流的意思,不指黄庭坚。《石遗室诗话》对此另有解释,认为张之洞这里只是表面上不贬低黄庭坚,实际上对黄庭坚也是不满的。
③ 郑孝胥文见于宣统二年的《散原精舍诗文集》弁首。陈衍于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年在《庸言》杂志发表《石遗室诗话》前十三卷。
④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宋芷湾(湘)有绝句二首云:‘岂果开元天宝间,文章司命付梨园?诸公自有旗亭见,不爱田家老瓦盆。’[……]可谓独见语,先我而实获我心者矣。”(《石遗室诗话》21)显然他说的“旗亭所唱”一语又是受宋湘此诗影响。
⑤ 学界已注意到晚清学人诗观念并非单纯的以学问入诗,如吴淑钿的《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认为“学人诗与诗人诗合”要求诗歌是理性德性才性的总体体现。见吴淑细: 《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台北: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本文在学人诗问题上注重沈曾植的诗论,认为沈曾植虽不明用“学人诗”术语,却是晚清学人诗理论的完成阶段。
⑥ 韦勒克认为在艾略特那里,“‘感觉’是无处不在的,具体的,精确的,几乎等同于知觉或察觉”。见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Chen, Sanli.Collected
Poems
and
Essays
from
the
Sanyuan
Vihara
.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3.]陈衍: 《石遗室诗话续编》,《民国诗话丛编》(一)。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Chen, Yan.A
Sequel
to
Poetry Remarks from the Shiyi Studio.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Vol.1.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陈衍诗论合集》,钱仲联编。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 - -.Collected
Poetry
Remarks
of
Chen
Yan
. Ed. Qian Zhonglian.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一)。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 - -.Poetry
Remarks
from
the
Shiyi
Studio
.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Vol.1.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丁福保编: 《历代诗话续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
[Ding, Fubao, ed.A
Sequel
to
Poetry Commentaries during Successive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Eliot, Themas Steam.Essays
of
T
.S
.Eliot
on
Poetry
. Trans. Wang Enzhong.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89.]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Guo, Shaoyu.Selected
Essays
of
Literary
Theory
during
Successive
Dynasties
. Vol.4.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李梦阳: 《空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3年。
[Li, Mengyang.Collected
Works
of
Kongtong
.Photo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Wenyuange
Copy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126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李延寿等: 《南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
[Li, Yanshou, et al.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刘克庄: 《后村诗话》。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
[Liu, Kezhuang.Poetic
Remarks
from
Houcun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刘义庆: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
[Liu, Yiqing.Annotated
The Tales of the World. Ed. Yu Jiax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刘永翔 徐全胜:“沧趣楼诗文集·前言”。陈宝琛: 《沧趣楼诗文集》,刘永翔、徐全胜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2。
[Liu, Yongxiang, and Xu Quansheng. Preface.Collected
Poems
and
Essays
from
the
Cangqu
Building
. By Chen Baochen. Eds. Liu Yongxiang and Xu Qu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3.1-22.]陆龟蒙: 《甫里先生文集》。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Lu, Guimeng.Collected
Writings
of
Mr
.Fuli
.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996.]莫友芝: 《莫友芝诗文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Mo, Youzhi.Collected
Poems
and
Essays
of
Mo
Youzhi
.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钱仲联:“沈曾植诗学蠡测”,《文学遗产》(1)1996: 101—05。
[Qian, Zhongli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etics of Shen Zengzhi.”Literature
Heritage
1(1996): 101-05.]——: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济南: 齐鲁书社,1983年。
[- - -.Critical
Essay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Mengtiao
Hut
. Jinan: Qilu Press, 1983.]——: 《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下)》,《文献》1(1991): 175—85。
[- - -.Lost
Prefaces
from
the
Hairi
House
of
Shen
Zengzhi
(3
).The
Documentation
1
(1991): 175-85.]——: 《梦苕庵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 - -.Poetry
Remarks
from
the
Mengtiao
Hut
.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Vol.6.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沈曾植: 《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 -.Reading
Notes
from
the
Hairi
House
.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Shen, Deqian.A
Special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79.]王国维:“东山杂记”。《王国维全集》。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Wang, Guowei. “Miscellanies in the Eastern Mountain.”Complete
Works
of
Wang
Guowei
.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王闿运:“论诗法答唐凤庭问”,《湘绮楼诗文集》。长沙: 岳麓书社,1996年。551—52。
[Wang, Kaiyun. “An Answer to Tang Fengting about the Style of Poetry.”Collected
Poems
and
Essays
from
the
Xiangqi
Building
.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6.551-52.]汪辟疆:“近代诗坛与地域”,《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Wang, Pijiang. “Modern Poetry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Wang
Pijiang
on
Modern
Poetry
.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勒内·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Wellek, René.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 Trans. Yang Ziwu. Vol.5.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翁方纲: 《石洲诗话》。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Weng, Fanggang.Poetry
Remarks
from
the
Stone
Islet
.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严羽: 《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Yan, Yu.Textual
Interpretations
of
Canglang’s Poetic Remarks. Ed. Guo Shaoy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3.]叶公超:“再论艾略特的诗”,《北平晨报》1937年4月5日。
[Ye, Gongchao. “Revisiting T.S. Eliot’s Poetry”.The
Peping
Morning
Post
5 April 1937.]吉川幸次郎: 《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
[Yoshikawa, Kojiro.A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 Trans. Zhang Peiheng, et al.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86.]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叙”。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576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
[Zheng, Xiaoxu. Preface.Collected
Poems
from
the
Sanyuan
Vihara
. By Chen Sanli.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1576.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1.]郑珍: 《巢经巢诗笺注》,白敦仁笺注。成都: 巴蜀书社,1996年。
[Zheng, Zhen.Annotated
Poems
from
the
Chaojing
Nest
. Ed. Bai Dunren.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