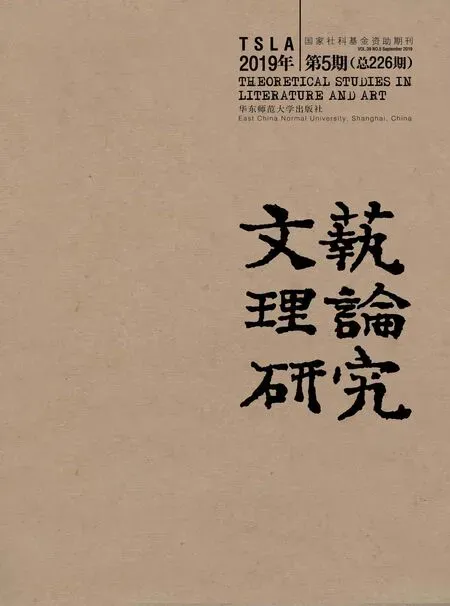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区别
高 玉
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关注晚清白话文运动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是: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基础,或者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继续。从表述上来说这没有错,但其观点似是而非。事实上,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仅只有时间上的先后性,而在理路、内涵、性质等上都不同,不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晚清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是两种不同的白话文,二者具有质的区别。晚清白话文在清末汉语体系中是边缘性的,辅助性的语言,附属于文言文;而五四白话文在现代汉语体系中是主体性的语言,也即“国语”,演变成现在的“现代汉语”,是国民标准语。
一、 启蒙运动与思想革命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启蒙运动,后者是思想革命。晚清白话文运动属于整个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一种方式。晚清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不一样,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向民众宣传传统的思想和知识;二是向民众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也包括科学思想。“启蒙”在这里主要是中文原初义,也即通过知识的方式开导蒙昧之人,所以其对象是普通民众。这和西方启蒙运动的启蒙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反封建专制和教会愚昧的思想文化创新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内部发生的思想更新、文化更新运动。而晚清启蒙运动不具有这种政治性,它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国传统知识和西方新知识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封建思想也是知识的一部分。理论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格物等实业“知识”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但在“知识”层面上,它们却和平相处并共存,这是晚清启蒙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之根本不同。
五四白话文运动则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白话文在这里并不只是语言形式,更重要的也是内容本身具有思想革命性。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被美国学者格里德称为“文艺复兴”(格里德77),但它不是指在汉字意义上复兴中国传统文艺,不是重现中国古代文艺或辉煌文化,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是思想革命,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反传统和思想解放。因为不是知识层面的启蒙,而是思想层面的革命,所以,西方的新科学等思想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与晚清启蒙运动不同,传统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再是传播的对象,而是需要批判、破坏和打倒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晚清启蒙运动的延续或者逻辑结果,也就是说,晚清启蒙运动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晚清启蒙运动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它和晚清启蒙运动遵循的是不同的理路。晚清启蒙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二者是连续的历史过程,但这种连续性是时间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外在语言形式上很相似,在功能外表上也非常相似,但内涵上却具有本质的不同。晚清启蒙运动为什么要用白话?根本原因是文言文作为语言太难懂,文言文繁难艰深,大量的偏僻汉字、偏僻词语,大量的用典,大量的不可理解的套语,不讲文法等,不仅一般士人阅读困难,掌握困难,普通百姓更是听不懂,读不懂。文言文造成了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包括中下层读书人对思想的深深隔膜,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书籍知识的层面上,不管是“经”“史”还是“子”“集”,不管是思想,还是物质和技艺,大多数都是平实的,普通人是能够理解的。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知识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和少部分知识分子的特权,而绝大多数国民则被剥夺了接受知识和思想的权力,这当然与经济条件、教育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语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文言文犹如一堵墙,把普通国民隔在知识和思想之外,这严重地降低了中国国民的素质。所以晚清思想文化界使用白话文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把文言文承载的思想、普通的知识用白话文传授给识字的普通百姓,讲给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听,当然也是让小知识分子可以看懂。白话文运动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古代知识和思想文化本身的问题。
用白话文传播封建思想文化其实早在清中叶就开始了,比如康熙皇帝曾发布16条“圣谕”,雍正皇帝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于雍正二年即1724年发布《圣谕广训》。“圣谕”和《圣谕广训》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虽然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日常道理,但普通百姓听不懂,也看不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中期以后出现了很多白话《圣谕广训》,比如《圣谕广训通俗》《圣谕广训疏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圣谕广训衍》和《圣谕广训直解》,比如“圣谕”第一条是:“敦孝弟以重人伦”,雍正《圣谕广训》对它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周振鹤 顾美华162)《圣谕广训衍》的解释是:“怎么是孝呢?这个孝顺的道理大得紧,上而天、下而地、中间的人,没有一个离了这个理的。怎么说呢?只因孝顺是一团的和气。你看天地若是不和,如何生养得许多人物出来呢?人若是不孝顺,就失了天地的和气了,如何还成个人呢?如今且把父母疼爱和您们的心肠说一说。”(163)《圣谕广训直解》是这样解释的:“怎么是孝呢?这孝顺爹娘,在天地间为当然的道理,在人身上为德性的根本。你们做儿子的,不知道孝顺你的爹娘,但把爹娘疼爱你们的心肠想一想,看该孝也不孝?”(165)这里所谓“衍”“直解”,其实就是白话翻译,只不过不是“直译”,而是“意译”罢了。清末提倡白话文,遵循的是同一理路,只不过因为使用广泛而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已。王照在《挽吴汝纶文》中说:“今吾中国公文中,亦恒曰养民教民,实则发之者官吏,收之者官吏,解之知之者,仍此官吏也。民固无从知也,纸上之政治,自说自解,自唱自和,视民之苟且妄作,辄于纸上骂以心死,责以无良,而民又不知其纸上云何也。”(王照31)清末白话文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当然解决的方法除此之外,文字改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晚清时期,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和技术知识已经大量传入中国,少量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传入中国,文言文汉字单字的表达方式完全无法适应这种知识的大爆炸。一是文言文无法准确地表达西方传入的新事物、新文化。文言文是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逐渐产生并发展演变的,它命名中国的事物,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的自然和物质包括社会的基本构成,中外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很容易就能够在文言文中找到对应的词语、对应的表达,但对于西方新的事物,新的科学和思想文化知识,文言文则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准确地表达。胡适说:“时代变的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108)傅兰雅引西人语说:“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然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若译泰西教门与泰西国政,则不甚难。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傅兰雅284)现在看来,这种翻译的困难主要是文言文的困难。近代文言翻译的困难,当时就有很多学者、翻译家表达过,比如严复说:“求其信,其大难矣。”(严复202)“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203)过去我们从翻译的技术角度理解此语,但实际上严复主要是讲文化的差异性、语言的差异性问题。之所以翻译难“信”,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的不对等,而不是翻译能力欠缺。
二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用文言翻译,即使勉强表达了,一般人也看不懂,不能产生社会效果。傅兰雅说:“已译成之书大半深奥,能通晓之者少,而不明之者多。”(傅兰雅287)之所以不能“通晓”,“不明”,倒不是西学有多难懂,很大程度上是文言文作为语言的障碍造成的。而在表达新事物、新知识上,白话具有很大的优势,文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词语。文言文主要是单字使用的语言,在文言文语言体系中,增加新事物和新概念主要是增加汉字,或者用句子表达,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和知识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还差可胜任,但晚清新事物剧增,知识特别是西方知识大爆炸,用增加汉字的办法来解决事物的命名、知识的概念等根本就没有可行性。且汉字在清《康熙字典》中就收录4万多,对于学习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掌握这么多汉字,普通人更没有可能了。而常用字组合词(即白话词),本身通俗易懂,而且大大减少汉语的识字量,且用白话词也解决了物质名词,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翻译问题。所以,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白话不仅表达和传播旧知识,也表达和传播新知识。
与此相关,晚清白话文运动所针对的是普通民众以及“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仍然阅读和使用文言文。胡适批评清末白话文运动:“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 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五十年”252)周作人说:“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51)他认为晚清白话本质上是平民语言:“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51—52)朱自清在《论通俗化》说:“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清朝末年。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的人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再一方面推行官话字母等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教。”“原来这种白话只是给那些识得些字的人预备的,士人们自己是不屑用的。他们还在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体’;俗语的白话只是一种慈善文体罢了。”(朱自清142—43)晚清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学者和比如裘廷梁和黄侃等人,他们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却是用文言文写的。这都说明,晚清白话文运动主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一个文化普及运动,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运动,它不触动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传播知识,而是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关心知识问题,不管是西方的知识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它更关注的是思想和文化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它不仅不传播和宣传,恰恰相反,它是批判和否定的。它主要是承续晚清就已经开始的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接受,而把它向前延伸、扩大,更重要的是把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应用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从而重建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文化。胡适说:“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自己仍然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这个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五十年”253)宣布文言文死亡,其实是宣布中国传统思想之核心和主体的死亡,文言文作为语言体系的死亡也即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死亡,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类型的死亡。把白话和文言文对立起来,并且废除文言文,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最大的不同。陈独秀概括为:“文言文-古文-古事;白话文-今文-今事。”(“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194)这可能过于机械了,但却是很深刻的区分。
二、 工具性与思想本体
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两者具有质的区别。从语言形式上来说,两种白话没有太明显的差别,语法基本相同,语音基本相同,词汇有很大的共同性,我们很难具体地说哪些是古代白话,哪些是现代白话。但从思想上来说,整体上它们具有根本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表达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中国人表达思想和观念,不再是用“道”“器”“理”“仁”“气”“韵”“孝”“忠”“君”“臣”“纲”“常”“格物”等,虽然这些字或词在现代白话中并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不再是核心概念,现代白话的核心概念是“科学”“民主”“社会”“国家”“自然”“法律”“自由”“理性”“感性”“现代”“思想”“观念”“真理”等,这些概念就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它们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以翻译的形态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的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翻译语言,其作用是把文言文的思想用口语进行表达;同时也是西方事物和自然、社会与科学知识的大众语的命名形态,也即用口语的方式翻译西方的事物和自然、社会与科学知识以及表达中国新生的事物。晚清言说中国思想的主体语言是文言文,白话文则是具有工具性的大众语,主要限于日常层面的交流。而五四白话文除了具有工具性以外,还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新的语言体系也即新的思想体系,这是其与晚清白话文的根本差别所在。
五四白话文在思想层面上具有现代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向西方学习而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深入到了西方的核心——思想文化,五四白话文实际上就是这种学习在语言上的表现,所以它是一种具有现代思想内涵的白话。关于二者之间的差别,新文学家们有清醒的认识,郭沫若说:“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文体,自然有异于历来的文言,而严格的说时,也不是历来所用的白话”,而是“欧化的白话”(郭沫若364)。过去我们把“欧化”解释为语法上的,这当然也是一方面,但却是极其次要的特征,五四白话文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欧化。胡适说:“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尝试集》自序”82)傅斯年说:“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傅斯年133)所谓“新思想”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洞的,而就体现在具体的表达即语言之中。鲁迅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鲁迅548)胡适也说:“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130)两人所谈最后都归结到了思想或者思维上面,鲁迅强调五四白话文在思想上的“精密”性,胡适则强调五四白话文在思想上的“复杂”性,可见五四白话文的思想本体性特点。
与此相关的是白话文的逻辑性问题,这是当时就讨论比较多的问题,一般认为五四白话文具有逻辑性、科学性,但这种科学性、逻辑性主要不是来自语法,而是来自词语,也即体现出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它们主要来自西方。陈独秀说:“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问题,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197)这才是五四白话文的本质。所以,把“汝”改为“你”,把“曰”改成“说”,这不是五四白话文的本质。五四白话文当然也承继了古代口语的白话,但这只是现代白话中的一部分,且主要限于日常层面。而五四白话文最重要的部分是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民主”“自由”“知识”“理性”“人权”“女性”等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白话,很多“词语”虽然古已有之,但内涵完全不一样。
正是因为五四白话文是思想性的白话文,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确认为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现代小说。事实上,白话文学早在中国的汉代就开始了,晚清也产生了很多白话小说,但为什么不能把晚清的白话小说也看作是“新文学”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不是在语言形式上,而在于语言性质,古代白话文学使用的是“旧白话”,也即作为口语的工具性的白话,而现代白话小说使用的是新白话,也即具有现代思想的白话。朱希祖说:“文学的新旧,不能在文字上讲,要在思想主义上讲。若从文字上讲,以为做了白话文,就是新文学,则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很多,在今日看来,难道就是新文学吗?”(朱希祖86)单从白话形式上我们不能把晚清白话小说和五四白话小说区分开来,但在思想层面上,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
瞿秋白对这两种白话文作了详细的区分,他把五四白话称为“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而把传统的旧白话称为“章回体的白话”:“这五四式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现在新式士大夫和平民小百姓之间仍旧‘没有共同的言语’。革命党里的‘学生先生’和欧化的绅商用的书面上的话是一种,而市侩小百姓用的书面上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两种活的区别,简直等于两个民族的言语之间的区别。[……]现在的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章回体的白话。”(“普罗大众文艺”465)瞿秋白把这种欧化的白话文称为“新式文言”(或“半文言”)是有道理的,虽然笔者不同意他对这两种白话文的态度,比如他把五四白话文也称为“骡子话”(“普罗大众文艺”467)、“杂种话”(“欧化文艺”493),可见其鲜明的倾向。但对于五四白话文的性质的分析,瞿秋白是正确的,他说:“五四式的白话,表现的形式是很复杂的: 有些只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有些是所谓‘直译式’的文章,这里所容纳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化,而是囫囵吞枣的。这两大类的所谓白话,都是不能够使群众采用的,因为读出来一样的不能够懂。原因在于: 制造新的字眼,创造新的文法,都不是以口头上的俗话做来源的主体,——再去运用汉文的,欧美日本文的字眼,使他们尽量的容纳而消化;而是以文言做来源的主体,——甚至于完全不消化的生硬的填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结果,这种白话变成了一种新式文言。”(“普罗大众文艺”466—67)和五四白话文不同,晚清白话文是真正的民间口语,是口语的书面化,是大众化的语言,或者大众使用的语言,这种白话文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五四白话文有口语化、大众化的一面,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它只是形式上的白话,内涵则是现代性的,其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历史、文学、社会、政治等思想则是一般民众所不能理解的。文学上可以大众化、通俗化,所以任何时候都有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但思想只是“有”与“无”,没有通俗与深奥之分。没有丰富的思想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史学、文艺学等思想体系。晚清白话文如果作为汉民族通用语,传统中国思想很大程度上就会消失,这也意味着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拒绝,那将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倒退。
五四时期,真正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礼拜六”文学等,他们使用的是晚清作为口语的、工具性的白话文,白话不够用时就用文言文。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诗歌、鲁迅小说以及周作人散文等所用的白话虽在工具层面上和晚清白话无异,但在思想上却是充分“西化”的白话,正是因为其思想性,所以它迅速地延及思想文化各领域,成为汉语通用语,也就是当时的“国语”、后来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不仅是白话文,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它包容了文言文,也包容了西方语言,所以它不是口语,不是大众语,而是民族标准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一直在变化发展,汉语向何处走也有很多争论,特别是文学上有各种尝试,比如有人向古文学习把白话典雅化,有人把白话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白话更“白”,但现代汉语的思想本体性始终没有变,即其在思想层面上始终具有现代性。
五四白话文的形成,因素很多,但核心内容是西方性,是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是通过翻译逐渐完成的。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到思想文化学习的三个阶段,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阶段是递进式的发展。西方的器物虽然很多,但翻译其实相对简单,本质上是“词”与“物”的命名问题,只有规定性,不存在错误或者不准确的问题,所以文言文基本可以胜任这种翻译。但到了社会性问题的翻译时,文言文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严复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如《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名学浅说》等时,就变得非常艰难,所谓“天演”“原”“群”“己”“名学”其实都不准确,非常勉强,这些词后来在现代汉语中有了更准确的表达。到了五四时期,西方大量深层次的哲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的思想输入中国,此时文言文完全无法胜任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言文中就没有西方思想中“宪法”“人权”“学术”“社会”“研究”“逻辑”“典型”“创作方法”等对应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相应的话语体系,所以,这些概念从内容上来源于西方,但从语言上来说则是创造,这才是五四白话文的实质,也即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新的语言,与西方语言更具有亲和性,与晚清白话文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文学翻译也是这样。纵观近代至现代文学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文学翻译基本上可以说是“改写”。林纾是大翻译家,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懂外语,他的翻译主要是由懂外语的助手先把外国小说用口语即白话进行翻译,然后林纾再把它改写成“古文”,即当时标准的汉语。这一事实的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内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助手或者合作者的“口译”恰恰是非常准确的,至少比如林纾改写之后的翻译要准确。但在当时,白话是不入流的口语,书面语还是文言文,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正统的“雅”事,必须用纯正的文言文中的“古文”。但西方文学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文言文根本就不能准确地翻译,或者翻译了一般读者也不能理解,所以林纾的办法有二: 一是“删”,把中国人不能理解和不容易理解的内容删去;二是“改”,把西方的故事改成中国古代的故事,把西方的情理改成中国的情理,把西方的说话方式改成中国的表达方式,同时还增加一些中国式的故事、细节以及对话等,这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恰恰是“正确”的。郑振铎认为林纾“错误”的翻译是“口译者所误”:“这两个大错误,大约都是由于那一二位的口译者不读文学史,及没有文学的常识所致的。他们仅知道以译‘闲书’的态度去译文学作品,于是文学种类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确有不朽的价值与否,足以介绍与否,他们也不去管他;他们只知道随意取得了一本书,读了一下,觉得‘此书情节很好’,于是便拿起来口说了一遍给林先生听,于是林先生便写了下来了。”(郑振铎367)这是值得商榷的,林纾的翻译方式与口译者有一定的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林纾的自我选择,而选择的根本原因是对翻译的理解。傅兰雅介绍当时的翻译:“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傅兰雅287)这和林纾的翻译情况是一样的,也是先翻译成口语即白话文,然后再加工成书面语即文言文。
用白话翻译,理论上应该有很多读者,会受到民众的欢迎,但其实恰恰相反,晚清具有阅读外国文学能力和水平的读者主要是旧式知识分子,而旧式知识分子的语言是文言文的,晚清尤其盛行典雅的桐城派古文,他们是不会读白话作品的,那不仅仅与他们的身份不符合,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审美观不一致。在他们看来,文言文是高雅的,而白话文是通俗的,这也是外国文学在晚清必须用文言文翻译的重要理由。白话是民众的语言,但晚清白话还只是在口语的层面上通行,民众识字有限,接受教育有限,所以虽然白话文他们能够理解,也能够懂,但他们实际上没有阅读的能力,也没有阅读的条件,因而白话文翻译实际上没有读者,这其实是晚清外国文学翻译不能用白话文的真正理由。在当时的文化、文学背景以及语言背景下,林纾的翻译恰恰是标准的翻译
用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在晚清大行其道,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西文,随着翻译观念的发展变化,这种翻译变得越来越难,内在原因是相异的语言,相异的文学趣味,文言文根本就不能准确翻译西方文学特别是其艺术性,文言文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中国古代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2册,初版时一共卖出41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文言文的限度内这可以说是上乘的翻译,但购买者很少,这说明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在当时已经没有市场。而外在原因则是清末民初汉语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汉语中的西方因素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向白话转变,也即白话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文学翻译不仅越来越趋向准确,也越来越趋向用白话,白话翻译不仅更准确,同时也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
晚清的白话文主要是命名西方新事物,而五四白话文除了命名西方事物以外,主要是增加新思想,这种新思想的加入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白话文的性质,也即使它从交际性的工具语言变成了书面性的思想语言。所以,“思想”才是五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最终成为“国语”的最重要的原因。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称文言文是死了的语言文字,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5),这是正确的,但这里的“死语言文字”不是从表达上来说的,也即不是从语言形式上来说的,而是从思想内容上来说的,形式上文言文并没有死,当时很多人还用文言写作,但从思想上来说,文言文是旧的语言体系,它不能准确地表达新的西方思想,因而可以说是“死的”。
三、 语言之辅与语言之主
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之间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作用上的“启蒙”与“革命”、性质上的“工具”与“思想”的差别,还在于地位上的“辅助”与“主体”的差别,也就是说,晚清白话是文言文的辅助语言,当时正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通用的、作为汉语语言体系的是文言文,白话主要是口语、民间语言、大众语言,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书面语体系,白话在思想的层面上还不能独立表达,还必须借助文言文,所以,白话文在晚清时实际上只是补文言文之不足,即弥补文言文在民间事物以及西方事物表达方面的不足,具有从属性。相反,五四白话文从一开始就是要取代文言文从而取得正统或中心地位,不是要提高地位,而是要“当家作主”成为民族共同语即“国语”,事实上,五四白话文最终成为一种新的语言体系。五四之后,文言文在一定范围和层面仍然在使用,但文言文总体上是逐渐退出现实使用而“历史化”,最终成为辅助性的语言,其主要作用是言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文学上则是表达传统趣味。官方的文件、通告,中小学教育,其语言全改成白话文。今天,一般民众,不要说表达和写作用文言文不可能,就是能够读懂文言文的都是极少数,文言文在通用语言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彻底被废弃了。
胡适曾描述晚清一般人的语言过程:“那些用死文言的人,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6)这其实也说明了晚清的语言状况,那时,文言文是“法定”的民族共同语,是正规的语言、是雅正的语言,白话思想和表达只有转换成文言思想和表达才具有“合法”性、正统性,才可以抵达主流的领域比如学校、官府、图书出版等。不仅当时的文学翻译和思想文化翻译是这样,很大一部分人的思维也是这样的,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思维语言是白话文的,书面表达是文言文的,正如今天很多人学外语一样,思维是中文的,不论是理解还是表达,中间始终有中文“翻译”的存在,真正的直接用外文进行思维的其实非常少。这种语言方式麻烦、别扭,丢失信息很多,在晚清社会和文化状况下还可以勉强运行,而到了现代时期,特别是在外国思想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完全行不通,根本原因是现代的、西方的思想没法用文言进行翻译和表达,强行把现代思想用中国典故来表达,已经不是翻译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了,而是“改写”“再创造”,不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是具有质的变化。同样,在文学上,强行把现代人的情感和审美用文言文来言说,实际上是把现代古代化,最后体现出来的是古代的情趣,这同样是性质的改变。胡适在美国求学八年,他的整个思想方式、知识体系都发生了变化,中西比较和转换在他那里是通过白话文和英文来完成的,但他要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国内,还需要把白话文再转换成文言文,这不仅是麻烦和“工序”复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可操作的问题,所以胡适提出直接用白话文进行表达,不仅“准确”,而且“现代”,这才是他提倡白话文的根本原因,也是现代汉语最深层的逻辑。
所以,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后来定为“国语”并继续发展为现在的现代汉语,它的内涵远比晚清白话文丰富,是各种因素构成的,也包括文言文的因素。文言文作为语言体系,它仍然存在,但却是以历史的形态存在,现代人也偶用文言文作文,但这非常边缘,构不成主流。文言文要言说现代思想和现代情感,必须借助白话文,包括现代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而晚清的汉语状况是相反的。所以,就提倡白话文来说,清末的裘廷梁、陈子褒比胡适更早,但他们提倡的背景不同,希望达到的目的不同,具体内涵也不同,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在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很多人对胡适的文学贡献包括提倡白话文的贡献进行了批判和贬低,除了一些“时论”以外,也有一些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比如谭彼岸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有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才有历史根据。”(谭彼岸3)据此,谭彼岸认为“胡适可以从心所欲地盗窃晚清白话先驱者的主张,割断晚清白话文运动,而使人不知不觉被欺骗了”,他批评胡适“把白话文的发祥地硬搬到美国去”(4)。这就是没有认识到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之间的根本性质不同。从时间上来说,晚清白话文的确先于五四白话文,胡适以及陈独秀都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胡适曾主编白话报《竟业旬报》,陈独秀曾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开办”17),他们在五四之前都曾尝试过写作过白话文,他们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过程以及作用等都非常清楚,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显然和他晚清提倡白话文不是一个理路。况且,白话文也不是从晚清才有的,早在汉代就有了。因此即使在形式上,胡适的白话文也不仅是延伸晚清白话文。当然,胡适用《白话文学史》一部书来证明白话文“古已有之”,从而证明五四白话文的合理性,这是错误的,由此也可见他本人对五四白话文在思想上、现代性上的认识不足。
刘禾描述五四白话文运动,“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在影响的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在语言经验的所有层面上都根本改变了汉语,使古代汉语几乎成为过时之物”(刘禾26)。取代文言文而成为新的通行语言,或者说建立一种新的语言体系而取代旧的语言体系,这才是五四白话文区别于晚清白话文的最重要特点。夏丏尊曾批评白话文:“白话文最大的缺点就是语汇的贫乏。古文有古文的语汇,方言有方言的语汇,白话文既非古文,又不是方言,只是一种蓝青官话。从来古文中所用的辞类大半被删去了,各地方言中特有的辞类也完全被淘汰了,结果,所留存的只是彼此通用的若干辞类。”(夏丏尊266)这里所说的白话文其实更像是晚清白话文,他所批评的就是后来“国语”建设所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五四白话文就是在充分融合古文、方言、外国词汇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语言体系,它不仅融汇文言文,也包容中国古代作为口语的白话,更重要的是它大量吸收了西方语言因素。
从五四白话文到“国语”到现在完备的“现代汉语”,这也有一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汉语“现代化”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目前还在继续。所以,五十年代翻译家傅雷从翻译的角度谈到当时白话文的不足:“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傅雷611—12)当然,这只是傅雷个人的感受,其实1950年代现代汉语已经完成了体系的建构,只是还需要丰富完善而已。但这说明当时的现代汉语还有弱点,特别是在翻译上有局限性。这种弱点和局限在1980年代之后得到极大的改善,在1990年代之后更成熟了,特别是在“现代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这个“现代化”的当代进程中,傅雷的翻译语言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语言上,五四新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是正统、主流的文学,相反,文言文即古汉语的文学被称为旧文学,则沦为边缘、次要、点缀性的文学,成了可有可无的文学。
在文学上,晚清也有白话文学,但它和五四白话文文学具有质的不同,晚清白话文学是通俗文学,是传统文学的通俗化,也即思想趣味上虽然是高雅的,但形式上是大众化的;同时是民间文学,即下层文学,也表现和迎合下层人民的审美趣味。晚清白话文学不管是通俗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都是附属性的、补充性的、次要的、低层次的,正宗的文学是文言文的文学,它代表了晚清文学的类型、高度和水平。而五四白话文学即新文学,是纯文学,代表了民族文学的最高层次,是现代时期的主流文学,是正宗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晚清的白话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
晚清所谓“通俗文学”,本质上是文化“下移”的结果。王尔敏说:“晚清流行通俗文学,十分繁富,在当时言,并无认识上之困扰。其意旨在于通俗,而其文体形式则什九并非白话。当时人重在雅俗之别,并未考究文体表达之如何浅白。虽然同时有人提倡白话文,亦有少数人从事白话文写作,但在当时通俗文学之中,白话文所占分量甚小。通俗之重点在于俗,必为习俗所能接受,习俗接受不必即是白话,此为当时通俗文学一致之现象,后人不可误解。[……]质言之,我辈在此必须了解清楚: 通俗文学并不等于白话文学,而只可以包括若干白话文学。”(王尔敏76)也就是说,晚清的白话文学只是晚清文学通俗化的一种方式,通俗文学只是晚清文学的一个次要种类,附属于作为纯文学的文言文学,而白话文学又只是通俗文学的一个种类和方式,可见晚清白话文学的微不足道,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地位,也没有产生什么有影响的、真正对中国文学的进程具有推动意义的作家和作品。反过来,五四白话文学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学,是纯正文学,是高雅文学,是新文学,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具有革命性,不是“通俗文学”,相反,它思想上的深刻性,艺术上的创新性,不仅一般大众不能理解,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能理解,它的“通俗”仅只是文字和语言形式上的。正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所说:“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新文化”219)也就是说,通俗文学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白话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反过来说,不一定白话的就是通俗的。五四白话文学在形式上的确有通俗的因素,但在内容上,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纯文学,和“通俗”相距甚远。
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很多人认为“平民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周作人特别作了辩解:“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惟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平民的文学”5)五四白话追求“通俗”,希望新文学能够有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享受这种文学,从而达到“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作用,傅斯年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傅斯年133)可见白话文只是手段,比白话文更深层的是思想改造,诸如反封建、反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建立新的人的文学,这才是五四白话文学的根本目的。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新文学不是迎合平民,恰恰是提高平民,改造平民。
五四白话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之主体,而晚清白话文学则是晚清文学之辅助,这从根本上是由“语言之主”与“语言之辅”决定的,也可以说是“语言之主”与“语言之辅”在文学的外在表现。
总之,晚清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在外在形貌上很像,但在具体内涵上,在地位上,在性质上都具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生成的,可以从五四白话这里得到深刻的阐释。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7—20。
[Chen, Duxiu. “The Origin ofAnhui
Vernacular
News
.”Se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 Vol.1.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17-20.]——:“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17—21。
[- - -. “What Is New Culture Movement?”Se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 Vol.2.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217-21.]——:“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演讲底大纲”,《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93—97。
[- - -. “Why Do We Write Vernacular Chinese? A Speech at Boone University in Wuchang.”Se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 Vol.2.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193-97.]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翻译论集》,罗新璋、陈应年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278—94。
[Fryer, John. “Kiangnan Arsenal’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Books.”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Eds. Luo Xinzhang and Chen Yingn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278-94.]傅雷:“致林以亮论翻译书”,《翻译论集》,罗新璋、陈应年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611—12。
[Fu, Lei. “Letter to Lin Yiliang on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
. Eds. Luo Xinzhang and Chen Yingn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611-12.]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5—36。
[Fu, Sinian. “How to Write Vernacular Chinese.”Complete
Works
of
Fu
Sinian
. Vol.1.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125-36.]杰罗姆·B.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Grieder, Jerome. B.Hu
Shi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1917-1937. Trans. Lu Q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61—80。
[Guo, Moruo. “Literary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Collected
Works
of
Guo
Moruo
. Vol.10.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361-80.]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的《导言》)”,《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6—39。
[Hu, Shi.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 Vol.1.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106-39.]——:“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64。
[- - -.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st Fifty Years.”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 Vol.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200-64.]——:“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4—57。
[- - -.“On a Constructive Literary Revolution.”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 Vol.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44-57.]——:“《尝试集》自序”,《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0—83。
[- - -.“Preface toAttempt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 Vol.9.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70-83.]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Liu, Lydia H.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 1900-1937). Trans. Song Weijie,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7—52。
[Lu, Xun. “A Joke Is a Joke, Part One.”Complete
Works
of
LuXun
. Vol.5.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547-52.]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91—97。
[Qu, Qiubai. “Europeanized Literature and Art.”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Literature
. Vol.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491-97.]——:“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61—85。
[- - -. Realistic Issues o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Art.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Literature
. Vol.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461-85]谭彼岸: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
[Tan, Bi’an.The
Movement
of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1956.]王尔敏: 《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
[Wang, Ermin.The
Rise
and
Fall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王照:“挽吴汝纶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31—32。
[Wang, Zhao. “Epitaph for Wu Rulun.”Collected
Essays
on
the
Late
Qing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 Beijing: Character Reform Press, 1958.31-32.]夏丏尊:“先使白话成话”,《夏丏尊集》。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2年。266—68。
[Xia, Mianzun. “The Priority Is to Make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a Real Language.”Collected
Works
of
Xia
Mianzun
.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2.266-68.]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翻译论集》,罗新璋、陈应年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202—204。
[Yan, Fu. “Translator’s Preface toEvolution
and
Ethics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Eds. Luo Xinzhang and Chen Yingn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202-204.]郑振铎:“林琴南先生”,《郑振铎全集》。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356—71。
[Zheng, Zhenduo. “Mr. Lin Qinnan.”Complete
Works
of
Zheng
Zhenduo
. Shijiazhuang: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356-71.]周振鹤撰集 顾美华点校: 《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Zhou, Zhenhe, and Gu Meihua, eds.Studies
on
Sacred
Edict
of
the
Kangxi
Emperor
,with
Annotations
.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6.]周作人:“平民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7。
[Zhou, Zuoren. “Literature of the Populace.”Art
and
Life
.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3-7.]——: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6—89。
[Zhu, Xizu. “New Literature Is Not Eclectic Literature.”Major
Works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ism
. Shanghai: Young Companion Books, 1935.86-89.]朱自清:“论通俗化”,《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142—43。
[Zhu, Ziqing. “On Popularization.”Complete
Works
of
Zhu
Ziqing
. Vol.3.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6.1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