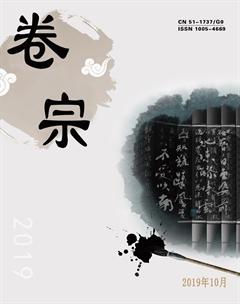娄烨电影中边缘人物形象分析
摘 要:第六代导演是中国影坛上备受瞩目的群体,娄烨无疑是第六代导演中颇具潜力的一位,娄烨的作品因题材和内容备受争议以及受严格的审查制度所限,导致其许多作品无法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但这并未影响娄烨对于电影的热爱以及通过电影的途径来表达自我。
关键词:边缘人物;需求层次论;欲望
1 娄烨电影中所刻画的边缘人物形象
纵观娄烨的影视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主要人物形象一个共同点,即极力刻画边缘人物形象。对于“边缘人物”这一词语的定义十分广泛,既可以指徘徊在社会边缘或底层的小人物,也可指漂泊无依的弱势群体。马斯洛指出“至少从理论上可对某人的单一行为尽可能的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表现根源”[1],娄烨电影中的边缘人物形可分为两类:以社会身份作为定位依据的边缘人物和具有边缘心理的普通人。
1)以社会身份作为定位依据的边缘人物。《推拿》中刻画的是盲人群体,富有文艺情怀的沙复明,受荷尔蒙支配的小马、极度自尊的都红都是社会身份处于边缘的人物代表。影片中按摩院的服务员、按摩房的性工作者,他们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苏州河》中马达靠送货赚取微薄收入,与同伙计划绑架牡丹也是出于窘迫的生活状态,美美靠着在水箱中表演美人鱼为生,他们身份地位的底下决定了其边缘人物属性。《春风沉醉的夜晚》中女工李靜,与罗海涛在一起的同时依附于老板阿明,在阿明入狱后,只能以身体作为筹码换取阿强的帮助,也是以社会身份作为定位依据的边缘人物。
2)具有边缘心理的普通人。《苏州河》中家庭富裕的牡丹,缺乏原生家庭的关爱,心理上极度缺乏归属感;《浮城谜事》中乔永照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但因依附于妻子缺乏男人的尊严;《春风沉醉的夜晚》中江诚则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靠着和不同的男人在一起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已婚男人王平拥有看起来幸福的家庭,但实则并不幸福,他们都是具有边缘心理的普通人。
2 娄烨电影中边缘人物形象的特点
1)归属和爱的缺失。马斯洛指出“爱是一种两个人间健康的、亲热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当其中一放害怕他的弱点和端出会被发现时,爱常常就受到了伤害”[2]娄烨的成名作《苏州河》中,单亲家庭的牡丹十分缺乏归属感和关爱,非常规的家庭状态和模式未给牡丹提供足够安全的环境,于是她试图从马达身上找到归属感;同样,美美也是处于双重矛盾下的,一边和“我”在一起,一边又极其渴望马达口中的爱情,她在与“我”的关系中没有得到想要的归属感和爱,所以对马达并不反感,反倒希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牡丹。
《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王平很大程度是迫于社会的压力选择和一个普通女人结婚,靠着暗地里与江诚的相互慰藉寻找归属感和爱,当两人的地下情暴露后,王平甚至想要与妻子林雪离婚以保全“真我”,当江诚选择避而不见,王平的心理防线几近崩溃,最终选择了割腕;江诚没有选择像王平一样向世俗低头,一直在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寻求自身的归属,不管是王平、罗海涛还是出现在最后的新男友,于江诚来说都是自己归属感和爱的来源,。罗海涛的女友李静也是在追求归属和爱,男友罗海涛的顽劣成性和幼稚不成熟,让她得不到应有的关爱,相反有妇之夫的老板阿明却对其百般呵护,在阿明身上她感受到了在男友身上得不到的归属感和爱,这也是她长期在道德的禁锢和出轨之间徘徊的主要原因。
2)对尊重需要的渴求。《推拿》中的都红与其他盲人技师最大的区别在于她能够正视自己是盲人的事实,并一直在追求和常人同等的尊重,可以说她的内心十分理性,她可以勇敢的接受自己是盲人的事实并且认可这样的事实。都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代表人物,她非常明白自己外貌的美在男性的意识中是什么,所以才拒绝了沙复明的爱意,这也是她内心极力想要追求被尊重的表现。在对小马暗示心迹未得到回应后、遭遇了意外事故折断了手指,她毅然离开推拿中心,既保全自己在爱情中的自尊,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罗海涛女友李静的前后变化,源于由寻求归属感和爱的需要转变为寻求尊重需要,影片以李静的两次剪发为契合点展现她的心理变化。第一次剪发是与罗海涛分手,老板阿明被抓,李静此时的归属和爱的需求自然是处于缺失状态的,而要换取阿明的被释放,她只能用肉体作为筹码来得到阿强的帮助,使得李静人格上受到的侮辱。在阿明被释放后,李静并没有再度寻求归属和爱,因此此时迫切的需要也已经被另一种需要所取代,即尊重需要,她的愤怒和仇恨难以消除,以至于选择离开阿明回到罗海涛的身边。第二次剪发是在李静再一次回到海涛身边,与江成一起三人共同出行旅游时,旅游的过程愉悦而开心,但是潜在的矛盾依旧存在,她发现了罗海涛与江诚之间的关系,此时的她内心是矛盾的,再度燃起的对于归属感和爱的需求,转瞬又被尊重需要所代替,当她买完东西回到宾馆之后看到男友与江成的激吻,终于意识到这种所谓的三角关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内心对于尊重需要的渴望再度燃起,所以独自离开。
3)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苏州河》中始终未露面的“我”在不断的寻求自我实现中一点一点吞噬自己的“情欲”。“我”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凌驾于每个人的故事之上,“我”从来不曾暴露过自己的内心,也从不插足别人的生活,更不会从别人身上寻求安全感,所追求的只是为实现自我价值。虽然看着美美每天出门,“我”会担心美美再也不回来,但一切只是因为“我”正被美美所需要,在美美的需要中“我”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当美美留下纸条“我走了,来找我”后,“我”并不会真的去找她,而是宁愿闭着眼等待下一次爱情,此时此刻美美已经不再需要“我”了。与其漫无目的的寻找不如迎接下一次爱情,“我”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样也可以寻找另外的载体。
《春风沉醉的日子》里,王平的妻子林雪也是寻求自我价值的代表,身为中学教师的林雪过着平淡且幸福的生活,丈夫的一次外遇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当得知丈夫的外遇对象是男人后,林雪的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重创,她本想压下来不做声张,一如既往的维持夫妻和谐的表象,但真相还是暴露了,扮演贤妻角色的林雪存在感减弱,在王平那里她找不到自身价值实现的载体。得知王平死去的消息时,王平的妻子和江成表现出了两个完全不相同的行为。江成独自一人蜷缩在角落里泣不成声,妻子林雪第一时间不是为丈夫的死而感到伤痛欲绝,而是害怕警察的追查,她对丈夫已经没有什么爱情可言,更多的只是在破坏的基础上寻求一种补偿。
3 结语
醉心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娄烨,其电影所最终的指向并非政治而是人性和欲望。“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无不首先具有深刻的‘审美性……现实的血肉并不比最离奇的幻想更容易把握。”[3]娄烨电影的核心在于自身价值观的表达,对于“边缘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娄烨电影中鲜明的特点。娄烨选择“边缘人物”作为电影的着眼点,通过人物关系映射社会和时代,试图挖掘人性的真实和复杂。作为一位作者导演,娄烨坚持不懈拍摄更为纯粹和有意义的影片,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怀和注目。
参考文献
[1]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47.
[2]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5.
[3]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社,2005:275.
作者简介
李婧(1994-),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电影批评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