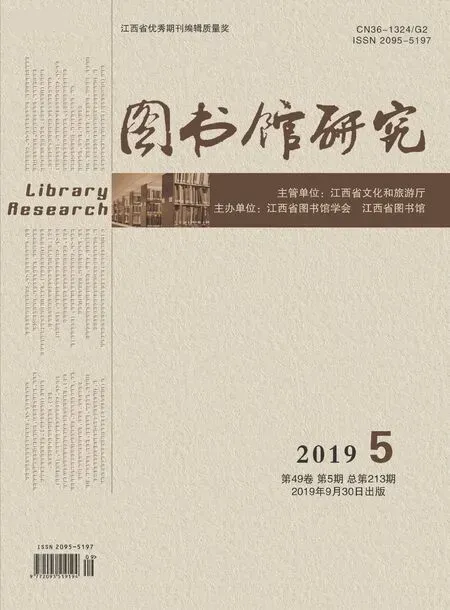论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对底本的修正
——以《毛诗注疏》为例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南昌府学刊刻《十三经注疏》所据底本为元刊明修十行本(以下简称元刊明修本)。是版刊刻年代既久,粗糙漫漶,修版多次,舛误尤多。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书前阮元《附记》云:“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1]刊刻之初,面对如此粗劣的底本,关于是否修正、如何修正一定有过一番论议,最终形成不予轻改、加圈于旁、后附校记的体例。但是元刊明修本毕竟墨钉满版,并且俗字、讹字较多。南昌府学具体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又进行过哪些修正?今以南昌府学所刊《毛诗注疏》为例进行探究。
1 底本墨钉之修补
“墨钉”即古籍中用以表示阙文的方形黑块,南昌府学刊刻底本——元刊明修本中存在大面积的墨钉。单以《毛诗注疏》为例:统共有二十卷,其中卷一、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十四、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以及卷二十,都存在较大面积的墨钉。这些墨钉,少者几行,多者满页,严重影响阅读,其中尤以卷八之一的《豳谱》部分为甚。面对这种情况,南昌府学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补齐墨钉所阙。需要探究的是,南昌府学根据什么材料缮补墨钉。南昌府本《校勘记》中提到闽本(嘉靖李元阳本)、明监本(万历北监本)、毛本(崇祯汲古阁本),说明这些本子都可参考。此外,乾隆武英殿本,作为一个通行版本肯定可以见到,《校勘记》中没有提到,可能出于政治考虑,不便指出御纂版本之讹。以上四种版本较为完整,皆可作为缮补墨钉的参考。现以《毛诗注疏》卷八之一《豳谱》部分为例,将以上四本与南昌府本进行对校。另外,日本足利学校藏有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刊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日本汲古书院印刷所1974年影印,以下简称“宋十行”),经鉴定是元刊明修本的底本。日本杏雨书屋藏有南宋单疏本《毛诗正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以下简称“单疏本”),亦为宋刻。二本皆可视为较为原始的版本,借以判断南昌府本是否缮补正确。

表1 校对结果统计表
校对结果汇总如表1。根据上表校对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李元阳本作为最早缮补墨钉的版本,所补墨钉多数妥当,当是参考了当时较为可靠的版本,多为沿袭其而来的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所借鉴,价值应当得到肯定。但是李元阳本所补墨钉并非完全准确,不少讹误出自此后。如“金滕直云”之“直”误作“惟”,“积德勤民”之“勤”误作“爱”,“俱是先公”之“俱”误作“则”,也被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袭用。
其二,汲古阁本对李元阳本以来产生的错讹做出一些纠正。例如“俱是先公”,李元阳本、北监本“俱”误作“则”,汲古阁本作“俱”,合于宋本。又如“也故金滕”,李元阳本、北监本、武英殿本“故”误作“彼”,汲古阁本作“故”,合于宋本。汲古阁本所做修订还有部分存在讹混,例如“金滕直云”之“直”,李元阳本、北监本误作“惟”,汲古阁本改作“勤”,宋本作“直”;“积德勤民”之“勤”,李元阳本、北监本误作“爱”,汲古阁本改作“直”,宋本作“勤”。日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亦云:“谨按正德嘉靖万历本上‘勤云’作‘惟云’,‘直民’作‘爱民’,崇祯本乃改之,误换其处。”[2]毛晋作为明代藏书大家,可能参照所藏秘本、珍本进行过校改。孙从添《藏书记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3]后世亦以汲古阁本错讹尤甚。现在看来,汲古阁本《十三经》也改订了许多陈陈相因的错误,价值不可小觑。
其三,南昌府本所补墨钉准确,皆与宋本相合,不承诸家之误。例如“金滕直云”之“直”,“积德勤民”之“勤”,“入摄王政”之“政”,“故亦谓之”之“谓”,“故周公”之“故”,诸本皆误,南昌府本独确。以上诸例,除了“积德勤民”条下引述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按语,“十有一年”条下运用理校,征引《正义》说明判断“十有三年”错误的依据之外,其余各条皆为直接改正,没有说明依据。可以证明,南昌府本缮补墨钉并不仅仅借鉴传世诸本,它的质量超出传世诸本。清代校勘考据之学大盛,至于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刊刻之时,已经出现多种校勘《十三经》的著述,重要者有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和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上校勘成果均与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关系密切。
1.1 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是书全本不存,残帙见于《群书拾补》。据《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云:“抱经先生手校《十三经注疏》本,后入衍圣公府,又转入扬州阮氏文选楼。阮太傅作《校勘记》,实以此本为蓝本。”[4]可见阮元曾经参考卢氏校勘成果。卢文弨喜校书,且又多观善本[5],《周易注疏校正》云其曾见“明人钱孙保影宋钞本”。因此卢氏校勘质量较高,价值较大。
1.2 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
浦镗自称采用北监本和汲古阁本进行校对。《例言》:“闽本及旧监本世藏较少,故据监本修版及毛氏本正焉。”又云:“修版视原本误多十之三。”[6]《豳谱》部分共出《校勘记》二十九条,其中五条直接引用浦镗说法。虽然浦镗所据底本较差,但是通过理校予以辩证,多有见地,成果亦被南昌府本吸收。
1.3 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
根据《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二年六月,阮元曾刊《七经孟子考文》。[7]是书《凡例》当中详细列举所校诸本:“有曰宋本者,乃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一通;有曰古本者,乃足利学所藏书写本;有曰今本者,谓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经注疏》本。”[8]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云:“山井鼎所称宋本,往往与汉、晋古籍及《释文》别本、岳珂诸本合,所称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诸本,竟为唐以前别行之本。”[9]对山井鼎所据古本价值加以肯定。《豳谱》中的补版部分,山氏共有四条出校:
1)金滕直云居东:宋本疏《金滕》:“勤云居。”“勤”作“直”。
2)由其积德勤民:宋本疏《金滕》:“由其积德直民。”“直”作“勤”。
3)其入摄王政也:“室”作“政”。
4)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三”作“一”。
以上四条,李元阳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皆误,南昌府本不误。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山井鼎等惟能详记同异,未敢决择是非,皆为才力所限……至于去非从是,仍在吾徒耳。”[10]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能够订正诸本之讹,亦因甄别采用山氏所供宋本线索。
2 底本文字之校正
阮元《附记》申明:“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那么南昌府本是否确如《附记》所言,明知底本误字却不轻改?通过校勘发现,南昌府本对于底本做了大量校正,并非“不使轻改”。《豳谱》之中,元刊明修本共有四十二例直接修改,没有校记说明。这些校正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元刊明修本的错讹明显。例如:“岐山”,元刊明修本作“皮山”。“公刘”,元刊明修本作“其刘”。“谶纬”,元刊明修本作“纤纬”。“文王”,元刊明修本作“又王”等等。并且文字位置多在墨钉旁边,因为元刊明修本的底本宋十行本漫漶不清,导致刊刻有误。诸家版本对此皆有统一的修改意见,如若不加改字,一一出校:一是《校勘记》不免烦琐,二是暴露底本粗劣,三是不便读者阅读,四是造成文本过于落后,因为其余诸本早已修正错误。综合以上原因,南昌府本参考吸收诸家版本,直接改字。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南昌府本对于底本讹字的纠正,跟文选楼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摘录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知道,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有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单刻本,又有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卷后所附《校勘记》,而南昌府本《校勘记》又是卢宣旬从文选楼本《校勘记》摘录来的,同时卢氏又有少量补充。《毛诗注疏》卷八之一《豳谱》部分,文选楼本共有校记二十九条,其中七条校记涉及元刊明修本的文字讹误,这七条分别如表2所示:

表2 文字讹误详表
由表可见,文选楼本七条校记,南昌府本仅仅摘录其中四条。南昌府本摘录出的四条《校勘记》所对应的错误文本,并未直接改正,而是遵从《附记》规定,仅在错字右侧标一小圈。但是另外三条没有被摘录的文选楼本《校勘记》所对应的错误文本,南昌府本直接改动。实际上,卢宣旬对于文选楼本《校勘记》的摘录,并非毫无体例。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判断文字讹谬有所旁证的文选楼本《校勘记》,比如引用浦镗说法的,或者通过他校证明的,卢宣旬都摘录了。但是其他通过各个版本对校,发现文本差异,进而推出讹误的文选楼本《校勘记》,可能觉得参考价值不大,或者认为推论不够踏实,卢宣旬全部删除不录,直接改字。
综上所述,阮元《附记》所谓:明知宋版误字,依旧不加轻改。其实并未落实。《豳谱》部分,校出底本讹字四十七例,其中只有五例加圈出校,包括摘录文选楼本《校勘记》四例,新补校记一例:“‘非是六军之事’。毛本‘事’作‘士’。按,‘士’字是也。”其余四十二例没有说明,直接改动。
3 底本字形之规范
元刊明修本存在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南昌府学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对大多数的俗体、异体字做了处理,主要表现在字形规范、保留原本特征两个方面。对于这些修正,南昌府本一律径改,不作说明。
3.1 字形规范
对于元刊明修本中出现的俗体字、异体字,南昌府本予以规范处理。例如,元刊明修本“挕”改作“攝”,“”改作“作”,“揔”改作“總”,“”改作“魄”,“刘”改作“劉”,“称”改作“稱”,“弃”改作“棄”,“迁”改作“遷”,“尽”改作“盡”,“实”改作“實”,“”改作“興”,“”改作“隰”,“艰”改作“艱”,“乱”改作“亂”,“恋”改作“戀”,“称”改作“稱”。
3.2 保留特征
南昌府本对于元刊明修本的部分字形予以保留,例如元刊明修本的“礼”,李元阳本、北监本、武英殿本俱作“禮”,南昌府本仍依元刊明修本作“礼”。元刊明修本“属”字,李元阳本、北监本、武英殿本俱作“屬”,南昌府本仍依元刊明修本作“属”。此类情况占少数。
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对于经书文字的规范,不仅提高了文本的准确度、规范性,而且可以避免产生文字讹混现象,利于经书文献广泛流传。
4 结语
南昌府本《十三经注疏》通过对其底本元刊明修本进行墨钉修补、讹字修正以及字形规范三个方面的修正,已然成为最为接近宋本,并且校刊精良,字形规范的版本,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阮元《附记》所谓明知有误,“不加轻改”,其实并未落实,而是存在大量文字改动。这条准则更像一个“障眼法”,掩盖了南昌府本所据底本粗劣多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