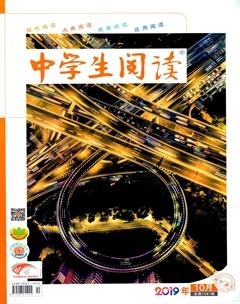谈文章中句子的安排
唐弢
刘知几在《史通》里,论及《汉书·张苍传》里的“年老,口中无齿”,以为其中的“年”“口中”三字,是多余的,改为“老无齿”,意思既没有出入,词句也较为洁净,这见解很不错。
废话的删去固属必要,但是硬把句子装成简短,却又可能降低句子的明确性,使意义不能完整。有的文言文,就有这样的弊病。唐子西《文录》:
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
简短诚然是简短的,但东坡所说,含义并没有完尽。这十个字里并没有指出所在地惠州,也没有“人未之信也”和“浮骨水上”的意思,意义含混,可见是并不高妙的。名手如东坡尚且如此,其他的自然更不必说了。
句子的好坏不能由长短来判断,或长或短,必须合乎提笔时候的需要。什么是提笔时候的需要呢?这就是含义的完整和明确。
然而完整、明确之外,还得讲求格调的和谐,世上固然不会有通篇都是长句的文章,也绝不会全是短句的。普通的文章总是有长句,也有短句,不但长短相间,而且单排(即排句,这里指整齐的句子——编者注)互参,读起来十分匀畅,可以朗朗上口、曲尽抑扬顿挫之妙的。
单句就是自成起讫,可以独立的句子,在普通的单句里,不但忌用太多的相同的字眼。连太多的相同的句调,也得避免,譬如:
两人的脾气是不同的。自然,相通之点是有的。但比较起来,差别是显然可见的。
这种句子在文法上并没有毛病,因为连用了几个“是……的”,读起来却非常不顺口,不舒服。这是因为单句忌同的缘故。倘是排句,即使句法和字眼相同,可就反而见得谐和了。例如:
(一)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
(王安石《同学一首别子固》)
(二)同伴远走高飞,有的发了财,有的做了官,有的为害于民,有的为利于国,有的流转沟壑,死而不得其所……
(李健吾《希伯先生》)
属于同一范围或同一性质的事象,用字数相近、组织相似的句法逐一表现出来,这就是排句。有些是短排,如第二例;有些是长排,如第一例。但即使是排句,它的本身也还须有变化,绝不能用一种句法排到底的,譬如第二例的“有的发了财,有的做了官”,是一种式样,“有的为害于民。有的为利于国”,又是一种式样,“有的流转沟壑,死而不得其所”,则又单独地成为一种式样,这正是使文章灵活多彩、避免呆板的办法。
再就意义上说,排句也有逐步分別浅深的,或则由浅而深,或则由深而浅,例如: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
(二)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些句子,含义都是一步紧似一步,不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似的,彼此并列了。这可以说是排句的别具一格。但在形式上,并没有显然的区别。
出乎排句,而在形式上又和排句稍有区别的,是修辞学上称为反复的句子。正如字之有复叠一样,反复的句子也是为了要表现强烈的情感和意见,这才用重复讲述的方法,把同样的话讲上好几遍。于此,人们可以得到一种强烈而又和谐的感觉。例如《论语》上的: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这是因为冉伯牛生了麻风病。孔二先生非常惋惜,所以反复申说,以表示低回嗟叹的意思。相似的例子多得很,这里不再枚举了。但是,反复的句子还有两种不同的式样。须交代清楚。一种是隔开来的,如:
(一)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周易》)
(二)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我静静地来到这里的山上/——时间是正午/天上没有一片云/太阳牢不动地在天空钉着/兽藏洞中/蛇卧草里/树脂如蜡泪一般地流着/一滴一滴地枯死在岩石上/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毕奂午《山中》)
这种隔开来的反复句子,当以用在诗歌里的为最多,但在别的文章里,有时也一样可以找到,例如鲁迅在《出关》里,就用了好几句“好像一段呆木头”,来形容老子的毫无动静。还有一种反复的句子,是就原句加一二虚字,使字数略有变动,而仍保持大部分的面目的。如: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秋夜》)
按照惯例,反复的句子总是申述同一意义,指点同一事物的,这里的例子所指的却是两株树,两件同样的东西。本来只用“两株枣树”四字,就可以说完了,作者却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说,用以增加文章的韵味,使人对此有回荡的情调、朴美的感觉。而这所谓回荡的情调、朴美的感觉,也往往是反复的句子的同有的特性。
(节选自《文章修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句子的构造和安排”)